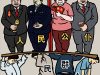最近,中国当红的知识份子季羡林离开了这个对他花团锦簇、亲亲热热的世界。如果他继续活下去,他一定会继续红下去,或者会更红下去。作为长者,98 岁离开尘世,应该受到分外的哀悼和尊重;作为一个学者,他在所从事的学术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应该得到社会的好评。用一句中国人常用的老话,他的死,是中国学术的一个损失。
在中国,他的死,又一次掀起了对他歌功颂德的一阵红浪。他的死可以说备极哀荣。中央领导的花圈,中央领导的送葬,使有些知识份子感受到大师的身价,为一些想跻身大师行列的大师后补者指明了航向,鼓起了内劲。全国的报刊电视,也忙着将他热炒了一阵。如果用红人言之,季老先生成了一个当朝的大红人;
如果用明星言之,季老先生成了一颗学术大明星。一个人活着到地球村来一次,活到如此模样,也算是不虚一游了。
是什么因素使得季老先生如此走红呢?研究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问题,理应列入国家重点课题。就国家而言,季先生被人称为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如果把造就大师、造就泰斗、造就当红学术明星的规律搞清楚,我们国家就可以培养更多的季羡林式的泰斗,培养更多的季羡林式的大师,培养更多的季羡林式的明星。这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就个人而言,如果总结出大师成功、大师走红的奥秘,更多的有志于成为大师的准大师或潜在大师们,就可以更自觉地走上自我培育之路,就能更自觉地向着高入云端的大师的高峰攀登,就能更好更快地成为大师、成为泰斗级的人物,至少可以多走一些捷径,少走一些弯路。人当红了,好处是很多的,人成了大师,成了泰斗,好处就更多,且不说领导不时地会关照你出镜出场,而且还有可能为你提供大师工作室,更有可能你死了会有高层领导送花圈,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荣光啊!因此,如果这个课题做得好,于公于私,实在是意义非凡。
不过,由于我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没有学好,也没有把和谐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光辉理论学懂学透,我一点也想不明白他如此发红的原因。在我的记忆里,有两件与老先生有关的事给我印象深刻,报上曾经报导过。这两件事都不是走红的充足理由。
一件事是,他老人家支持了一个企业家(一说是他的一个学生)出版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的宏伟计划。这部巨著将由季老先生当主编,它将收罗中国古代全部典籍,这部煌煌巨著浩如烟海,其价格预定是68000元。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巨著的吉尼斯记录,如果有,季老先生主编的这部书一定可以创造新的记录。可惜,尽管主编这部书的伟大宏图电视台作了播送,尽管银行也投入了几十个亿的钱,但是,这个企业家后来卷走了几十亿元的钱,并从人间神秘地蒸发了。这本书并没有真正开始。季老先生主编的这部巨著至今仍然停留在电视报导的水平上。中国人为此损失了几十个亿(报导说是41亿),全国人民辛辛苦苦为这场骗局买了一次单,也让季老终于没有真正当一回68000元大书的主编。尽管主编没有真正当成,季老先生答应这个企业家主编这样的大书,等于是为骗子做了一回广告,当了一回工具,这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忽悠。如果主编成功,红一下是自然的,应该的。但被骗上当只当了个虚拟主编,毕竟不能成为明星、成为走红的理由。
第二件事似乎也不能作为走红的理由。那就是他的高足、一个著名的教授向他致意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竟凝神息念、膝下一软、扑通一声地跪了下去,对着端坐着的季大师,又扑通扑通地叩了几个响头,在电视的转播下,让全国人民大饱了一次眼福,亲眼看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叩头是一个什么模样。虽然,教授叩头的样子美妙而动人,虽然,教授叩头的声音轻脆而动听,虽然,羡老先生端坐受礼时宠辱不惊,物我两忘,不过,毕竟叩头不能算是一种新生事物,更不能说成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中国的叩头历史实在太悠久了,中国的叩头的人数实在太普遍了;毕竟这次叩头没有叩出与一百年前向老佛爷叩头有本质区别的先进性来。看来,这次叩头有点像是黄盖周瑜的现代版。一个愿叩,一个愿受。可惜,叩头是叩了,受叩也是受了。但这也不能成为季老先生走红的充分理由。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使季老先生在垂垂之年,成为学界的明星和当红的巨匠呢?
是他的高龄吗?不是。高龄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说,巴金老人中年的时候,只有被关牛棚、被批斗的命,能干事的时候不让干事,到了高龄不能干事的时候,却给你戴上了一个又一个大红的高帽子。甚至在巴老先生到了半明白、半不明白的时候,还一个劲地将种种光环套在他老人家的头上。因为他此时,再也不会提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要求了,也不能再写有点自由化思想的《随想录》了。不过,高龄的人很多,多数老人却不走红。并不高龄的学者同样成了大师,同样在走红。看来,要走红,高龄是一个重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是他的国学吗?不是。他虽然被许多迷迷糊糊的中国人尊称为国学大师。其实,他没有研究过国学,也没有出版过国学著作。他对孔学似乎也没有多少深厚的感情。不然,当年打到孔老二、对孔夫子老家抄家、毁林、砸墓的时候,当热火朝天批林批孔的时候,他多少可以表示一点意见、一点痛苦。国学大师么,人们对国学大师的要求应该不一样。但是他没有,他也参加批林批孔,至少不反对。看来,他的国学大师的称号是别人硬给的,后来他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可见,提倡孔学,并不是他走红的原因。
是他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记》吗?也不是,文革中的受难者实在太多了,叶剑英讲话说有1亿人受难。季老先生的受难也并不能算特别深重。即使像我这样的小知识份子也在文革中整了一次又一次,他的《杂记》写作得一般,并没有特别的经历,并没有特别的思想,也没有特别的美文。如果中国的宣传部门不要横下一道禁令,竖下一道禁令,这一类的《杂记》,可以出个成千上万种。我所看到的文革回忆,如《浩劫》,就比它要深刻得多,感人得多。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是什么使季先生成为当红的知识份子呢?
根据我的研究,我觉得是因为他比较和中央保持一致,特别是在8964运动后紧紧地与中央保持一致,这是他当红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有读者指出,“季羡林57年欢呼反右斗争取得辉煌胜利,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邓,等等,中国各个历史转折关头的文章发言,大家自行查找吧。至于季羡林老人家在89年5月去广场鼓励学生坚持到底,而六月初又坚定支持镇/压反革/命暴/乱,反差过于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太好奇。”(原文如此)看来,羡老先生是比较能与时俱进的。
略举一例。五十年前,中国先是搞了个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对于反右运动,他自己表示是衷心拥护的。他说,“这一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份子的.我怀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拥护这场运动。”如何拥护,老先生没有说,读者可以想像。接着搞起了大跃进。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季羡林都要写一篇文章向海外侨胞们报告祖国建设的成就并谈谈自己的感想。1958年他写的文章题目是《在大跃进中庆祝国庆》。文中写道:
‘我以前常用“祖国的建设简直是日新月异”这句话;但是在今年,这句话无论如何也不够了。如果允许我杜撰的话,我想改为“祖国建设简直是秒新分异”。当年领导认为一天等于二十年,季羡林用‘秒新分异’来形容。
当年,中国大地上,到处都在放着半是玩笑半是欺骗的玩笑,说最初在报纸上读到有人想亩产小麦千斤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也满是问号。然而不久亩产千斤的记录就出现了。不但出现了,而且像给风吹着一样,记录一天天升高。有的时候晚报上的最高记录,第二天早晨就被打破。有一些科学家也着了慌,他们用最高深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来证明,小麦亩产最高产量是三千斤;然而事实却打了他们一记耳光,记录一直升到七千多斤,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记录。现在有许多农民和科学家已作出计划,明年的产量不是以千斤计,而是以万斤计。’
‘稻子也是一样,早稻的最高记录已经达到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中稻竟达到四万三千多斤。有些人觉得这些数字简直是神话,他们有点半信半疑。信嘛,他们不能够想像,在那有限的一点点地方,这么多的稻子如何摆得下;疑嘛,他们又知道,中国报纸从来不说谎话。不管这些人怎么想,我可以告诉诸位侨胞:这些记录还只是牛刀小试,不用说明年,就是在今年,也还会有许多地方打破这一记录。至于最高记录究竟是多少,现在很难预言;我只希望侨胞们有一个思想准备,将来不至于过分吃惊。……’
可见,对于反右运动后的大跃进的大好形势,羡老先生是很保持一致的,是热烈欢呼的。而对于学术上的大跃进,他也是一个积极的歌颂者:
“……我所在的东语系,在短短的二十几天以内,已经编出了汉朝词典、朝鲜外来语词典、华日词典、越汉词典、乌尔都汉语词典、印地汉语词典等等。这些词典,无论是从量的方面来看,还是从质的方面来看,都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羡老先生当时已经是著名的学术权威,他充分肯定了学术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他的肯定表明,大跃进真的在量上还是在质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几十年后,他老人家在回忆录里又一次说到大跃进。这时,他口气一转,似乎从来就不相信那些虚报的产量。对于学术的大跃进,对于他自己亲笔所写的学术大跃进“在量上和质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话,更是闭口不提,只字不提,仿佛那是别人写的,仿佛它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他在《我的心像一面镜子》中说到大跃进时说,“那时各地竞相弄虚作假,大放卫星,有人说,如果亩产几万斤,一亩地里光麦粒或稻谷就要铺得老厚,是完全不可信的。”他心安理得地批判起亩产几万斤是弄虚作假,是不可信的。在弄虚作假的大军中,有没有北大教授季老先生呢?令人遗憾的不是季老先生当年说了错话,而是一种毫无自我反思的心态,是永远表现出‘错误与我无关’的文过饰非的人生态度。有一次,他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 ”。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他到台湾参观胡适墓的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呢?为什么不足为外人道?是对当年参加批判胡适的大合唱的愧疚,还是紧跟伟大领袖战略步骤的欣慰?或是别的什么,他语焉不详。他所缺乏的,正是巴金老人、周扬老人那样解剖自己、正视自己的勇气。
在毛泽东时代极左潮流中走曲折的路,说一些错误的话,人们是容易谅解的。但是,季老先生的曲意奉承却会引起人们的厌恶。季先生是与时俱进着,在新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 2005年,温总理看望病床上的季羡林与钱学森。温家宝向钱学森说了一大堆成就,听了听人鼓舞。钱学森静静地听着,没有为总理所说的大好形势加温,他深刻地指出:中国恢复高考快30年了,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教授,我们现今是世界第一个博士大国,为什么出不了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为什么诺贝尔奖总与我们无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因为中国现今的大学越来越不像大学,我们的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没加引号,大意如此)。他还对中国的教育说,自己的成就与对艺术的爱好有关,艺术使自己思路开阔。现在流行的分数第一、偏科现象,不重视艺术教育,是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培育的。钱老说得多好啊,多肯切啊。中国需要的正是这样说真话实话的学者,而并不需要一个劲地唱颂歌的歌唱家。
然而,季先生却正是这样的歌唱家。当温家宝看望90多岁的季老先生的时候,先生说的是:“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身母亲,一个是精神母亲——伟大的党,并且要求将他的“两个母亲说”写进中小学教材,教育祖国的花朵。同样是年高的学者,一个是真诚地指出问题,一个则是与时俱进的紧跟,说着肉麻而于国无补的伟大的空话。事实是,正是这个母亲,把你和千百万好人关进牛棚;正是这个母亲,把林昭等北大最优秀的儿女送上断头台,给800个教授和学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将他们送进古拉格。你一个北大教授,怎么不想想这些人的命运,不想想反右、大跃进、文革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摧残,不想想天安门广场上青年的鲜血?季老先生如此紧跟,如此费心,党自然是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人不走红,让谁走红呢?小平同志有一个伟大的思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果不其然,他老人家让0。4%的高干子弟们占有了全国70%的财富,比美国人5%的人占有全国60%的财富更胜一筹。中国在财富的集中性中第一次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超过了老美。同样地,我们也要让一部份人先红起来。季老先生就是先富先红的兼富兼红的新型知识份子的代表。论财富,他老人家虽然以前比较清贫,这几年也积累了14件珍贵文物,其价值不是一个小数,以至尸骨未寒,就纷争蜂起。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垂垂老人,短短三十年间能挣上如此家业,是很不容易的。而他在这短短的一二十年中,也由一个普通的教授变成了“大师”、“ 泰斗”、“国宝”,真正是实现了大跃进、三级跳了。
作为一个垂垂老人,他本来早就应该安心养老。但是,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前不久,不惜以老迈之躯,大唱颂歌。2008年,他又一次热情地欧歌这个伟大的时代,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也许,季老先生又富又荣又贵,内心又和谐,因此,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就如贾府上的老祖宗、老爷、太太、小姐们,一点也不知道世道的艰难,一点也不知道柴米之贵。他那里知道,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劳保的4000万无地农民的生活有多么艰难?他那里知道,失去了儿子和女儿的天安门母亲的内心有多少痛苦?他那里知道,几十年来到北京上访的人们被驱赶、被捕捉、有的被强奸的心酸(2009.8.6南方周末就披露了安徽上访人员李蕊蕊被集中关押在北京聚源宾馆(实际上是简易房)内被看守强奸的事实)。季老先生还为当局提出了大兴孔学、促进和谐的好建议,还主张将孔学推广到世界。他说,“孔子是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好好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你看,季老先生为中国和谐还不够,还要在全世界提供尊孔,还要将和谐发展观推向世界。可惜,尽管孔子和谐论提了2000年,孔子先生还是莫名其妙地杀了少正卯,留下了不和谐的一笔。现代版的和谐论也提出多年,不过,云南的未成年的学生们仍然被有权者们奸淫,湖北一个小小开发办的干部仍然因为强奸邓玉娇而命丧黄泉,通钢几万产业工人仍然痛打了要让所有工人下岗的前来兼并的总经理,全国每年十万起群体事件还是此起彼伏。如果五四先辈们如鲁迅陈独秀听到季老先生尊孔的理论,也许会为当年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羞愧万分。可惜季老先生尊孔提得晚了,不然,当年的五四运动就不会发生了。
有一年的8月6日,温家宝为季羡林先生庆寿,称季先生“代表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精神和良知”。有些读者也居然写道,季先生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季先生是一个学者,也有较大专业成就,是一个普通的知识份子。他有值得令人尊敬的地方。但是,作为“大师”、“泰斗”、“国宝”,实在是言过其实;说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说他“代表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精神和良知”,也与他一生的行为相悖,真点莫名其妙。他只是一个紧跟潮流、(无论错误与否)紧跟时代口号的可怜的知识份子。代表时代精神和良知的人,只能属于那些对社会对时代有批判精神的人,属于那些真正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关心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人。而季先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也是不敢、不能做到这一点的。透过季先生暮年的好运,听着季先生所唱的一支又一支歌功颂德之歌,听着控制着的舆论对他唱的一支又一支小夜曲,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独立思考精神的贫乏,折射出中国社会理性精神的贫乏。许许多多根本不知道季先生的人,也跟着别人大师大师地乱嚷,为什么不做一个脑子清醒的国民呢?
综上所述,季先生的走红,主要地不在学问,不在年高,不在他那本肤浅的《回忆录》,而在于他的紧跟形势,“与时俱进”。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我相信,我认真总结的这条规律,如果推而广之,被千百万中国知识份子所掌握,所应用,中国一定可以涌现千百个大师,千百个泰斗。这个理论,已经被另外一些大师、一些向大师高峰攀登着的准大师们的命运所证实。如果不信,我们拭目以待。那些有志于充当大师的人们,请一定好好学习本文。如果你们真正当成了大师,请不要忘记阅读本研究所获得的心灵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