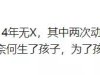经偷渡和相亲挑选来到福建,有人离开,有人因孩子留下,希望为孩子争取户口
在家乡她吃上了想念已久的咖喱饭。但这次自由回归终究变成了探亲,“妈妈也劝我,‘老公对你好就行了’。”更重要的,她想念不满半岁的儿子。
缅甸新娘,中国新郎。
在福建省宁德市的很多乡村,很多家庭的异国婚姻,没能拥有结婚证,他们把对婚姻的承诺留在婚纱照里。
团圆和林德武有两本婚纱册,一本拍在中国,一本拍在缅甸。林德武头上扎起了白围巾,团圆披上了粉红色的特敏(筒裙)。看起来像一对缅甸夫妻。
这是对团圆的安慰。虽然有一场缅甸婚礼,她仍希望有缅甸式婚纱的瞬间。
和她一样,很多缅甸新娘在婚前并没有想过自己的命运和生活,会和中国人联系在一起。她们对中国的印象大多是碎片化的,有的只知道影视剧里的李小龙和孙悟空,有的会觉得中国人很有钱。
来中国以前,这些颧骨稍高、皮肤略黑的年轻女子,穿着盖过脚踝的长裙,在山区或田间耕种,手上长满了老茧。
缅甸姑娘边境扎堆
边境村落有很多“点儿”:中国男人相亲,媒人找来有意向出嫁的缅甸姑娘。有时会有姑娘扎堆让人“挑选”
陈孝武双手合十,埋头许愿,他笑看着妻子喊雪和两个女儿,几人一起吹熄蜡烛。8月16日是他40岁生日宴。亲朋旧友面前,他说,因为有老婆孩子,他对生活充满感激。
在福建省宁德市漳湾镇,陈孝武曾是最着急成家的单身汉,也是最早娶缅甸媳妇的农民。
这媳妇娶得不容易。
陈家祖辈守田而居,6年前,村里同学的孩子都背着书包上小学了,34岁的陈孝武还在不停相亲。
有几次见面,人都不错,但一谈到七八万元的彩礼,这庄稼汉眼睛就直了。他全部积蓄只有三万多元,陈家三兄弟都到了婚龄,他是老大,不忍心管父母张口要钱。
心思不在耕田种菜上,陈孝武经常找邻村单身汉林德武借酒浇愁。30多岁的林德武开摩的,一天能赚几十块钱,相亲的姑娘们见他都摇头,嫌他家境不好。
“咋不娶个缅甸姑娘?云南那边很多漂亮的。”一位云南来的大姐给两个光棍出主意。
漂亮、花钱少、听说村里的穷人找过缅甸老婆,这些诱惑让人动心,俩人各揣上三万多块钱,结伴去云南。
七年前的云南瑞丽弄岛小镇,一元钱能点唱一首歌,陈孝武和林德武一晚上能用几十首伤感情歌打发不眠夜。白天,俩人在附近村庄转悠,也常趁人不备,从没把守的小路熘进缅甸的村庄。
边境村落有很多“点儿”:村民成了媒人,家里成了中介所。一有中国男人来相亲,媒人立刻找来有意向出嫁的缅甸姑娘。有时会有姑娘扎堆让人“挑选”。
辗转二三十个村庄,两人平均每天要相两三个姑娘。
在那里,陈孝武提高了条件——人要漂亮。“我长得不好看,再找个不好看的,生出的孩子就没法看了。”
林德武和一个叫团圆的缅甸姑娘好上了。团圆父母很看好这个外表斯文的中国青年,特意在缅甸老家办了十几桌酒席以示欢迎。
没过几天,瑞丽的一个村子,陈孝武遇见了喊雪。“(她)耐看,温顺,主要是眼睛很大。”小眼睛的陈孝武也找到了媳妇,他给了喊雪父母1万多元彩礼钱,把姑娘带出缅甸木姐那个四面环山的村子。
外来新娘的本地生活
缅甸媳妇吃的东西不会表达,用食指和拇指在脖子上比划,发出“嘎嘎”的叫声,要吃鸭子了
喊雪离开家乡时,只背着一小包衣服,初到福建的半个月她天天哭,说想家。但异乡夜晚的灯火通明,又让她新鲜和兴奋。
“这里有电,有电话、电视机。”喊雪说,在缅甸,村里没电,只能点蜡烛,什么也做不了。
嫁到漳湾头几个月,语言成了缅甸新娘最大的障碍。感冒了想挂吊瓶,就摸摸额头,再用食指在手腕上戳,陈孝武才明白。
缅甸媳妇米拉刚到村里时,吃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用食指和拇指在脖子上比划,发出“嘎嘎”的叫声,老公知道这是要吃鸭子了。
如今,29岁的喊雪已经能流利地说出当地方言。可6年了,团圆仍然徘徊在当地的语言体系之外。
当丈夫向记者自我介绍叫林德武时,团圆瞪大了眼睛:“你不是叫孝林(音)吗?大家都叫你孝林。”“不是啦,林是我的姓。”林德武有点尴尬,妻子不明白大家通常称唿的“小林”,“小”字是前缀。
但这并不影响她们家庭主妇的生活,虽然身体的黑瘦是抹不去的痕迹,但喊雪和团圆不用像在缅甸那样,顶着烈日爬山种花生、玉米。
即便攒不下钱,陈孝武和林德武也不需要老婆赚钱养家,只要他们回家有个女人,有孩子叫声妈就行。
每个周末,陈孝武都会带妻女去公园唱歌,现在已不是6年前唱《单身情歌》的心境,而是《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喊雪也跟着哼哼,她记不住歌词,但喜欢老公唱歌时的调调。
米拉更喜欢在中国做家庭主妇,“在缅甸,老婆做工赚钱,老公在家里,不干活,还打老婆。”她还说起姐姐,“姐姐不到40岁就当了奶奶,很辛苦的,要养一大家子。”
在漳湾镇南埕村,变化最大的莫过于陈玲玉。现在,邻居们都能说出她的体重——180斤。她笑笑,“刚来那会儿才130斤。”
陈玲玉其实至今吃不惯当地的饭菜,“这里的东西太清淡。”在陈家饭桌上,同样的猪肉、鱼、青菜,各有两份,一份是清汤的,另一份是红红的、麻辣的、炸得油脆焦黄的。
很多当地人知道,陈家对这个外来媳妇好。他们也知道,这个缅甸女人当初是被骗来的。
淘金陷阱
六七年前,南埕村有五六个以介绍工作为名义被骗来的缅甸女子,陈玲玉是唯一留下来的
5年前,陈玲玉和另外三名缅甸女子从仰光被带到福建,“他们(中间人)说这里工资高。”
一到福建,介绍工作的人就变了卦,让她找老公。随行的三个女子不见了,听说都被嫁给了当地人。“给我找了几个男的,我都不同意,又哭又闹。”陈玲玉回忆。
介绍人急了,“最后给你介绍一个,再不干就把你送走。”
几天后,一个肢体有残疾的青年出现在她面前。陈玲玉不敢再哭闹了。
这名男子叫陈兆明,时年28岁,小儿麻痹症让他的右小腿只有小臂粗细。靠经营一间10平方米、只有三排货架的小卖部为生。
像陈玲玉一样,2007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缅甸女子被带到宁德的偏远山村——几乎都是以介绍工作的名义被骗来的。
英文报纸《缅甸时报》今年1月7日报道,缅甸警方透露,2006年1月到2011年8月,缅甸共发生731起贩卖人口案,其中585起案件与中国有关,过去6年里,缅甸拐卖人口案80%的受害妇女均被卖往中国,被迫嫁给中国光棍。缅甸警方共解救1305人,其中从中国解救的有780人。
报道称,人贩子多以高薪工作诱惑,使这些贫穷、未受过教育的缅甸妇女抱着到中国淘金的梦想,结果落入非法婚姻的陷阱。
但当地人并不认为这是个陷阱:在一起是靠相亲,双方有选择权,并非男方强迫,况且他们也付出了金钱的代价。娶陈玲玉进门,陈兆明给了介绍人3万元。
当年,没人知道这个27岁姑娘的缅甸名字,嫁入陈家,婆婆给她取名陈玲玉,与夫同姓,意为此女视同己出。
这并没阻止陈玲玉逃跑的想法,可她没有钱,无处可投,人生地疏,“报警也没用”。
报警并非没用,据中国媒体报道:2012年12月,宁德蕉城警方从漳湾、洋中、虎贝、石后等地成功解救43名被拐卖的缅甸籍妇女,她们被送往大陆偏远山区,以2-3万元的价格卖作人妻。
警方介绍,她们均已在中国生活两年以上,都生子或怀孕,多数人均表示愿意留下。
六七年前,漳湾镇南埕村有五六个被骗来的缅甸女子,陈玲玉是唯一愿留下来的一个。出逃的念头在到来几个月之后打消,来时穿的衣服系不上扣,怀孕了。
今年8月,见陈玲玉时,她一身粉色碎花睡衣,一只胳膊杵在冰柜上。这位村口小卖部的老板娘每天6点多起床,做好饭菜,打开小店大门,店门前摆好铁靠椅,搀扶老公坐上,递货、找钱、记账,日复一日。
“跑的那些估计都是在缅甸还有家庭的,那边十五六岁就结婚。”陈兆明知道,陈玲玉在缅甸也有过家庭,还有个女儿,“那个丈夫死了,婆家不要她了。”听丈夫说着,陈玲玉点了点头。
对于这些缅甸新娘,一边是家,一边是家乡。不管是否被骗,总归可以做出选择。
落跑新娘
“外面的世界太大,恩雅变心了。”恩雅跑回缅甸,把孙家给她的金项链等都当了
生完孩子5个月,陈玲玉回了缅甸。临行前,婆婆给了她5000块钱,“回不回来,你自己决定吧。”
在家乡她吃上了想念已久的咖喱饭。但这次自由回归终究变成了探亲,“妈妈也劝我,‘老公对你好就行了’。”更重要的,她想念不满半岁的儿子。
对于团圆来说,缅甸已成了她和老公度假的好地方。前几年,俩人还想去云缅边境买块地,盖间房,可那里遍布开发商,根本没地可买。
并不是所有的缅甸新娘都安于异国。这半年来,孙华彬每天都在等着恩雅回来。
5年前,恩雅被带到福建,以为会找到高薪工作,后来却成了孙华彬的新娘。
晚上7点,漳湾镇兰田村的闷热没有消退,从工地回来,孙华彬躺在卧室床上吹电扇,墙上的婚纱照里,恩雅依偎在他肩头。现实中,他身高刚过1米5,勉强到老婆肩头。
邻居们仍记得恩雅进孙家门时的样子:黑得像炭,就俩眼珠是亮的;瘦成干了,裙子像裹在一堆柴火上。
为了让恩雅死心塌地留在孙家,全家人想方设法讨好她。
邻居们常从门口张望到,婆婆洗恩雅的衣服,恩雅刚坐到餐桌前,饭菜立马端上来;恩雅坐在床头数钱时满面笑颜,亲戚们就不断塞给她零花钱,往小猪存钱罐里投100个一元硬币;恩雅不会说汉语,孙华彬从工地请俩月假,买了台点读机,手把手地点着水果和动物的图案,教恩雅说汉语。
他很在意恩雅的感受,一次俩人开玩笑,他拍了下老婆的头,恩雅把脸沉下来。缅甸人忌讳他人用手触碰头部,孙华彬知道后,再没碰过恩雅的头。
这些没能挽回恩雅的心,她的电话多了,每晚至少半小时。说的都是缅甸话,家人一句也听不懂,“说是她哥哥。”孙华彬翻看她手机,一条英文短信,“我不会英语,但love还是认识的,还有一些心形图案。”
从前年开始,她回缅甸越发频繁,一年三次,借口去买电话卡都能离家出走,从不打声招唿。她也曾去莆田一家宾馆打工,回来时整个人都沉默。公婆给她几百元家用,她接过来就甩在一边,不像以前那样数上几遍。一次为女儿买牛奶,恩雅不肯出钱,“那是你的宝宝,你花钱。”
“外面的世界太大,恩雅变心了。”孙华彬和家人有种被骗的感觉。频繁往返缅甸福建,每次都要花1万多,恩雅就把孙家给她的金项链、金镯子、金戒指当了。
今年三月,恩雅再次出走,至今未归,音信全无。
俩人还有感情吗?孙华彬说不出,“至少以前出走后,她会哭着打电话给我”,她把这当家吗?孙华彬也不知道。街坊们说,这里更像她的客栈。还会接她回来吗?孙华彬想了想,又笑了笑,“我在等她电话。”
难求的身份
“孩子一出生,医院连出生证明都不给开。”米拉说,孩子落户也成了难题,从小学开始就有可能被拒之门外
恩雅的电话终究没来,孙华彬后来打听到,老婆是和陈玲玉一同回缅甸的,走前告诉了喊雪。
家毕竟不是故乡,留下来的缅甸女人们,相互间形成一个小圈子,知道有谁嫁过来,总是尽量要来电话号码。即便是最开朗的喊雪也说,“交不到当地的好姐妹。”也只有在聚会时,她们才能找到在家乡交流的感觉。
在漳湾,六七年前嫁过来的缅甸女人几乎都是非法入境,自然没有护照,“也不知道去哪儿办。”
米拉保留着一份4A纸大小的在缅甸老家的户口页,还有一张套着塑料壳的粉色缅甸身份证,可没人能读懂上面的缅语。
自从嫁到当地,警察有来做笔录,她们结婚生子后也得到了村镇等基层政府的默认,得以继续留下来。
对于未来,缅甸女人们大多没有规划,她们更多地把话题和希望集中在孩子身上,“孩子好不好?户口办下来没有?”
孩子的户口是缅甸妈妈们最大的牵挂。“偷渡”让她们在中国成了“黑户”,不能和丈夫领结婚证,孩子的户口也成了难题。包括米拉在内的三位缅甸媳妇,5个孩子中,最大的6岁,最小的2岁多,都还没有户口。
“孩子一出生,医院连出生证明都不给开。”米拉说,孩子落户也成了难题,从小学开始就有可能被拒之门外。
米拉所在的穆阳乡派出所所长介绍,以前没遇到这种情况,需要米拉和孩子做亲子鉴定,当地警察要做调查,村里也须开具相关证明。获得身份认证是个漫长的过程,米拉和老公雷荣枝一次次地办,她不希望孩子没学上。
孩子上学是她改变一切的希望。
在缅甸,米拉只上过幼儿园,1到10的英文读写她至今记得,每天,她都重复地教4岁的女儿这10个数字。“两个孩子能上学读书就有文化,有文化就好挣钱。”
挣钱对她来说很重要。米拉在村子几乎不出门,她甚至不知道村委会在哪里。她希望能够有机会出门挣些钱,让孩子脱离她曾经的贫困,也让她摆脱这深深的寂寞。
(应当事人要求,部分人物为化名)
前言
异国不是他乡
异国新娘常常会让人有浪漫的想象。
截然不同的文化,因为婚姻而融合在一起。这其中的碰撞、妥协,连同爱情的包容,让日常生活有了不一样的张力。
远嫁河南林州的越南姑娘阿垂说,“越南新娘对感情是真心的,不管吃多少苦都不会放弃”。她与丈夫在边境相识,来到大陆,面对很多的格格不入,她依然愿意依赖于真心的情感。
异国婚姻背后有爱情和温暖,但也有金钱、欺骗和无可奈何。
有的婚姻之所以发生是对贫穷的躲避,中国的富裕是两个人结合的底子。富裕意味着另一种生活。缅甸新娘喊雪离开晚上黑乎乎一片的缅甸村庄,来到了有电、有电话和电视机的福建村子。其实,对于她的中国丈夫陈孝武来说,娶了喊雪,也是对贫穷的避让。他实在不愿意倾家荡产娶一个女人。
有的婚姻是因为差异,不同的文化带来的陌生感和对方某种让人心动的特质。蒙古新娘琪琪格在大学里碰到了中国男人贺希格。贺希格说,他没有能力买房。琪琪格说为什么一定要有房子呢。琪琪格喜欢贺希格对婚姻的责任感。为了这份安心,她选择了他。
也有人是抱着新生活的希望被骗到了异国他乡,寄希望于命运的恩赐。就像福建的缅甸新娘陈玲玉。她被拐卖,她想过离开,却没有办法抗拒再也扣不上的扣子。新生命让她留下来,用夫家起的名字,安安稳稳地生活。
孩子是她们的希望。在中国,她们有了真正的亲人,也有了自己的诉求。为孩子争取身份,为孩子好好挣钱,让孩子好好读书。
本报记者分几路探访福建、河南、内蒙古等地,观察不同的异国新娘在中国的生活,揭示她们面临的种种冲突、困惑和逐渐融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