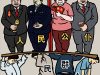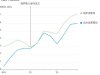第三章心理学分析
核心概念:1.肛门期被控与肛门期失控2.道德虚无主义3.情感控制、节奏感控制和音乐控制
肛门期是德国著名心理学家佛洛德提出的心理学概念,按照他的理论,幼儿的心理发展分为口腔期,肛门期和生殖器期大致三个阶段,其中肛门期牵涉到对幼儿的按规则去厕所的排便训练,从而从生理心理上建立最初的人的规训意识。孙隆基在其《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曾试图论断中国人“肛门期”失控从而不守秩序,有极大的以偏盖全,且部分分析脱离实际,并不准确。就中国大陆实际情况而言,城市里有教养的家庭对子女幼儿时期的厕所训练非常严格,并不存在孙隆基所说的“肛门期失控”。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也并不存在普遍的无规训。但是农村地区往往会有客观条件限制,就是厕所基础设施的落后。农村很多厕所,并不是城市家庭里的蹲式或坐便器式抽水马桶,而是粪坑或粪缸,这样的设计往往会给幼儿落下心理阴影。而幼儿一旦选择不去恐怖的粪缸而是在野外找地方”解决“,那么就客观上造成了孙隆基说的“肛门期失控”。笔者在此无意考究大陆城市和农村的厕所发展史,笔者要讨论的重点是中共有意设计的肛门期二次驯化。这个驯化跟孙隆基说的由于缺乏规训而导致的被动的“肛门期失控”的结果完全不一样,中共是主动同时驯化“肛门期被控”和“肛门期失控”的。这里体现了台湾人孙隆基对大陆的经验空白。
中共的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是大课堂,一个班有几十个人的那种,这种情况下它是不可能让小孩子随意去上厕所的。一般来说,学生只能忍着,忍到下课再去厕所。而多数“根正苗红”的学校,往往故意特别严酷的训练小孩要“憋著”。这一招是杀手锏,因为就中国大陆的食品安全状况来看,小孩子出现拉肚子很常见。而教师法西斯般的训练,往往会让小孩子憋到后来痛苦万分,但又由于被灌输的红色的“集体荣誉感”,个个都要做“邱少云”,宁可忍辱负重也要苦水自己吞。笔者就读的小学,曾不止一次出现低年级小学生大小便失禁的情况。也存在学生实在忍不住,在课堂上举手向老师乞求去上厕所的情况。但如果这么做的话学生是要有很大勇气的,既要有心理素质忍受同学的笑话和白眼(五六十人的课堂,全部学生都在听老师上课,这种请示会遭来集体的目光。并且,中共擅长搞建立革命崇高感的假大空教育,让小孩子觉得解大便解小便这种“小事”不值一提,这种“小事”都忍不了还怎么干革命“大事”。更要命的是,红色宗教渲染出来的脱离肉体的血色崇高感会让人潜意识里认为排泄以至于人的排泄器官本身就是“污秽不堪,见不得人”的事物,并因此产生自卑感。此外,“大家都忍你不忍”那么你就是“意志最不坚定的”。),又要表现出极大诚意赢得老师的同情以求批准。中共的学校极大程度在这个过程中驯化出学生高压忍耐之后对“被批准上厕所”的感激涕零,与中共擅长的“与领导交心”,“政治纠偏之后的感激涕零”的整人驯化和脑控同出一帜,并且,前者是为后者打下了生理学基础。
从全国来看,很多学生,尤其是小学生,“一遇考试就想上厕所”的情况非常普遍,这都是我上文描述的这种“肛门期被控”的后遗症。而就不同年代的人来看,50后60后“肛门期被控”的症状更加明显,要强于80后和90后。“肛门期被控”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肛门期失控”。忍了很久的学生们一下课往往一窝蜂冲向厕所,这种体验只要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都知道。笔者曾经读过最离谱的新闻是-居然有小学生纷纷涌向厕所因人数过多导致挤压死亡的。而中共的公共厕所设计往往特别缺德-它不是像西方那种单间封闭的坐便器设计,而是一条长沟,中间由半人高的瓷砖或隔板隔成一个一个的单元,使用厕所的人两脚分开蹲在或站在不同单元的沟上大便或小便-这对于大便的人尤其难堪而没有尊严,因为上端和一侧都没有遮挡,因而成了“公开展览”。有些条件稍好的学校会象征性的在一侧建半壁遮挡,但不改其基本结构。且不谈这种厕所结构卫生条件堪忧,其给人的羞耻感羞辱感是极其强烈的,很多小孩不敢在学校公共厕所大便。而在一些痞子学校,厕所则成了学生间进行霸凌的场所,比如有人会“撒尿过墙”凌虐解大便的容易被欺负的同学。中共公共厕所还有个特点就是恶臭,修建时间越早的厕所越是肮脏恶臭,甚至有粪便堆积如山的情况。笔者对话过很多人都有因童年体验过或见过过于肮脏的厕所而落下心理阴影的。(中国大陆90年代及以前还有一种公共厕所叫“旱厕”,是直接在地下下水道上端开一个口子变成供人蹲的坑,这种厕所不仅肮脏恶臭到令人作呕,而且让人蹲到目光所及深不见底的黑洞洞的下水道之上,可以让人内心恐怖到极点。)
学校公厕的恐怖把厕所与人的羞耻感、肮脏感、恐惧感、攻击性等种种消极情感和心理绑定了起来。再加上“集体开闸”的这种规训,共产党非常狡猾的为其搞政治运动时集体抗击或批斗“敌人”打下了生理心理学基础。共产党所煽动的很多极端仇恨,尤其是煽动一个集体狂热的仇恨,最初都是来源于生理上开垦小孩子的“肛门期被控”和“肛门期失控”。有外国人惊叹,中国政府或有政府后台的组织在发动一些年轻人集体性的狂热运动时(包括海外学联运动),究竟是如何一种力量把他们高度一致的组织起来的,并且都很投入不像是演戏。除了金钱利诱和我前文所说的“身体化集体”的极权控制之外,最初把那种“集体忍憋”和“集体排秽”深深植入他们潜意识的是对其自小到大的排泄管控驯化。笔者曾与西方研究前苏联极权主义的教授就此问题讨论过,其感叹中共的厕所模式与前苏联同出一辙,而在程度和种种细节上是比苏俄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大陆到了大学反而要教学生“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并非是因为小学没教过,而偏偏是因为小学驯化过度了,等学生到了大学之后出现萎缩式反弹。人从小时候的道德模范变成了长大后的道德虚无主义者。
很多大陆人一方面在中共各种集体会议上一声都不敢吭,即便领导犯了明显的错误也不敢发笑,而是全程表情严肃。而另一方面,一个群体中领导者笑,其他人再跟着笑(即便一点不好笑);领导者不笑其他人屁都不敢放,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大陆人过强的“自我规训”经常给人“机器人”的感觉,而另一方面,很多大陆人的不守秩序和“抢座位”“插队”又让人大跌眼境。大陆人的这些反应往往是下意识的,行为完全没从脑子过,一方面是来源于“身体化集体”的恐怖驯化,一定要争抢在前的等级避免落到“猫猫屁”被排挤整肃和牺牲掉,一方面是中小学时候“下课冲去上厕所抢坑”这种驯化造成的条件反射的长期投射。“肛门期被控”和“肛门期失控”的生理心理学驯化造成的影响,与“身体化集体”的集体恐怖相互配合,对中国大陆多数人的影响无处不在,几乎可以解释全部中国大陆很多人在国内和在海外的奇特行为。这些奇特行为,如果用素质解释的话,是忽视了他们行为根本不是由自己意识所控的巨大事实。(素质的前提是人是有意识的自由的实践其行为的。)正如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的分析,艾希曼压根不仇恨犹太人,一切对他“反犹”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而是他丧失了判断的能力,只管像机器人一样执行命令。阿伦特本人也因揭示了这个机制而在西方名噪一时,使她“罪恶的平庸”(也有译作“平庸的罪恶”的)的概念成为她研究极权主义的理论原创,并引出了她著名的教诲“思想之风的显现不是知识,而是辨别对错,辨别美丑的能力。”共产主义与法西斯同属极权主义,而共产主义造就平庸的机器人的模式比法西斯主义更具系统性也更加邪恶。
中国大陆很多学生也不太善于与人沟通,该说的话不说,有时碰到不合理的事情也能忍则忍,但另一方面有时候会因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突然爆发,这些都跟笔者分析的肛门期控制的“忍憋机制”有关。该上厕所时候不上,忍着,忍不住的时候就大小便失禁了。
道德虚无主义
中共的道德虚无主义是因为其早年道德理想主义走极端走崩溃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后果,充满了辩证法式的黑色幽默。
因为中共早期的宣传教育都是宣传“高大全”或雷锋式的榜样,都是“从不利己,专门利人”,刻意的把他人和自己对立起来,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共生关系,其结果就导致丧失了这套所谓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总是试图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专门利己,从不利人”。当下的中国社会崇拜“土豪”,把共产党当年“打土豪”的“土豪”从贬义变成褒义。共产党领导干部纷纷攀比自己有多少个情人,在海外有多少套房产,是把早年“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廉洁攀比掉头一转引向另一个极端。这套“逆向乌托邦”式的价值观让奉行它的人过得并不舒服。因为所谓“专门利已从不利人”和“专门利人从不利己”一样不可行,与早年觉得自己不够无私的共产党员的自责愧疚相反,当今的共产党员会因为别人间接“沾”了自己好处或自己“贪得还不够,搞的还不够”而觉得自己吃亏了,结果又导致捶胸顿足痛苦不堪,并要再与人斗把“搞回来”。
当一个社会拥有背景的特权阶层和富人们在实践了“反乌托邦”式的价值观后仍然获得不了幸福时,他们所能做的除了向社会炫富和滥用权力,还希望全社会的人都来信奉这套价值观,并且尽己所能摧毁美好事物,否定一切价值和伦理道德,否定人类本身的价值和尊严。这最终导致道德虚无主义。
拥有道德虚无主义价值观的人灵魂是飘着的,脾气古怪,情感起伏大,说变就变,行为自相矛盾,思维不连贯而眼神游离,很容易被任何一股外在的力量暂时潜入身体里而控制。
中共的特权阶层和中共社会下的土豪阶层人是极其精神分裂的,一方面土的要死,一方面什么都要最新的最时尚的;一方面什么都不懂,一方面什么都要最好的最顶级的;一方面是素质最差的,一方面又有做“红色贵族”情节。因为中共这些土豪祖上很多是小偷和妓女,因此这帮历史上最恶劣的边缘土匪们的后代们对传统秩序有一种逆反的心理。当他们将维权律师投入大牢安一个寻衅滋事罪名,并找一个文盲来当法官(最夸张的是,笔者读过法庭上法官当庭销毁证据并打律师的新闻);当他们将传统社会对大家闺秀“小姐”的尊称变为新时代党天下对妓女的称呼,并暗中系统性的逼良为娼的时候,他们心理上有一种言不由衷的快感。中共的这些土豪和官僚,一般性取向上都有罕见的重口味和性变态,而平时说话也不正常,笑点哭点与正常人也有较大差异。
而道德虚无主义最终是让人长期痛苦的,因此中共特权阶层的家属在长期承受这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后,有一些开始追求信仰,开始信“佛”或信“基督”,但由于他们骨子里受中共的腐蚀并没有痊愈,往往又信到歪门邪道的路上去了,笔者已在“伪佛教伪基督教”一节中叙述。而那些终日不思悔改也不试图从信仰中解脱的人最后要么自己走上绝路(飙车死,吸毒死,床上死,艾滋死,斗殴死等等),要么需要不断的从周围人的走上绝路里寻求毒瘾般的刺激感,庆幸自己还活着,但随之恐惧感又进一步加剧,并惶惶之中疑神疑鬼,开始不信神信鬼,不信自由信命。
情感控制
情感控制是一个全面而又系统化的工程。笔者前面说的肛门期控制毫无疑问是一个基本手法,但党的配合招数还有很多。共产党喜欢培养人的极端情感,并引导其宣泄的管道。共产党还喜欢在小学生年幼的时候给他们看“红岩展”,展览各种酷刑刑具让他们恐惧到极点。笔者幼年经历过学校组织的“渣滓洞白公馆酷刑展”,里面展出带血的竹签比人的手臂还长,又粗又尖。可以插到鼻子里的漏斗,据说是灌辣椒水用的。还有一段黑白视频,听到里面大叫,解说员说是人先被鞭子打得皮肤全部脱落了,然后用胶水加绷带缠好,像个木乃伊一样,最后用力一撕,肉就撕下来了看到血淋淋的心脏在里面跳。笔者的同班同学当时有当场吓尿的。在教育领域喜爱培养人的恐惧感,遗憾感,痛苦感,道德英雄主义和道德经验主义。(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面是非常反对在悲剧剧本里面填入令人恐惧、遗憾和道德崇高的东西的,因为这些东西不利于净化人的情感,杂糅而不干净,只会影响伟大悲剧的悲剧性,造成悲剧高潮的情感宣泄(emotionalcatharsis)不能达到。而关于道德英雄主义和道德经验主义,笔者将在哲学分析一章中详述。)
节奏感控制
共产党的讲话,尤其是领导讲话,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无聊无趣,感觉跟背书一样,新闻联播(字正腔圆的腔调)也是如此,各种会议和通稿也皆如此。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它说话不是先有内容再有结构的,而是先有结构再填内容。
中共任何讲话,任何稿子,其模版特质都太强烈了,都是开头结尾先用固定模版写好,全是啰嗦没用的废话和口号。中间内容都设定好排比句结构,顺序都不能搞错,都是先用中共版“word模版”把“全面推进……加强……深化……大力……同时……加速推进……更加深化……切实抓住……”等关键字摆好,中间留多少个空格都按模版先计划好,再往里面填东西。老百姓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中共讲话全部千篇一律,都差不多。那为什么这些这些差不多的讲话中共要一遍一遍天天讲呢?正如我已经指出,重要的不是讲话内容本身。重要的是新闻联播和尚念经式的排比腔调,和领导人三字一顿,一字一顿和四字一顿的节奏,目的是让在场的人意识情感被这种节奏感所控制并形成习惯,屏息凝神,连呼吸都跟着领导人腔调节奏的韵律走,就像部队随着军歌“一二一,一二一”前进一样。(把中共领导人的现场讲话和港台或美国领导人现场讲话一对比,可以感受到明显区别。)
自然而然的,中共的军乐也是对人节奏感控制的核心手段。从小做操做到大的大陆学生已经习惯了每天听解放军军歌等歌曲蜂拥著去操场,很多人长大以后一听到那些音乐仍然兴奋,下意识的想去走方队。在此我就且不论文革时期的忠字舞和当今的大妈广场舞了,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广场舞到今天还存在是大陆人的悲哀。
与节奏感相干的还有文字狱,就是中共的用词非常敏感,一个字都不能差,包括媒体用词,对领导人名排序等,2018年11月爆出陕西美术家协会召开会员大会的新闻稿因在叙述中写到“大会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收到1万五千元罚款,只因为多写了“总书记”三个字。类似的例子很多,但笔者的要点是,文字控制的背后最本质的还是节奏感控制。中共如果长期给老百姓驯化比如“XXX,XXX,XXXX,XXXX”的节奏习惯后,那么老百姓听到“XXX,XXX,XXXX”的时候就会自动做出“XXXX”的反应(打拍子的“嗒嗒”声),就跟驯化对狗摇铃的条件反射一样。尼采曾经专门研究过一个音乐情绪是怎样引发词曲作者创造诗歌音乐的灵感的,而西方的思想家无不认为绘画是空间的艺术,但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叔本华认为音乐是最能反应世界本质的;康得认为空间是直观外部事物的形式,时间不仅仅是直观自我的形式,更是直观外部世界的前提;海德格尔则直接说“存在就是时间”。中文本身音律特质就挺明显的,中共利用了这一点,再配合它有意设计的节奏和音乐,以及音乐般的文字,结果让老百姓像得了羊癫疯一样天天手舞足蹈,但只要中共闸门一关节奏感一停,老百姓又变机器人了。
音乐控制
中共的红色音乐最初都是受启发于苏俄的革命浪漫主义,但是中共的红色音乐往往不像俄共那么凄婉哀伤,而是更加具有宗教性,乐观向上而斗志昂扬,几乎可以匹敌西方的基督教音乐。像《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直接一上来就把老百姓心都唱融化掉了,一头磕到地上,对着太阳就起不来了;过了一会好不容易醒过来了,又突然被“地上的毛泽东”召唤起来在大地上开始扭秧歌了。而到了2000年《还珠格格》片头曲《自从有了你》则是把那种类似的宗教情感给世俗化爱情化了,消解了寄生虫似的拜毛狂热,功不可没。还有比如像《我的祖国》、《小小竹排江中游》等红歌艺术价值都很高,但掺入了很多有害的私货,终沦为精神鸦片。能消解苏俄式红歌毒性的解毒剂是德国作曲家舒曼、舒伯特、勃拉姆斯以及波兰作曲家维尼亚夫斯基等人的作品,而能消解带有民族情感和诗情画意的红歌的毒性的则是邓丽君的歌曲。当下新时期大陆流行歌曲则是良莠不齐,有些能反映作曲者的消极颓废或躁郁症式的情感,而另一些则黯然神伤,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中国大陆的音乐分析,笔者有空去写专门论文,在此不再发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