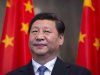本文提要:
认识论问题,是源于希腊的二元论哲学,Philosophy的基础问题,它也是近代文艺复兴后兴起的启蒙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问题。
大约五十年前,一九六九年,作为一个生下来就只知道马克思主义的高中生,我开始自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短短的几个月后,认识论问题就使得我开始走向反叛、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此后对于认识论问题的学习、探究贯穿了我前半生五十年在哲学领域,以及由此出发的对共产党问题、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为此,在二〇一九年我反叛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五十年之际,我希望用这篇文章做一个回顾性的总结。
与此同时,我也要强调,这篇文字不仅是个总结,而且也试图揭示我们正在面临的严重问题,以及我们的任务。我认为,明年是五四一百年,是彻底反省百年教训,寻找新的道路的时候了。
本文以认识论问题为中心记述了我进入认识论问题的经历,以及它和当代对于极权主义问题,思想问题的探究的关系。
文章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记叙的是认识论问题引导我产生反叛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彻底的进行批判性的反省。
第二部分记叙的是认识论问题在当代对于极权主义专制研究的三个领域中的作用:
1.哲学研究;
2.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
3.思想文化根源的研究中的作用。
第三部分概述了最近三十年的政治、社会现象及问题。
第四部分首先探究了为什么说认识论问题的探究依然是研究最近三十年,或者说这一百年问题的基础。然后强调为什么年轻的学生在读书以及研究时,首要的问题就要重视并且思索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2018.12.9
明年,二〇一九年是我插队、反叛,走向这条极权主义研究道路五十年。
从一九六九年夏季开始,“认识论”(epistemology)问题成为我反叛的起点,到现在整整走了五十年。认识论问题不仅是导引我反叛的起点,而且奠定了我反叛的基石,贯穿了我对于共产党、极权主义问题研究的整整五十年。为此,在别人纪念插队五十年之际,我特以此文记下自己的思想历程,为我这一代人提供另外一种不同的回忆及思索人生的参照文字,为仍然在共产党统治下,被共产党文化禁锢的青年人提供另外一条精神和思想之路。
一.五十年思想历程概括回顾
二十世纪被西方权威的自由主义学者称为是极权主义的世纪,有一亿以上的人死于极权主义的灾难。历史的变化发展也的确如此,极权主义问题从一九一七年,共产党在苏联掌握政权开始就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问题。
一百年来国际学界在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两方面:
第一,和思想研究紧密联系的哲学、历史研究,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
第二,和信仰、形而上学前提紧密联系的文化研究。
我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深切地感到受到共产党社会的欺骗,在六八年秋季决定自学哲学,六九年夏季后步入寻求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因此进入认识论问题、启蒙问题。在对于认识论、启蒙问题和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系问题的探究中,我在思想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彻底反叛出马克思主义,继而在七十年代初期把颠覆中国四九年后的知识界作为自己一生工作的责任及任务。为此,它使我从七十年代初期后孤独地走出我那一代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经历了各种风雨;最终到了本世纪初期,二〇〇三年,因为这个无法绕过的根本性的问题——认识论问题,在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争论后,我研究生时期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宣布彻底和我断绝关系。
本来我以为,这个认识论问题和极权主义专制思想及文化的关系问题,对于已经能够直接看到国际学界的文献的今天,早已经不是问题。但是,我却真的是没有料到,思想方法的根本变化,认识论问题在很多人那里,包括一些已经留学西方的年轻人,以及所谓八九民运的学运人士那里居然仍旧没有任何变化。为此,这让我感到,现在再描述一下启蒙、认识论问题在探究极权主义问题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我在这条路上的经历,对于中国下一代学人,甚至对于当前世界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世界居然仍旧没有从我当年所遇到的问题中,乃至可说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遇到的问题中走出去。
二.认识论问题引我走入哲学之门
1.五十年前的一九六八年底,我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开始自学哲学。在有限的马克思主义的读物,以及共产党所铸造的思想框架下,半年多后,在读到列宁的《哲学笔记》后,接触到列宁在文章中提到的马赫等人的只言片语,我通过对于现象、理论和人的感知及认知的质问,很快就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禁不住追问的教条。为此,从六九年夏季开始,我希望能够从这个追问中探寻更多的在哲学领域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九六九年冬季回到北京零星发现并且搜集到罗素的《哲学问题》、《心的分析》,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它引我进入了经验主义哲学。七〇年到七二年期间,我从废品回收站、王府井210号,琉璃厂内部书店,陆续收入了一些六十年代初期内部出版的,或者是供批判用的黄皮书,例如大约二十本的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集,以及一批科学哲学的著作,其中包括尼尔斯•波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续集》、玻姆的《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与机遇》,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以及赖辛巴赫的《科学哲学的兴起》、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辑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等。那时买到的也有萨特的《辨证理性批判》、《人道主义批判资料》、考茨基的《唯物史观》等书,但是在封闭年代,心智不全的时候,前述可怜的几本哲学翻译书籍居然能够引我步入经验主义哲学之路,并且让我为了读懂这些书籍所介绍的哲学问题而制定了自学计划,开始有目的地自学高等数学、物理和外语,现在想来,真的是庆幸自己的感觉及运气。
对于这段经历,说来现在人都很难相信的是,我第一次听到测不准原理,并且从而使我对现代物理学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科学哲学书籍,而是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计划时代》的翻译书,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劳文,谈的是经济问题,但是在该书谈到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对当代人的认识的影响,并且特别为此加了一个注释。这个注释让我如获至宝,立即抄写下来,反复看。它让我对现代物理学和人的认识的关系感到奇妙。就是这个注脚和所有前述那些科学哲学书籍,以及那时所了解到的一知半解的术语一起,让我决心一定要把大学理论物理学完,彻底掌握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以后的道路让我深感,这个直觉没有欺骗我,正是认识论问题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的根本的作用,在对抗各种教条及专制思想中的作用,让我在其后五十年的人生道路中,从感觉开始,越走气越壮,一直能够孤独地坚持到今天。
而正是由于我有了这个在黑暗中探究,处处遇到困扰、禁锢,甚至被窒息的经历,所以我深知,首先我这一代人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理由,例如下乡后疯狂的读马列,那是封闭和无知的结果,真理部教育的结果,不是让人可以吹嘘的光荣!再如晒书单,我是我那一代人晒书单的始作俑者,但是我在九零年谈到这点是因为想说明我那代人遭遇的封闭,以及我们是从哪里得到的真理部以外的影响。不料其后晒书单竟然成了我们那代人中的一些人的自诩。为此,在这里我要强调,在晒书单、说自己如何刻苦自学的时候,如果不能让人看到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可怜的时代,一个让人欲哭无泪,回想起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内心就流着血的时代,那真的就是歌颂脓疮艳若桃花。
其次也正是为此,我才在最近几年的文章中一再反复向年轻一代介绍“认识论”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在探究中我的遭遇。
我的经历让我深切地认识到:从真理部走出来,直接面对黑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如果你在认识问题的基础及方法上站稳了脚跟,找到基石,你就不会在这个对抗中,在黑暗里的孤独探索中,在共产党利用权力及意识形态建立的大厦前退缩。
集我五十年来和极权主义文化对抗的经历,我也发现,真理部及其子弟们的凶恶并没有比五十年前有所收敛和退却。为此,我感到有必要在此专门就我对于认识论问题和极权主义研究的关系问题,就我的部分经历来专门描述一下认识论问题对于认识极权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以及更广泛的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当然这也是对于真理部及其子弟们的直接抗击,对于那些至今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甚至依然对于启蒙及认识论问题的重要性提出质疑的人的回答。
2.黑暗中的我的西学之路
2.1.沿着启蒙主义学者的思想之路
我的思想觉悟过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你拒绝再使用周围人使用的语言,拒绝他们提出问题的方法及问题,你就会立即受到孤立及攻击。这个攻击,甚至可说是那类想要把你置之死地而后快性质的攻击,这种孤立伴随了我整个五十年。然而正是由于在我觉悟的时候,首先是从认识论上怀疑唯物主义专断、虚妄的主张——“人能够客观地认识世界”的时候,我几乎只是经过了非常短暂的迷茫,就发现了在西方思想史上存在的经验主义的痕迹,所以我很快就立住了脚跟,感到自己的想法可能不孤。
那是在六九年夏天,在我读列宁的《哲学笔记》的时候,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我马上发现,不谈结论对否,马赫是在针对人的认识能力提出问题、辨析问题,而列宁是在不加分析怀疑地批判、打棍子。
我从列宁的《哲学笔记》中的他对于马赫的关于感觉、认知、思维等问题的批判,第一次接触到经验主义(Empiricism)及经验主义者马赫(Ernst Mach)、贝克莱(George Berkeley)、洛克(John Locke)等对于这些基本的认识问题的探究。被列宁批判的马赫,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名字,他的思想,我虽然当时毫无了解,但是出于一个少年的直觉,它们立即激发出我的好奇,导引我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提出问题。
一,凭什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可以断言人能够正确地反映世界,凭什么可以把人的感觉绝对化,并且把人们的感官感觉到的现象不假分析证明地等同于世界。唯物主义没有让人信服的基础,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是一种专断!
二,既然世界是一分为二的,那么对立双方就没有谁好谁坏的问题。因为没有左就没有右,左右冷热没有谁好谁坏,谁必然地一定存在,谁要被消灭、克服。如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如此。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二元论的辩证法等于什么都没说!不过是一种诡辩!
……
如是众多的疑问,使得我从六九年秋季,模糊地开始了自己对认识论的探索及学习,为此我所固有的经验主义的气质被唤醒。紧接着,其后在政治上我也开始彻底看到共产党统治的残暴,走向了反叛。
在这条反叛的路上,追求的路上,我必须要说的是,一旦追随这一道光亮开始探索,此后就不断发现西方学者,前人和当代学者的著述,它们启发并且支持我走到了今天。作为一个在黑暗中的高中毕业生,令我尤其惊奇的是,几乎在每一程,在我的思想的每一个阶段,我都找到了西方学者曾经探寻过的痕迹,论述过的著述。
今天回过头来看六十年代末期那个荒诞的年代,凭着一个高中毕业生的感觉我能够摸索向前,我能够凭着嗅觉发现他们的著述及想法,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它们让我感到我走在了正确的、前人走过的路上。
这个过程也让我认识到,对于共产党及纳粹极权主义问题的出现的探索在过去一百年是思想界学界最重要的研究题目。而它之所以对西方学界重要,因为他们面对的现象及对手都是在他们自己的社会——西方社会中发生、发展的现实及人物。所以我必须要说的是,我陆续发表的绝大多数看法,都不是我的看法,都是西方学者提出并且论述过的看法,我只需要找到并且沿着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走下去。
迫使我十分谨慎地提出自己的想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孤独及封闭黑暗,所以在我感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面对周围无处不在的共产党社会的真理部所营造的框架及气氛,从来第一反应是诚惶诚恐,不敢轻易自信到放心地提出来,公开对抗周围的观点。因为这一切即如德国的物理史家赫尔曼(Armin Hermann)在《量子论初期史》中谈到上个世纪初,面对经典物理提出另一种想法的物理学家时说,你面前是一个大厦,你的批评稍不留心,就会被人指责为无知。对此,从七十年代中期一路走来,我有着深切的经验及体会。这让我进一步感到,我能够居然没有被真理部的知识分子们窒息而死,或中道而返,可说是一个奇迹。
事实上,这个过程就是在今天也没有成为过去式,因为我聚焦的是认识论问题,否认的是整个共产党社会的文化,它不仅包括思维方式,而且也有生活方式,知识界存在的合理性。而这就使得我即便是在海外,我也还是依然要面对被那个社会改造了的两代人的各类激烈的、甚至丧失理智的反应,包括谩骂、人身攻击。然而,这其实又一次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认识论问题的重要性,它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
说到此,我要说的是,在所有我谈过的看法中,所有关于认识论问题,对极权主义的具体认识,都来自于西方的学者,属于我的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现代欧洲及世界不是“现代社会”而是“后基督教社会”。布拉赫认为,过去一百年是意识形态的世纪,极权主义的世纪,而我认为称它为“后基督教社会”,能够提供更简单、广阔的参照及分析背景。
2.2.最重要的是启蒙和认识论问题
在这个依靠西方前辈学者的研究及支持的过程中,积我四十年来的探索经验,我所对读者不断强调的认识论问题,其实就是人们早已经关注的科学史家库恩曾经指出的:规范的转变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转变!
认识论问题强调及考察的是你认识问题的基础!规范的转变就是要你换一个头脑,换用另外一套语言及方法系统来看问题。不能够鸡同鸭讲,不能够风马牛,认识论问题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如果你读过《一九八四》的话,如果你在共产党社会中生活过的话,你就能够非常具体清楚地看到共产党、真理部所强力推行的一套规范。这个规范的前提是:有一个唯物主义,或者说物质主义的真理,共产党占有这个真理,有了这个前提,共产党主导下的对一切的解释和掌控才是合理、合法的。这就是共产党社会的以论带史、彻底地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思想及精神。
意识形态式的思维的特点必须,或者说观念论演绎出来的概念一定是二分法、非黑即白的,而这就是奥威尔说的,真理部创造了一套新话,新思维。
用这套新话、新思维人们已经不可能理解历史上的事物及思想本来的情景及意义。
拥有并且只允许一种话语及思维,这让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世俗的权力专制都没有自己的文化,只有共产党极权主义专制拥有自己的文化——党文化。这不仅是一个十分值得思索的思想及历史问题,而且这直接导致每个出生于那个社会中的人,如果要想使得自己的思想及精神正常,首先就是要从共产党那套新话、新思维中走出来。
如果你对这个新话和新思维是什么到今天还没有体会,即如果你生在共产党社会,而且读过《一九八四》依然不明白,或者没有感觉到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界、哲学界、知识界、文化界和真理部的血肉联系,没有感到你从语言到思维都必须改变,那我建议那些来攻击我、骂我的人还是三思后再来谈问题吧。而这其实就是我前文所说的,围绕认识论问题我和许良英先生争论了几乎三十年的原因。
2.3.由于认识论问题贯穿了我和许良英先生三十年的争论,因此在这里我要加一笔说明。
在对于启蒙及自由主义思想的认识和推崇上,在对于哲学、科学及认识论问题的认识上,在对于文化思想问题、传统问题的认知上,乃至在对于共产党的看法及态度上,我的思想和许良英先生从一九七五年第一次见面开始,就产生了全面地对抗。其后我虽然试图采取各种方法影响他,但是都没有用,为此导致二〇〇三年,他甚至突然宣布我们之间的关系彻底决裂,把我所谓革出师门。对于这个争论及对抗,在我八八年离开中国后到二〇〇三年我们的决裂,我们之间留下了几十万字的通信。这些通信都已经输入成计算机文字。笔者认为这个通信可说是一位启蒙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和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认识论问题讨论的典型案例,它甚至可说是一部具体的思想和历史性的教科书。
要了解这一思想争论的历史,在此,笔者还要向读者推荐二〇一七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许良英先生一生的战友范岱年先生的口述历史《行走在革命、科学与哲学的边缘》。这本书让笔者感到非常幸运,因为可能范岱年先生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它为笔者和许良英先生关于认识论以及其它一些基本的世纪性的各种思想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最翔实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历史背景,很多问题根本甚至毋须再去考证及回答了。
这本书让人们看到,中国自然辩证法界是由许良英先生及范岱年先生们直接参与创立的,一九四九年后,所有那些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大批判,包括文革中对于爱因斯坦的批判都始于他们这些人。尽管自然辩证法实际上是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属下的一个重要“部门”,但是自然辩证法既不是学术、也不是思想,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而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意识形态,一种世俗教义、教条,一种世俗神学。而我之所以使用“部门”而不是学科还因为它不折不扣地是一根党在政治上在知识界扫荡的工具,一根“世俗神棍”。他们这批人从来没有对此进行过根本性的,即对自己的认识论及方法论基础进行过彻底的反省和检讨。
为此,我相信,和他们那些人打过交道的朋友都会对这种“党棍”特性有所体会。这种不合常理的为人之道,“棍”性常常让一般人感到困惑。事实上,那正是真理部的人所具有的特色,它显示的绝对不是他们的诚实、勇敢。因为参与创立自然辩证法界的这批人,几乎每个人都是如此:在对待党的高层领导,对待他们觉得不可以顶撞的同僚,例如于光远们时,他们几乎都是毫无例外地媚态;只有对平民、亲友时,他们是祖师爷。人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不过是十分典型的真理部的人所天生的党棍特性。
关于自然辩证法,在经过了七十年代的反叛及各种知识的学习积累后,一九八六年笔者从对抗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开始,第一次公开在中国发表文章。这个对抗立即受到中国哲学界及范岱年们的排挤打击,两年后笔者只好游学到德国。在德国,我幸运地受到德国著名批判性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波普的学生和朋友汉斯·阿尔伯特的支持。他为笔者写的申请研究资助的推荐信中明确、清楚地点明“自然辩证法不是学术”!在哲学史、科学史上毫无影响及地位!但是它在共产党社会,在政治及文化思想上影响巨大,因此尽管在西方没有任何必要来研究及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在那个共产党地区,要想变化就必须来重新说明这个问题。坦率说,让笔者始料不及的是,在笔者离开中国大陆整整三十年后,中国知识界中竟然没有第二人来谈这个问题,年轻一代人中竟然没人起来对自然辩证法发出质疑。为此也可说中国知识界实际上是毫无变化的迹象。因为单只是范岱年先生回忆录的题目就能够说明这点,“行走在革命、科学与哲学的边缘”,是一个十足荒谬的题目!
从认识论角度说,革命、科学和哲学,其本身蕴含的一般意义就在西方知识领域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根本没有交界的边缘可谈。所以单只就何为革命,何谓科学,何为哲学,看来笔者在此生的学术探究中,封山之前还必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再谈自然辩证法不是学术,它是真理部缔造的世俗教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