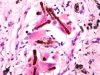中国女星袁立
1
下午四点四十,上海下着小雨,天色昏暗。还没有到吃饭时间,餐厅一个客人都没有。袁立进来了,扬声叫道:“杨语?”她的声音很清脆。前一天,电话里也是这样的声音:“杨语吗?你加一下我的微信,我告诉你地方。”没有助理,也没有经纪人。这是熟悉的面孔,也有过去角色的影子,杜小月,欧阳兰兰,《牟氏庄园》里的姜振帼。但这些都无法描绘现在的袁立。她穿黑色的皮衣,拉链拉到脖子,更像个职业女性。这提醒我她现在的身份:袁立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来餐厅之前,她刚在朋友圈发了救助的名单——基金会正在开年终总结会议。
这家餐厅在新天地,袁立的朋友说好吃,她来鉴定一下。袁立是出了名的喜欢美食,爱下厨,之前的电视采访中,她有几次被主持人要求露一手。此刻她迅速而认真地翻看菜单,点了几个菜。她给自己点了热红酒,“好的,加一根肉桂。”主菜点了羊肉,“有lamb吗?”她问服务生。她不时夹杂着上海话、英语,语气都相当坚定。
放下菜单,她看向我和同事,先提问道:“你们写这么多有人看吗?现在都看视频,谁还看文字啊?再说了,现在的人都关心那些东西,特热闹的事,谁关心这个(尘肺病)?”她向窗外偏一下头。餐厅外面,一家奢侈品品牌正在做活动,一群人穿着礼服围作一团,闪光灯闪个不停。
这些问题都很犀利。对于“热闹”和“寂寞”的对比,袁立应该是深有感触。明星里面,宣称关心公益的很多,真正投身其中的却极少,袁立是其中之一,而且,她非常具体地选择了尘肺病患者。这也成了她这些年最重要的身份。
所有人都会好奇,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尘肺病呢?袁立说,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她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位矿工推着矿车,矿工脸上都是煤灰,车虽是空的,他看起来却非常累。“像是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他身上”,照片透出的艰辛让她触动很大。她记不清是哪一年,却记得自己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看到了这张照片——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没多久,她又看到“开胸验肺”的新闻。2009年,河南省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为了证明自己得的是尘肺病,自己要求开胸验肺。这些新闻累积起来,让袁立很想做点什么,来帮助这些人,她便在微博上搜索公益组织,找到了“大爱清尘”,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尘肺病救助组织。
2015年6月,袁立跟着“大爱清尘”的志愿者,去陕西和湖北探访尘肺病患者。她跟志愿者一起,住县城的宾馆,上农村的旱厕,在村里的小买部吃方便面。第一天,她拒绝穿“大爱清尘”志愿者的T恤衫。后来,人手不够,袁立临时上场,当了志愿者。
回忆那次探访,袁立说,她看到了很多痛苦的人。她以前也见过农民,但是,她生长在杭州,杭州的农民很有钱,或是拿到拆迁补贴,或是卖很贵的茶叶,“就这样,我认识的几个茶农还很不满足,觉得自己钱还不够多”。在陕西和湖北,她看到的农民完全不一样,他们很苦很苦,又很憨厚。房子很破,家里有病人,但是他们要请志愿者们吃饭,拒绝收钱。袁立说,不是苦难,而是他们的真诚和乐观打动了她,“这个苦放我们身上我们可能就趴下了,你明白吗?”
从陕西回来,袁立接受了不少采访,一遍遍讲述尘肺病的状况。中国有多少尘肺病人?六百万——袁立甚至还能迅速说出湖南的某个村里有多少尘肺病人。尘肺病跟哪些职业有关?建筑工人,珠宝工人,矿工,一切会接触到粉尘的职业,大多数是农民工。尘肺病人的生活状态怎么样?许多人工作时没有签署劳动合同,索赔难,因为呼吸困难,晚上跪着睡觉,“跪着走向死亡”。还有人自己给自己漆棺材,袁立拉着他的手,安慰他,那人就哭了。
人生的苦难有很多种,但是尘肺病不同,袁立觉得,尘肺病是人为造成的,由于用工单位恶劣的条件,出了问题之后又不愿意负责,尤其是那些没有合同的农民工,“你不尊重他的生命,你把他看成最下面一等人是不是?他就是抹布是不是?”袁立说,“我觉得上帝造出来,他也是尊贵的人,不可以这样。”
2009年7月30日,河南新密市刘寨镇老寨村,张海超向记者展示自己做手术的伤口。2013年,张海超进行了肺移植手术,如今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2
菜上齐了,袁立双手交握,低头祷告。祷告完毕,才开始吃饭。
袁立招呼我们开动。我迟疑了一下,问她要不要拍照。“我现在吃饭都不能拍照,我甚至都不敢去旅游了,怕人家说我是不是拿了公益基金会的钱去吃去玩,”袁立说,“我觉得生活受到了严重的监督,好吓人。”
2014年,她从美国回来,开始关心公共话题,也和一些热心公共事务的媒体人相互转发。对她的赞誉和谩骂都很极端,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是很容易引起争议的公共人物。有时候很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攻击她。她很快地回答:“就是信仰吧。”她又说,“他们都说孙神棍已经被赶走了,就剩下一个袁神婆了。”
以前,袁立参加慈善晚宴,捐钱像是履行义务。她不在意钱最终去了哪里。后来,她开始有意识地在网上寻找公益组织。她捐助了一些组织,困惑也随之而来,甚至曾经发生过公开的争论。
“公益基金会里面,有一个现象是容易自义,就是我做好事情了,来崇拜我吧,我是领袖。我觉得不能因为你做了点好事情自义。做了就是做了。”袁立说。(作者注:自义是自以为义的意思,在基督徒的语言里,这被用来形容一个人在做了好事后产生的道德自满。)
2015年底,袁立在party上遇到一个律师朋友。她跟朋友聊起自己想做公益,又不知道怎么做,朋友告诉她,可以申请成立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只要两百万就够了。但是得抓紧,到2016年9月,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行,在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注册资金门槛将提升到800万元人民币。
2016的夏天,袁立开始注册基金会。那时她还住在杭州,基金会的注册地在上海。她不停地在杭州和上海两地之间往返,有时坐出租车,有时坐高铁。陌生的专业名词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她面前,“执行费”,“管理费”,“超过比例”。平时买菜从不点算找零的袁立,现在忽然要算募捐、管理费,工作人员的“五险一金”之间的比例关系。
夏天过完,那年11月14日,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注册资金两百万元人民币均来自袁立。她松了一口气。闲了半年,又接到民政局的询问:“你怎么还不开工?再不做你就要关门了。”
袁立很惊讶:“做公益还有任务?”她以为钱在基金会里放着就可以了,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原来《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也就是说,袁立得在2017年内把十六万元给花到尘肺病人身上。
这数额虽不大,但她要救助的尘肺病人都是农民工,得去乡下找到他们。她和工作人员先坐火车、飞机,转大巴或中巴,最后可能还要坐摩托车。到了尘肺病人家里,拿到他们的各种材料,查看他们的肺片、血动脉、抽血的动脉指数,还要联系医生鉴定,给病人发制氧机。有时他们忙活一周,找到的捐助对象却只有两个。
“我后来才知道,真的好痛苦,我真的没有想到,做志愿者去下乡和成立基金会,那真的是两个概念。”她说,成立基金会之前,她碰到李亚鹏。李亚鹏劝她:“千万别成立。”回想起来,袁立有些后悔,“他说得太简单了,我根本没往心里去,他如果跟我说得详细一点,我可能就要想一想了。”
除了工作的困难,基金会也会带来风险。注册之前,袁立原本想起名叫“施爱基金会”。但朋友说,这名字可能募不到钱,叫“袁立基金会”吧。用了自己的名字,袁立就紧张起来,她怕砸了自己名声,只能亲自上阵当理事长。“我可不相信人家”,她说,而且,她管就不需要工资,可以省下一笔行政费用。
当了两年基金会的理事长,她才知道基金会的操作有多难。质疑的声音时有出现。面对这些声音,袁立想到自己曾和很多质疑者一样,对公益完全不了解。现在她才知道,公益基金会的细节太多了,操作太复杂了,而大部分人很难了解这些细节。袁立的选择是,把基金会的报表做清楚,也就不解释那么多了。
袁立基金会的办公室在上海浦东的一栋办公楼内。办公室不大,朝南,有一个铁皮文件柜,两张沙发和四张办公桌。除此之外,就是随处可见的绿植,还有占了一整面墙的三幅地图。绿植,一张沙发,还有铁皮柜顶上的一幅装饰画,都是袁立从自己家里搬来的。另一条沙发则是对门办公室的旧物,“人家不要了,我们觉得挺好的。”
每天上午十点半,袁立到办公室上班。她的“工位”靠窗,桌上没有电脑,摆了一排基督教书籍。公益基金会的事务,无论大小,袁立都要亲自过问。“工作人员可能不是故意要出错,是不小心的。可是被人用‘放大镜’一看——你是在骗钱吧?”袁立说。
基金会有十个工作人员,会计,出纳和三位法务员工不常来,除了袁立,日常上班的还有三个年轻人。她们在办公室同袁立第一次见面时,建议袁立坐公交车。“这帮人太没眼力见了,”袁立说,“她们真的没有经历过演员,觉得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坐公交车,当然我也可以坐,也没有什么。但是有一些事情还是要稍微顾及一下,比如坐地铁、挤公共汽车。咱也不是说没钱,干吗要这样?而且公共汽车又慢,但是又觉得,别跟他们废话了,跟他们讲这个也太累了。”
无论如何,基金会坚持了下来。2018年,他们完成了合计2547964元的善款支出,给623名尘肺病患者的孩子付了学费,发放了215台制氧机,给34名尘肺病患者提供了医疗救助,给74名极为贫困的尘肺病患者提供了生活救助。这些救助对象大多集中在湖南。他们分散着居住在山村里,单靠工作人员挨家寻访,工作量实在太大。在过去的一年里,基金会在乡下和县城找志愿者,给他们培训,又通过志愿者找志愿者,终于在当地有了支小小的志愿者队伍。其中有的是一期尘肺病人,有的是尘肺病人的家属或遗属。袁立下一步的计划是,在四川建立志愿者队伍。为此,她特意买了一张四川省地图,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过去的一年,袁立几乎每个月都会下乡探访尘肺病农民。她说,农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基金会,他们以为袁立和工作人员是政府派来的。有些农民认出她,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称呼她“豆(杜)老师”。
我问她:“和第一次下乡的时候相比,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
袁立的回答让人有点意外,却也非常合理:“我只是有点麻木了。以前还觉得蛮心痛的,会拉着他们的手,后来我不怎么拉,我进去看,是什么问题,就跟工作人员说怎么做。再到下一家,越来越快了。”她停顿了一下,又说,“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痛苦都是一样的,没钱看病了,孩子没钱读书了,以前我不懂,现在我知道了,我想多看几家。”
“那你会担心自己自义吗?”我问。
“我们今年才做了两百五十万,你觉得有什么可自义的?”袁立说,“两百五十万是我拍戏的几分之一,有什么可自义的?”

袁立下乡时的工作照(图片来源:作者公众号/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提供,下同)。


3
2017年12月,袁立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她参加了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在节目中,她的行为毫无逻辑,前一分钟还好好站着,后一分钟就跳起舞来,突然,又毫无预兆地怼起评委。播出之后,很多观众说袁立神经病。袁立在新浪微博上发声,指出这是节目组剪辑的结果,并贴出了和剧组工作人员的对话。
袁立参加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
和袁立面对面谈话,你会相信她的说法。她精明干练,反应奇快,是典型的江南女性的形象。再谈起当时的那场风波,她说:“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让你去的时候是非常客气的。我好久没有上娱乐节目了,我不知道已经‘水已经这么深’了,那个水你看起来是很平,旁边插了一点塑料花,你会觉得挺美,你跨进去,一条鳄鱼把你腿咬出血来了。你真不知道底下有鳄鱼。”
“这事出来之后,您是不是觉得没法回到演艺圈了?”
“那不会。娱乐圈只不过是社会的缩影,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勾心斗角,有交换,有肮脏的东西。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够好,难道我要自杀吗?不,我还是会回去,但是你要更好地保护自己。”
“以后您还会再参与这种节目吗?”
“如果这个节目我看了还可以,如果它的价格也可以,为什么不参加?合同写清楚就好了。”袁立嘴角微微上挑了一下,看起来有点讽刺的意味。
但是,毕竟她已经不再年轻,在目前的影视环境里,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她也不喜欢现在的电视剧。她说,她的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她也不看现在的电视剧——“以前也不看”。那自己演的呢?“我以前演的戏我只看我的部分,别的快进。(自己演的)有时候也快进,但我觉得我演的戏还是蛮有质量的。”
袁立尤其讨厌宫斗戏。她说,换在以前,她绝对会演,而且会嫌角色写得不够狠,没有把对手干掉,现在可不会了,“你让我演我也不演”。
我问,那你希望演什么样的戏?
“我想拍有爱的,温暖的。反正宫斗我肯定不拍,我没兴趣。现在这个年龄,爱情题材我也没兴趣。”
前几天,袁立坐一辆出租车出门。路上,司机在看金马奖颁奖。袁立突然想到,自己其实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她也是一个演员。不可否认,她非常留恋红毯,“因为我是一个来自那里的人,我是听掌声和欢呼声来的”。相比之下,尘肺病人的救助工作太寂寞了。但是她又想,这些人上去领了一个奖,跟农民工有什么关系?跟尘肺病农民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而自己确确实实地帮助了尘肺病农民,帮助他们的孩子读高中,她觉得特别地扎实和温暖,“我觉得,我们的赏赐真的是在天上。”
晚餐结束了,菜还剩了一半。“这家餐厅也就一般,”她说,“我要发消息告诉我朋友,这家餐厅也就一般。”从餐厅出来,外面还在下毛毛雨,气温是上海初冬特有的阴冷。奢侈品品牌的活动似乎接近尾声,围着的人少了一些。袁立拉起大衣拉链,从人群里穿过,没有人认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