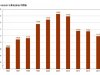从别处花钱买来孩子,再报假警称捡到弃婴,从而让买来的孩子能够顺利登记户口,让“收养”合法化。
靠着这样的方式,章兴(化名)刘雁(化名)夫妇顺利将买来的女婴“合法”收养。令人错愕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
9月中下旬,根据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湖北省建始县和江苏省常熟市,以咨询落户的领养人身份,暗访两户涉嫌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为违法收养的孩子办理落户的家庭——前者已顺利落户,后者已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案,等待出具“捡拾弃婴报案证明”,以完成整个上户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在我国,弃婴的收养及落户,涉及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及儿童福利机构三方,有明确的办理程序规定和收养政策。那么,违法买婴者如何通过合法渠道“洗白”襁褓婴孩身份?铤而走险的背后,又有何隐秘?记者调查发现,购买婴儿的家庭往往存在不孕不育或者其他一些原因,遂产生了收养孩童的需求;而贩卖婴儿者,多为原生家庭无力抚养或非婚生育等多种原因。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张善根认为,对无法生育,或失独等原因走上非法领养之路的家庭,国家相关部门需加强政策性保障和福利,但社会不该对这类所谓的“良性违法”采取包庇或纵容的态度。
“辅警亲戚给我走的正规程序,搞了个领养证”
章兴是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人,现年36岁,个头不高,体型微胖,黝黑的圆脸总是挂着笑容。他曾外出打工,机缘巧合认识了“北漂”十多年的刘雁。刘雁来自湖北恩施州建始县,是家中长女。2017年,两人结婚后,章兴把户口迁到女方家,并跟着刘雁在亲戚的服装厂上班。疫情之后,他又搞起了社区电商。
去年8月初,有个老乡来电话,说“有一个娃娃”。想都没想,他就回复“要”。章兴和妻子算了一笔账,治疗不孕症至少要花费十万至几十万不等,还不一定能治好。现成买个孩子,只需要花不到一半的钱。这两年,夫妻俩还去过武汉和恩施两地的福利院咨询领养事宜,但都失望而归。章兴说,“恩施福利院里一个孩子都没有,登记了,也排不上。”
老乡介绍的女娃,原生家庭有些复杂:父母双方均是离异者,两人同居但还未再婚,各自还育有多名儿女。章兴称,他们不要孩子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养不起”。
对方以“营养费”的名义,一开始要价6.6万元,但章兴算了算,前前后后共转账了近8万元。孩子出生第七天,他就和妻子去医院抱了回来。章兴说,为了防止孩子被要回去,他们请了当地最好的律师制定协议。厚厚一叠,像一本册子,双方签字并盖了手印。“当时我就明说,如果将来扯皮,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大不了就一起进去吃牢饭,他们卖孩子是犯法的。”
孩子皮肤白皙,有一双清澈透亮的大眼睛,像个洋娃娃,让夫妻俩很是喜欢,但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父母信息不匹配,孩子落不了户,让他们犯起愁来。
“后悔死了,在医院,(孩子)父亲(一栏)本来可以写我的名字,他们都说不用,现在看来难搞了。”去年10月21日,章兴在一个讨论“送养”婴儿相关问题的微信群里“冒泡”。和群友交流中,他透露,“我派出所有熟人,说不着急,会给我搞定”,“礼都送了,都是亲戚,可以说是自己屋的人”。
这两句话,引起了上官正义的注意。章兴此后向其坦言,“我亲戚给我走的正规程序,搞了个领养证。”
孩子落户的主要依据是医学出生证明(简称出生证),可以凭司法亲子鉴定结果补办。近年来,随着对开具出生证的监管的加强,通过以“捡拾弃婴”之名报假警,并以收养弃婴的方式上户,逐渐成为“洗白”孩子身份的一种新路径——而这种“合法化”的方式,给打拐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交流,章兴逐渐放下戒备,并开始在与上官正义的微信私聊中“直播”最新进展。今年7月13日,章兴发来消息,“已经登报了,要等两个月。”9月2日,章兴又说,“我刚刚回来,今天给女儿搞户口,走正规渠道太费劲了。”
9月10日傍晚,记者记者在建始县民政局附近见到了章兴。他刚开了80多公里山路,把负责评估收养条件的民政局工作人员送回县城。初次见面,章兴有些拘谨,但聊起给孩子上户,他逐渐打开了话匣子。他表示,“报假警”是民政局一个彭姓主任出的主意,而“派出所关系”指的是建始县公安局某派出所驻村的刘姓辅警,负责维持村里治安,三十多岁,“是刘雁的爷爷辈亲戚”。
11日上午,记者来到刘雁家,新修的两层楼房位于半山腰处,背山朝南,上下各有四个房间,门口晒着豆角和一些药材,与其他两户人家并排紧挨。章兴满头大汗赶回来,刘雁父母还留在山上忙着打理十几亩土地。推开仿红木大门,走进客厅的左侧第一个房间,刘雁独自抱着女儿偎在沙发上。她一米四十几的个头,皮肤白皙,体态丰腴。望着扑闪着大眼睛的女儿,刘雁一脸宠溺,洋溢着为人母的喜悦,“白天她爸还能抱一抱,一到晚上,就只黏着我”。孩子一岁多,她只带出门一两次,“就怕别人给我抱走了”。
章兴此前发来的“捡拾弃婴报案证明”上写着,孩子是去年8月15日凌晨2时许在自家屋后水沟处捡到的,但记者注意到,刘雁家的房子紧靠山体斜坡,坡上是一片玉米田,难以走近。“走形式来了一下。”章兴坦言,当天凌晨,他报警称“捡”到了孩子,在出警过程中,刘姓辅警“让人关了记录仪”,直接写了出警记录,盖完章就走了,“孩子丢在哪儿,都是他写的,我们只签了一个字”。出警结束后,接下来的笔录、失踪人口DNA对比等流程也“一路绿灯”。今年6月16日,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拾到女婴“情况属实”。
送记者到村口的路上,章兴接了一通电话,他语气轻快地说,“民政局昨天来过了,星期一应该就能办好,只差这一步了”。接下来的两天,章兴带着妻子往返于县城和乡镇补齐剩余材料,办出了收养证。9月14日傍晚,章兴发来消息,“户口上好了”。匆忙见了记者一面,他便和妻子赶回长阳县。
记者获取的一份报案证明显示,邻居徐老汉是事发当时的见证人。他告诉记者,他家的房子紧挨刘雁家,事发当时,他并未亲眼见到女婴被弃在刘家门前,直到次日刘家亲属抱着孩子到其家中借婴儿衣服,才被告知孩子是凌晨捡到的。孩子被丢在哪儿?他也说不清,“大概是丢在家门前吧。”他还表示,女婴被弃前,就已经在刘家住上了。
9月15日,记者记者来到建始县民政局,找到了章兴多次提到的彭姓主任,他是儿童及养老福利科的负责人。
一开始,记者以当地人的身份,询问如何将领养来的孩子合法化,他表示,“违反法律法规,涉及到买卖关系都不行。”聊了一会儿,见记者似乎有难言之隐,他示意可以去屋外谈。走到屋外的开阔处,彭主任点上烟,开门见山说道,“把你们的情况如实和我说”。当记者表示有一个买来的孩子,无法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能否通过“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上户,他犹豫了一下,说:“捡拾(的方式)很难,但你们能把那边弄好的话,也可以。”
他所说的“那边”,指的是基层公安部门。“孩子丢在哪儿,就找对应辖区派出所负责出警的人。”彭主任解释道,处理弃婴的收养问题,民政部门以公安机关的核查为准,在调取报案记录、失踪人口DNA对比结果等资料后,进入登报公示流程,“至少公示2个月”,接下来,核查收养人的犯罪记录、家庭收入情况、房产证明等情况,核查是否符合收养条件。
根据我国《收养法》要求,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三十周岁。章兴夫妇均满足以上条件。
当记者追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落户,彭主任表示,“只能报警,没有其他路了。”
章兴此前提到,从报案开始到上完户口,孩子都一直在家里。但根据2013年发布的《民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公告期满后,仍查找不到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需经主管民政部门审批后,办理正式进入儿童福利机构的手续。
对此,彭主任解释,疫情期间,福利机构内部采取封闭式管理,孩子均由符合收养条件的报案家庭暂时寄养。
建始县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院长詹顺国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福利机构以民政局审核后的材料为准,不单独做调研评估,“只负责盖章”,收养登记、评估及发证,都由民政局彭主任一人负责。对于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上户这一问题,他回复,“只要程序合法,符合收养条件,就可以办理”。
詹院长还表示,目前当地有数十户家庭登记领养,但一般而言,采取“谁捡到、谁领养”的方式处理,“自己找(孩子的)来源”。他直言,不少家庭是因为孩子上不了户口,才办理收养证,“有些孩子已经养了好几年了”。
也就是说,在弃婴的收养及上户所涉及到的三方机构中,公安机关是第一关,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关。根据章兴提供的信息及村里张贴的“民辅警联系牌”,记者拨通了刘姓民警的电话,但他否认与刘家相识,也不愿意作进一步沟通。
“宝宝在这样的原生家庭,实在太惨了”
去年12月,张芦依和上官正义在一个名为“缘分到了”的送养微信群里相识,彼时,她正急切地寻找送养人。
今年8月中旬,张芦依传来了好消息,说领到了一个三个多月大的女宝。为了给孩子上户,她也准备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我们跟派出所说好了,等那个接警员值班。”9月1日,她又发来消息,“昨天刚去派出所报案了,等出证明。”
9月16日,记者记者在常熟市一餐厅见到了张芦依。说起领养孩子的经历,她眉头皱成一团,开始大倒苦水。
她现年32岁,和丈夫都从事会计行业,经相亲介绍后,2014年结婚。婚后,一直与男方父母住在一起。二人世界虽潇洒,但在长辈的心里,没有孩子,始终是一个心结。张芦依说,每年过年,双方亲戚围在一起吃饭,都要提起孩子的事。有一天,张芦依母亲不经意说了一句,“我都怕到你家吃饭了”,深深刺痛了她。“关键又不是我们不愿意生了,也是没办法啊,反正外人是不会理解的。”她的话语里满是无奈。
她想过做试管,但怕风险太高,也想过去福利院登记,但身边的朋友亲戚都劝她放弃,“福利院里绝大多数都是有缺陷的孩子,没有人会白送健康的宝宝进福利院,确定不要就托人找买家。”
2016年,经介绍,张芦依认识了一位未婚先孕的高中生。一开始,双方谈好了价钱,但等张芦依夫妇赶到了医院,对方突然变卦,说要把孩子送给自家亲戚。“卖孩子的人会同时找很多下家,估计有人出了更高的价格吧。”对第一次失败,她始终有些耿耿于怀。
接下来的几年,托亲戚、朋友帮忙留意,搭上一些送养人,但领养之路始终不顺利。“每次问有没有,都说有有有,但后来都不了了之。”张芦依说,有个孕期9个多月的产妇,开始谈得好端端的,后来以感冒为借口,说把孩子打掉了。“谁信?现在没有孩子(的家庭)很多,孩子很抢手,就看谁出钱多呗。”
今年6月,张芦依的姑妈还在饭桌上提醒她,“有没有熟人,赶紧去领一个,没有孩子是不行的。”
8月初,在一次喜宴上,张芦依婆婆的朋友提到有个女娃。当时,这个孩子已经三个多月大了。为了避免再被对方放鸽子,经两方中间人沟通后,张芦依和丈夫商量,第二天就把孩子抱回来。
本来双方说好的是8万元,但接走的前一晚8点多,中间人通知她,“带好9万,孩子接走。”当天清晨7点多,张芦依和丈夫一行4人来到了送养人提供的地址,眼前的场景让她有些吃惊。
张芦依称,这是位于张家港的一个工厂宿舍,一家四口挤在不到5个平方的小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几乎没有别的家具。孩子刚刚洗完澡,躺在床上。旁边只有一个奶瓶、一个温水壶,还有一罐奶粉,“没见过的牌子”。
张芦依说,孩子的亲生父母均是外来打工人员,三十多岁。两人各自在老家有孩子,再婚后育有两个女儿,一个三岁多,张芦依领养的是老二。给完现金,张芦依让婆婆赶紧把孩子抱走。孩子的母亲本想收拾两件衣服让她带走,回头看到孩子不见了,只是淡淡说了句,“已经走啦”,就忙活别的事情去了。
“还好让我们抱走了,宝宝在这样的家庭,实在太惨了。”张芦依一边翻阅手机里女儿的照片,一边感慨道。
为了避免留下买卖孩子的证据,双方当时并未签署任何协议。但张芦依确信,对方不想要这个孩子,也找不到她,“电话地址一个没留”。
孩子到家后,亲戚们的闲言碎语消失了,家里的欢声笑语逐渐多了起来,丈夫充当奶爸,婆婆时常抱着孙女出门遛弯。张芦依则开始了报假警的计划。她透露,她的一个闺蜜也通过这个方式,帮孩子上了户,“现在虚岁6岁,都上中班了”。
巧的是,张芦依丈夫的堂兄池某,是常熟市某派出所的一名辅警。8月31日傍晚5点30分左右,在约定好的时间,张芦依称她直接抱着孩子走进派出所报案。张芦依的姑妈是“见证人”,3个值班民警和她一道指认现场。丈夫则留下来录口供,并表达了领养意愿,孩子直接代养在他们家里。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报完案,张芦依就准备好了登报公示所需的照片。闺蜜提醒她,等待派出所出具“捡拾弃婴报案证明”的同时,可以陆续办理民政部门所需的收养材料。张芦依表示,“派出所第一步是最关键的。接下来就是跟着步骤走,民政、福利院没有太大关系,最多走一年。”
9月17日中午,记者记者见到了张芦依丈夫的堂兄池某。当天他没上班,穿着一身休闲便装。当记者询问如何报假警上户,他表示,要先打听好所在城市的弃婴收养政策,接着寻找所在辖区派出所的人脉关系,如负责区域治安的社区民警。
“上户这个事急不来,孩子上学前都可以办,还是先去想办法找找关系吧。”他建议道。
“如果我假称拾到孩子,但发现不能指定让我收养这个孩子,那谁会冒如此大的风险,花钱买一个‘可能性’,还再去报假警呢?”张永将说。
其次,拐卖儿童是一个结果导向的犯罪行为,在调整与完善现行收养制度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买方的行政处罚力度。
在此前的交流过程中,前述建始县民政局彭主任向记者提起,之前有太多弃婴是因为只能生一个,生育政策放开后,捡到孩子的情况很少发生。去年,建始县当地发现一个弃婴,登报后,全国各地电话蜂拥而至,不少夫妻从外地赶来咨询领养事宜。他曾一天接到200多通电话,一直从上午9点打到晚上12点多,“手机打关机,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对比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15年-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孤儿50.2万人。这个数字逐年大幅递减,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孤儿19.3万人——同比减少了30.9万人。但五年间的全国办理收养登记件数总体而言浮动较小,除了2015年超过2万件,2016年至2020年,均超过1万件。稳定的收养需求始终存在。
“立法层面需要考虑实际情况。”结合多年在基层民政部门工作的经历,彭主任认为,可以适当修改,扩大收养人的范围,简化领养手续、降低收养门槛,提高领养成功率,出台更多的细则。
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会长、江西省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李云龙指出,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报假警一般处以刑事拘留和罚款,缺乏对买方的威慑力。如果将此类报假警案件与收买被拐卖儿童罪挂钩,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愿意冒风险的人就会少很多。
章兴说,接回孩子的当天,刘雁的爷爷塞给他500块钱,“连自己的亲孙女,都只给200块”。刘雁说,每个人爱孩子的方式不同,她会在自己的经济范围内,给予孩子最好的。张芦依说,这个孩子,像个小天使,让她相信了何为缘分。
“良好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其实是阻却违法犯罪的最佳利器,一味依赖法律高压来打击,难以真正化解儿童买卖的困局。”张善根说。
(文中张芦依、章兴、刘雁均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