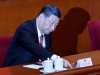1997年2月5日,新疆伊犁发生的使用军队镇压民众抗议事件。伊犁市的维吾尔人组织了一次非暴力抗议示威,呼吁停止对维吾尔人的宗教压迫和种族歧视;示威被血腥镇压,之后,大批参与示威的维吾尔人被中共当局抓捕。
1997年2月5日那一天,我正好在乌鲁木齐。1997年的穆斯林开斋节是在2月7日,汉人的春节好像也是2月7日。
到2月5日为止,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大家都在为过节做准备。当然,作为穆斯林,大多数的维吾尔人都正在封斋,耐心地等待开斋节。每一个维吾尔人家的女主人也都开始准备馓子、甜点,开始给儿女准备节日的新衣服和礼物。
2月5日那天,我们一位老同学请客,几个要好的大连工学院毕业老同学带着家眷,晚上8点按时来到了一位同学在南门的家。但一位在公安厅上班的同学没有来,房主人说,他答应一定来,可能耽搁了,要大家等一会儿。
等了半个多小时,快9点了,公安厅上班同学还是没有出现,大家决定先吃饭。饭也吃完了,他还是不见身影。大约10点多,公安厅上班的同学来了。出乎大家预料,平时西装革履的他,却穿着警服来了,而且一脸沉重。
寒暄过后,他坐了一会儿,似乎掂量了一下,然后对我们说:“伊犁出事了,出大事了。我不知道也不能说太多,事儿很大。载有北京领导的飞机已飞达伊犁,新疆军区已经调部队进入伊犁,兵团也已动员。我们都被要求日夜轮流值班,随时待命。为安全,我建议大家今天还是早点各回各家。”看他凝重的神色,我确信事情很大。当然,不用说,大家都明白出的大事必然和维吾尔人有关。
聚会的热情骤然消失,紧张和忧虑笼罩。我们大都在伊犁有亲人,出动军队、动员兵团意味着又一场对手无寸铁的维吾尔人的屠杀。
我们匆匆告别房主人来到街上,那天下着大雪,我和另一位同学站到路边挡出租车。一辆又一两,出租者司机减速探出头看一下我们,然后就加速离开。快半个小时,我们决定让女士和孩子挡出租车,一辆车停下来了,我和同学几乎是从路边冲到车前,快速拉开车门和家人钻进了车里,告诉司机我们要去的地方。汉人司机看看我们说:“今天我本来不拉维吾尔人,看你们像是受过教育的维吾尔人,我就拉一下你们吧。”
我有点不高兴,“为什么不拉维吾尔人?我们一样付你钱。”
“你不知道吗,伊犁的维吾尔人暴动了。伊犁一部分被你们的人占领了,听说乌鲁木齐机场附近也出现了武装的维吾尔人,要打过来了,维吾尔人又要杀汉灭回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伊犁的一部分被维吾尔人占领,被手无寸铁的维吾尔人占领,可能吗?乌鲁木齐飞机场出现武装维吾尔人,哪来的武器?可能吗?我不想和司机争论,也不想猜测传言。
本来我计划那一个寒假都呆在乌鲁木齐,和朋友们一起度过,但突然一切都变了,红色恐怖的气氛开始替代节日的气氛。乌鲁木齐也开始到处是军警,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报纸、广播、电视到处都是有关“分裂分子”在伊犁打砸抢的报道。我决定回家,带着孩子和家人回到了石河子。
到了石河子,似乎学校就在等着我们,学校通知全体老师返校参加学习。表面看,我们是在学习江泽民和王乐泉发表的无数个重要讲话,但很快我们就搞清楚了,这实际上是针对我们十来个维吾尔老师。我们被迫人人表态,义愤填膺地批判“分裂分子”。这,本来就令我心情郁闷,感觉特别窝囊,憋了一肚子的气没处发泄。
一天下午,又是学习党中央文件。台上书记在念江泽民的又一个重要讲话,什么“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分裂主义”等等。我身边一位姓陈的老师大概也是寂寞了,嬉皮笑脸对我说:“伊利夏提老师,听到了吗?危险是来自你们这些分离主义分子。”我一下子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大声说道:“毛泽东不是说过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要解放,民族要独立!’怎么维吾尔人就不能反抗一下吗?”整个会场大家都转过头看着我,那位陈老师低着头不敢看我。
书记看着我说:“怎么了伊利夏提老师,这是在开会,注意会场纪律。”我抢白到:“陈老师说分裂分子是我们维吾尔人,维吾尔人怎么了?这是维吾尔自治区!我们的权利被剥夺,还不能说话了吗?我不参加会议了,再见!”我越说越来劲,越说越激动。
说着走着,我气呼呼地走出了会场。来到操场,我遥望蓝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尽管有一种一吐为快的感觉,但也不无担心。我没有注意到校办主任是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的,他拍拍我的肩膀稍带威胁地说:“伊利夏提老师,陈老师不过是在和你开玩笑。你要注意,不要在会场闹事,你的职称评比会受到影响的,要考虑后果啊。对了,书记要我告诉你,他要你明天早上先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书记办公室。书记是一位老右派,上海人,他是从老师转到教务处当主任,再突然升为书记的,我们很熟。书记办公室门开着,我一出现,书记示意要我走进去。他先让我坐下,然后站起来把门关上了。
他看看我,一脸严肃地说道:“伊利夏提老师,我很尊重你,但你得管住自己,昨天你的做法非常不好,破坏了会议进程。你是破坏政治学习,知道有多严重吗?你必须写检查,陈老师也要写检查。”
他继续说道:“我本来也要找你谈话的,有老师也有学生反应,你在教室给学生讲无关课堂内容太多,谈民族问题太多,有政治问题。以后请你只讲相关课程,不谈民族问题,相信党中央政策。你应该知道,你的中级职称一直评议不过关,就是因为你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希望你三思而行,改变态度。”
我听出书记话里有话。我们教研室有一位姓赵的党员老师,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从北京被发配到奇台县,住在维吾尔人村庄,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改开”平反后,来我们学校担任汉语老师,给我担任班主任的民族班教汉语。她几次以听课名义,在我给学生讲地方史时出现在教室里,听到了我用维吾尔语嘲弄中国编造维吾尔历史的话语。当时,我就看出她很不满意,而且她也曾当着学生面和我争论,我都是一阵冷嘲热讽怼回去。
那时,我所在教研室主任是另一位上海老右派,对共产党嗤之以鼻。他曾有一天下班把我留下,关上办公室的门警告我:小心赵老师!他告诉我,在教工党员会议上,赵老师指责我民族情绪非常严重,经常给学生灌输分裂主义思想等等,是个思想不合格,不适合当老师的人,更不应该允许我给民族学生上课。
我猜到了,赵老师把状告到了书记这儿。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老师或学生。
我没有和书记争辩,只是点头表示在听。等他讲完,我问他是否可以离开?他似乎非常不满意,直视着我说道:“伊利夏提老师,我这是以校党委的名义警告你,你必须端正态度,虚心接受批评,学习党的政策,提高认识。否则,后果自负!”
那一年,我的中级职称又没有评上,工资也没有涨。优秀老师、先进工作者,我想都没有想过。看着别人拿职称、涨工资、评先进,尽管我尽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知道家里亲人也都觉得我活得窝囊。那些进步人士,则是觉得我不知好歹,不知感恩党国。
那年暑假,我回了一趟伊犁。2·5屠杀过后的伊犁一片萧杀,恐怖笼罩城市。维吾尔人人心惶惶,不知道那天晚上警察会冲进谁家,抓走谁家的孩子;走在街上,也是惊恐的眼睛看着持枪的警察,担心一不小心会被开枪射杀。
我长大的村子,年轻人也都大部分被抓走了,我上维吾尔小学时的同学有几个被判了重刑;我的一个表弟被酷刑折磨,几乎成了废人;远亲有两个被枪杀。我呆不住了,十天左右我就返回了石河子。
1997年的2月5日,改变了很多维吾尔人,尤其是那些体制内的维吾尔人,包括本人。第一次,中国政府以所谓“打砸抢”名义对维吾尔人的屠杀就发生在我身边,我认识的人、我的亲人、朋友被抓捕、判刑,被枪杀。
1997年的2月5日是维吾尔人近代历史上,又一个还在流血的伤疤。到底,中国军队、兵团打死了多少维吾尔人?抓捕了多少维吾尔年轻人?没有人知道。但伊犁的维吾尔人几乎每家,都有年轻人被抓走或被失踪。至今,还有很多伊犁的维吾尔人在等待那些被判重刑的儿女们能够回家,还有很多维吾尔父母在等待2月5日那天失踪的儿女。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