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1906.6—1977.4)是中共密战领域的杰出人物,早期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是上海密战系统的实际领导人,上海左翼联盟的创建者。潘具有坚定的革命理想,1935年8月他乘“东方红”号苏联货船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接受密战培训。期间,为将来一心从事革命,做了绝育手术。1937年9月,潘汉年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1955年4月3日,因“秘密接触冈村宁次和汪精卫”被判刑,1977年在软禁中病逝。
解放后,毛提出的经济建设政策经常不切中国实际,刘少奇因此威信快速上升。毛明地里提出“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暗地里却想借刘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历史问题整倒或控制刘,曾要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在伪满档案中查询少奇被捕的档案,同时高岗得到了主席的特别信任与快速提拔。如果高饶当年真的结成了反党联盟,作为与刘长期共事的同事下属,只要饶漱石出具一份刘少奇是叛徒的证明,也许当年倒台的并不是高饶,而是刘少奇。甚至再退一步,如果没有饶漱石抖落出毛的历史问题并执着质疑,有说不清楚的被捕出狱把柄在毛的手里,刘也会退缩,高岗可能会顺利取代刘的位置;而刘会象张闻天一样被逐渐边沿化。
1953年底,高岗受毛指使到东北敌伪档案中搜查刘的秘密记录(高派下属张秀山去查了);同时利用主席的支持和对少奇的不满,暗地串联阴谋取代刘的位置。此时刘少奇数十年的老部下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挺身,利用汪伪档案质疑潘汉年受毛指使在1939年与“冈村宁次和汪精卫秘密接触”的事情。(饶的妻子陆璀是刘的秘书。)
——1939年,斯大林为把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火引向西欧,引向英国,而与希特勒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局即把斯大林的此一重要动向通知了延安的中共高官,授意中共可与侵华日军卵翼下的南京汪伪政权打交道,从中套取情报,必要时联汪反蒋,实际上是联日反蒋。这是“马列主义”的灵活应用,毛于当年10月派最出色、最能干的情报大将潘汉年潜赴上海(内称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建立新的情报据点。毛嘱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可设法去和汪取得联系,并转达他的口头致意。具体协商内容不详,据1947年7月24日《时事公报》二版:“毛XX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民国三十年八月七日,……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这些由民国报纸披露的资料未必可信。但抗战期间日军从未进攻或轰炸过延安的原因一直让人不解。1953年饶漱石的质疑激辩、和1955年潘汉年检讨报告又印证了上述并非完全子虚乌有。
高岗本来是毛的亲信,串联活动也受毛的指使,可是在饶漱石跳出来抖落出陈年烂事后,毛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把高岗的行为定性为个人行为,把对党集体核心少奇的攻奸定性为“反党”。同时把饶漱石质疑也定性为“思想狭隘的”、“个人行为”,当然也是“反党”。戏剧性的是饶质疑毛莫名其妙的成了反毛反刘,把两个互为对手的人定性为一个“高饶反革命集团”来打倒。
本来大佬们借历史问题行政治攻奸没有潘汉年什么事,可是,1955年3月15日夜,潘汉年以上海市副市长的身份乘列车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4月2日,带着写好的材料去向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报告,报告检讨说饶漱石讲的“秘密接触冈村宁次和汪精卫”事情都属实,但辩解说这一秘密行为直接受命于毛。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安慰了潘几句,便匆匆将潘的交代材料亲自送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责成公安部秘密执行。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住处被公安部长罗瑞卿宣布实行逮捕审查。之后,他被带到公安部看守所功德林监狱,监狱管理人带潘汉年走进一间单人牢房,沉重的铁门打开后,潘汉年一看,房间有15平方米左右,一张单人沙发床,桌子及椅子,地上铺着地毯,墙角还有抽水马桶与洗脸池等,房里有暖气。
潘汉年的消失并没引起多大震动,因为潘汉年是被秘密逮捕的。当时,亲属和朋友都认为他又去执行什么特殊任务。潘汉年被打入死牢的惊世缘由:封存毛与汪精卫往来的历史。毛亲自下命“秘密逮捕”。潘汉年左右为难,讲受命于延安等于找死,说自行接触等于汉奸,好在只有公安部长罗瑞卿与他短暂交谈后,再没有人审问他,最高领袖的批示只是“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潘只好闭口。无期、软禁,为的是让潘封口。一直到1977年病逝,潘一直处于软禁隔离状态。相对于其他有历史问题的人物,软禁反而是一种保护,避免了在文革中受到冲击、避免了受基层造反派的追审。
潘汉年当时不知道陈毅对饶漱石存有刻骨仇恨,不知道陈毅痛恨刘少奇在陈毅、饶漱石之间刻意扶植饶,他的检讨报告不是转到了刘的手里而是毛的手里,更不知道这是毛刘角力掀起的史海钩沉,如果转到了刘的手里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
由于在高岗事件中,毛将为刘少奇两肋插刀的饶漱石一并处理,刘少奇保持了沉默没有施救,毛认为饶一定怨恨刘。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毛授意“中共中央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的人多次提审饶漱石,想从饶漱石嘴里得到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最有力的证据。因为饶漱石是中共党内第一个最早知道刘少奇被捕和释放经过的人。1967年6月1日,饶漱石为专案组写下了如下材料:
我是1929年到满洲(即东三省)担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之职的。当时刘少奇同志担任党的满洲省委书记。刘出狱不久即离开满洲。刘离开满洲后,我当代理党的满洲省委书记之职。关于刘少奇在满洲被捕亊件,因为时隔三十多年,详细情况无法回忆,我只记得他是因为到沈阳奉天纱厂等候工人党员谈话被敌人当作小偷而被捕的。因为敌人未得到刘的其他材料,故刘只在监狱住了十天左右即获释放。刘被释放后即到我家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我。当时我们对秘密工作都缺乏经验,故发生刘被捕后我仍未立即搬家和刘于被释放后即到我家的亊情。当时我对刘被捕释放事件过分信任刘的报告,故未作详细研究,当时党内已有个别同志因刘被释放亊件过于简单提出过意见的。现在,我认为我当时对刘过分信任的态度是有错误的,我认为今天把此事彻底审查清楚是完全必要的。(见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397页,陕西人民岀版)
这份材料,因不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而没有被专案组使用。反而为日后刘少奇平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3)原审查报告影射一九三○年四月满洲省委大破坏,是刘少奇同志“提供情报”的结果。这是蓄意歪曲历史。根据党的历史档案(一九三○年九月十八日中共满洲总行委第十二号《通知》)和敌伪档案(一九三四年日本大阪对支经济联盟编《苏联和满洲的共产运动》)、敌伪报刊(一九三○年五月一日《盛京时报》)记载,以及上述当时在满洲党、团省委工作的赵毅敏、杨一辰、王鹤寿等同志一致证明,这次大破坏,致使党、团省委领导人及党、团员三十余人被捕,是由于杜兰亭(当时在团省委工作)四月十二日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团省委机关的地址造成的(当时党、团省委负责同志正在那里开会,许多同志因而被捕)。当时刘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满洲去上海工作,这件事同他毫无关系。(4)刘少奇同志是在被捕半个多月后,统治阶级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取保释放的。据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补充材料”说:“对我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对刘少奇也是‘不予起评,取保释放’。”杨一辰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两次证明,当时对刘少奇同志判决“检察却下,不起诉处分,取保释放”。还有饶漱石(当时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等人,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明材料。”即上面的那份材料。
这充分说明,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恶劣的环境下,饶漱石没有落井下石,没有提供对刘少奇不利的证明材料。而当年与刘少奇被捕事件有关的人几乎都写下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只是后来都翻供了。可因与“反对刘少奇”有关而身陷囹圄的饶漱石却写下这份与众不同的证词,足见饶漱石的铮铮硬骨。刘少奇生前自然看不到这份材料。不知刘少奇的后人如果看到这份材料,会作何感想。
饶漱石和刘少奇曾多次在一起共亊,深得刘少奇的赏识。刘多次称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刘在快速晋升过程中,每次推荐的继任者都是饶漱石。饶漱石生前拒不承认自己和高岗结为反党联盟,拒不承认自己“全面反对刘少奇同志”。再三强调“少奇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拥护的”。恳请“党中央在这一点上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实际上饶漱石从一介书生快速提升到国家领导人的过程中,完全得益于刘的信任与提拔,感激都还来不及,怎么会反刘,但深夜质疑毛、借民族大义激辩3个多小时确是真的。
高岗、饶漱石是两个很少共事又分属毛、刘两个司令部的人,如果因高岗反刘、饶漱石质疑毛分别被定为“反党”也说得过去。戏剧性的居然一并定位“高饶反革命集团”,是一段典型的伪史。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感到刘少奇越来越难以驾驭,想借白区工作的历史问题整倒刘,是毛亲自要高岗去东北查刘少奇被捕的伪满档案,如果高饶当年真的结成了反党联盟,只要饶漱石出具一份刘少奇是叛徒的证明,也许当年倒台的并不是高饶,而是刘少奇。但由于毛出重手处理高岗,极大的迷惑了刘。毛抛弃高岗仍有大批人员可用;刘舍弃饶漱石,其系统仅剩彭真一人。由于刘被高岗事件迷惑,在打倒彭真的过程中迎合毛,刘在批彭大会上讲:“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当彭真被打倒后,刘的政府阵营再无铁杆兄弟。庐山会上当刘带头上岗上线的批判彭德怀时,预示着作为军委副主席的刘,也彻底失去了军队内的潜在支持者。被打倒是迟早的事。
罗瑞卿本来是毛阵营的人,但缺乏政治敏感性与刘走太近,又因为知道的事情太多,是否为了“封口”而被打倒,也未可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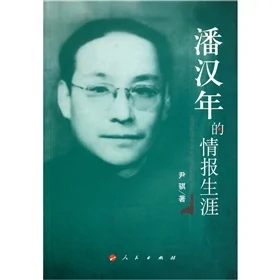
附录:潘汉年出生于书香门第,儒雅、潇洒。1931年参加中央特科,1935年8月他乘“东方红”号苏联货船痛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接受秘密谍战培训。在此期间,作为漂亮男谍,为将来一心从事革命方便,在苏联做绝育手术。下面文字选自《青春、革命与知识分子》作者:单世联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中国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但由于社会革命的对象之一是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传统伦理,由于革命动员以“解放”、“自由”为口号,因此对于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来说,革命也包含着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还有性自由的意义。1928年,曾志到湘南参加朱德领导的暴动。“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又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
革命意欲颠覆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系统对人性欲望的约束力,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性自由当作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岂止是知识青年,在闽西,少年先锋队在反封建、反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面作了大量宣传工作,“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头、童养媳,经过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纷纷起来反抗,投身革命。”后来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1925年由父母包办与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子结了婚后,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的终身寄托了。”
一些青年最初是冲着婚姻自由而参加革命的。胡也频在小说《同居》中这样描写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妇女们更快乐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像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好像是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适地同居起来。她们生下来的儿女也由‘公家’保育,不要自己担心。”这并不只是文学的虚构。直到1937、1938年,受斯诺《西行漫记》和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响,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对革命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时,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在延安也相当盛行,男女交往相当随意,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很有市场,甚至一些历尽艰辛的老干部也以“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为新生活的标志。
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为后,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大发脾气:“这还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男女都不分了,……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何舍鹅也许只是吓唬一下,但1930年江西“肃AB团”期间,就确有领导者认定AB团“利用婚姻绝对自由的口号,实行乱交及漫无限制和恋爱”,然后把自由恋爱或在两性关系上犯错误的同志,一律打顾AB团。
同样,“杯水主义”在延安也只是流行了一小段时期。1939年后,新型的革命等级制度开始建立并严格执行,此后流行的是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严格的男女关系是新社会的基本伦理之一,甚至是革命的基本要求之一。1968年5月19日,陶铸在中南区“文革”动员大会上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证据之一就是:“今年‘五一’节的夜晚,红场上有许多的男女青年,大跳摇摆舞,男的女的一块乱来,接吻,讨价还价。破裂的就一脚踢开。有的男女青年玩得好好的,突然男的把女的踢倒在地,简直是发疯了。苏联的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同我们更是鲜明的对比,我们到处是革命的新风尚,他们是腐烂透顶,令人作呕。”陶铸当时并不在红场,但不妨碍他说得绘声绘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