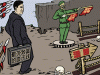1944年10月,卢作孚在北碚各界为他赴美出席国际通商会举行的欢送会上
给女儿的信
1952年1月20日,卢作孚给远在上海的小女儿国仪写了一封回信,国仪来信,说准备回家生孩子,征求父母意见。父亲的信是亲切的,说母亲将会为女儿照顾孩子,还说:
我所恳切告诉你的,是今后任何事情,都应照此次计划那样,有决定以前的从容思考和从容商讨,才能避免困陷在进退不得的境地,影响不仅及于工作而已。
似乎写信人的心情有些难以言说的东西。卢作孚对“困陷在进退不得的境地”有体会吧,以至反复地这样叮嘱心爱的小女儿。年轻的女儿万不会想到,这竟是父亲给她的最后一封信!
1952年1月27日,是这年的春节。这天,外地工作的孩子们没有回家过节。卢作孚本人也没在家过节,他到丰都去了,不久前民生公司的一只轮船“民恒”在丰都沉没,他去了事故现场。
1月28日,卢作孚乘飞机去北京“商讨要务”,30日即飞回重庆。
“华益,我对不起你!”
1952年2月5日下午,民生公司原业务处经理邓华益来到民国路20号卢作孚住所,与卢作孚做了一次长谈。
邓华益比卢作孚年长六岁,出身贫苦,由教会教育长大,年纪轻轻就做了英商白理洋行买办。1927年,在全国反帝高潮中,他买下白理洋行两只轮船成立自己的九江轮船公司,一跃而为重庆航业界老大。
当年民生公司要联合川江华资轮船公司,共同对抗强大的外资轮船公司的竞争,因各家华资公司互不信任疑虑重重而难以联合,邓华益以当时实力最强的九江轮船公司加盟民生公司,自己进民生担任航业部经理。这一举措,对重庆航业界“统一川江”的运动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邓华益主持的重庆轮船业同业公会,努力维护航业市场秩序,维护轮船公司的共同利益。公会尤其注意捍卫我国航权,抗战时期,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在川江营运,公会向政府呈请制止。抗战胜利以后,一些外国轮船公司在我国营运,公会代表轮船公司向政府提出,要求海关查处。1947年,中国民营轮船公司认为,“中美商约”侵犯中国轮船公司利益,同业公会出面反对中美商约签订,对此,当时的政府作出积极反应。
1949年4月6日,重庆市轮船业公会发出通电,吁请交战的两党政要,能够维护长江航运,给船员及其家属一条活路。在通电上署名的,是重庆轮船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邓华益。
邓华益这样一位在公司历史上的有功之臣,既为大股东,又是高级管理人才,重庆航业界的权威人物,在1951年3月28日,竟被民生公司以“年老体弱”为由“资遣”,邓家老小被勒令搬出民生新村。
当时民生公司的有功之臣,高级管理人员,受到迫害和凌辱的,还有相当一批。已被董事会任命为代总经理的郑璧成,重庆解放到不一个月就被扣押,虽保释出来,也不允许再在公司工作。更有民生公司第一条轮船“民生”轮的第一任经理、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在厂前江滩上被当众枪毙(陶在80年代“平反”),公司董事石荣廷也在镇反中被冤杀(石在80年代“平反”)。民生职工中被资遣,被管训者更多。
邓华益日后回忆道:从不送客出门的作孚将他送到门外,几次说:“华益,这些年来我对不起你!”沉重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五十余年后,卢作孚幼子卢国纶写道,“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这一天,民生公司的“民铎”轮在长寿附近失事。
含泪做检讨
1952年2月6日,上午八时半至十二时,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卢作孚第一次当众做检讨。
卢作孚的这个检讨,从记录看,是十分认真而严肃的。一开头就沉重地说,“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一句话未完竟落下泪来。
在这个检讨里,卢作孚简单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是一个知识分子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一生,他尽可能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来描述自己,表现了他与新政府的合作意识,也可理解为他已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他提到在川南办教育时,曾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共事,检查自己报国的道路选择曾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影响。卢作孚一生自奉甚薄,已为世所公认,可是却检讨自己,连生病住中央医院都以为太享受了。他对自己被视为资产阶级是难以接受的,不光因为在当时资产阶级已被视为可耻的另类,更因为卢作孚一生提倡“造公产,不造私产”。他似乎有些愧疚,又感到很大的委屈。他没有掩盖他的情绪——对郑璧成等一批懂航运懂船的管理干部被捕或被清洗的伤感与痛苦。在检讨的过程中,他数次流泪,甚至泣不成声。
在此之前,民生公司襄理以上的干部会,有公股代表参加,发言很集中,已将矛头指向卢作孚,说当前公司的困难和矛盾都是他造成的。有一种意见即是战后大量借外债是盲目扩张。这样重大的决策,关系到民生公司在中国二战后的大政方针,必须由董事会通过,公司高层管理,都是相当清楚的。当初,整个中国企业界都向往着抗战胜利后的大发展,利用外资发展生产,增设航线,是有远见的举措,大家都没有反对意见。现在,因为政治的原因,外债未能及时产生效益,反成负担,人们却把责任都推到卢作孚身上。
海损与亏损
这天下午,卢作孚去了“民铎”失事的现场。两年来,政治运动愈演愈剧,事故越来越多,据《民生公司史》统计,1950年至1952年8月,发生海损事故502件,死亡232人,大大超过了战争时期。后来公股代表张祥麟在向交通部的汇报中,说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前“事故平均每二天一次”,与这个统计大致相符。
航运企业家都是爱船极深的,有一次遇到海损沉船,一向沉着理性的卢作孚竟会在办公室里号啕大哭。
民生公司一向重视人的管理教育,长期以来不断总结改进,已有相当成熟的制度,卢作孚及一批高层管理干部,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实为首屈一指。更有年年的股东大会,必须要向股东们做出报告,并接受监事会的监察。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民生公司,在生产业务上,财务上,在安全航行上,不可能长期出现大的漏洞。
在全国性的大规模战争已结束的时候,民生公司却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事故和巨大的损失,到底是什么破坏了正常的管理秩序?为什么管理干部再不敢管理,是什么伤害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回到公司,卢作孚立刻找到负责财务清理的公股代表欧阳平,算公司二月份(疑为一月份)的收支情况。民生公司在整个1951年已损失339.7亿余元,在1952年一月只可能有更大的危机。
算过以后,卢作孚一掌击在桌上,叹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把门关了来搞‘三反’,搞了再开门!”
1950年3月,卢作孚通过民生公司驻京办事处主任何廼仁向周恩来提出公私合营,请求国家银行贷款的同时也制定了还款计划。计划只要民生公司生产正常,到1951年7月,便可开始偿还债务,当年可还700余亿元;计划1952年偿还1000余亿元欠款后,还有400余亿元的余额。以后按约分期偿还加拿大外债,同时为国家作出贡献。
然而,在民生公司执行公私合营过渡办法期间,不但还款计划成了泡影,还新增了800亿元债务。
1952年2月7日上午,卢作孚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去,见到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时至中午,和卢作孚一同来的胡子昂在机关门口等着他一起乘车回去,却久不见他出来,胡子昂便进去找他。有人告诉胡子昂,卢作孚先生和邓小平书记一起吃午饭呢。胡子昂就自己回去了。在饭桌上,卢作孚和邓小平会谈些什么呢?
在刚刚过去的1951年,民生公司人与生产的损失超过战争年代,公司危机越来越严重,卢作孚1950年8月即与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签订公私合营协议,至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尚未批准。
那时,中央财经委员会已决定,民生公司的民主改革不彻底,就不给贷款。民主改革即是清理敌人的政治运动,民生公司的民主改革不彻底,已被重庆新华日报点名批评。在新一波民主改革运动里,卢作孚被任命为民主改革委员会主任。卢作孚这时应该明白,他做这个主任,什么也决定不了,不过是要他出面表态,用他的口来宣布在公司里谁是敌人,谁是分子,以及对他们的处理。在他辞世以后,这个事情落到了童少生头上。以至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还不能原谅童少生。
公股代表“引火烧身”
1952年2月8日,这是卢作孚生命中最后的一天。
当年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张祥麟说,“三反”运动开始后,在公司大楼里走道的墙上,贴着一张一张的小字报,内容是质问公股代表为什么不下来,不到工人中间来?公股代表为什么没有贪污?他手指着自己说,就是不相信我没有贪污的意思嘛。
“有写卢作孚小字报的吗?”
“没有,没有提到卢作孚名字的。”他迟疑一下,又补充说,“也可能有,我没有看到。”
“卢作孚看小字报吗?”
“不知道。应该也看到了吧,因为他上下班总是要经过那里嘛。”
1952年2月8日上午,卢作孚经过贴了小字报的公司大楼走道,去参加公司召开的“‘三反’坦白检举大会”。“‘三反’坦白检举大会”,是档案中一份《关于卢自杀的报告》里的提法。张祥麟回忆,这个会是“三反”动员会,他在会上做检讨,也是做动员。我过去采访的一些老民生职工都认为,这个会是当时公司工会安排的,但从张祥麟的回忆来看,他本人是事先有准备的。他说,会上,有人上台向他提意见。除了发言人上台外,其余都坐在台下,卢作孚坐在台前一只沙发上。台上发言后,台下自由发言。这时,卢作孚的服务员,19岁的广东人关怀坐着提了几条意见。
关怀提的什么意见呢?
张祥麟回忆,“在北京,卢作孚住在东安市场一个楼里,我们去和他谈工作,谈事情,一起吃饭,吃烧饼,豆腐脑。关怀就是说的这个,但都没有提卢作孚的名字。这就是浪费。我就检讨,我说开会,比如股东会大请客是浪费。在北京还一起去洗澡,一起到万寿山逛了一回,和卢作孚一起去的。当时,卢作孚说,‘这些都记在我账上’,我也没有提他讲的这个话,只检讨说是公司浪费了。”
有回忆文章认为,关怀上台批判,是卢作孚至死重要原因。
张祥麟说:“那个服务员关怀嘛,他没有上台,他坐着提意见,大家都是坐着提的。关怀是从卢作孚家里搬出来了,还有什么就不知道了。那个会先是台上发言,然后叫大家提意见,大家讲时,关怀也讲,没有点卢作孚的名。卢作孚就在那坐着。公方代表就我和欧阳平在场。据我了解,散会以后,卢作孚还找了关怀,在办公室里讲他,我们花的自己的工资,有什么错误呀?”
关于这天上午的会议,卢作孚长子卢国维的描述是这样的。
“民生公司召开以市工会联合会和公司工会为主力的‘五反’动员大会,公股首席代表张祥林(原稿如此)(兼党委书记)作动员报告并进行所谓引火烧身,说自己跟随卢作孚去北京开会,还想请卢买一件皮大衣,虽然最终没说出口,但是差一点中了‘糖衣炮弹’。接着父亲的随身通讯员关怀一个箭步冲上台去,大声嚷着要揭发公股代表的‘受贿’行为。所举例证竟是前不久公股代表数人同总经理(即我父亲)一道去北京开董事会(私方董事居住北京者较多)期间,总经理(代表私方)请吃便饭、看京戏,同去理发代付钱。当时在场的同仁见父亲面色难看,知其心里毕竟难受。名为揭批‘索贿’、‘受贿’,人们自然会联系到‘行贿’。在‘群情激昂’的会场上,首席公股代表优柔寡断不知所措,散会后也没设法对当事人做好‘工作’,启发开导使其放心。全然忘记了中央确立的对民主人士的保护政策。”
会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卢作孚对关怀说,讲话要实事求是。这个年轻的服务员从广州过来专门照顾卢作孚,卢作孚关心他,教他学文化。让他做一些重要工作。就在这天早上,一直住在卢作孚家的关怀从家里搬出去了,现在,这个年轻人竟然当着他的面,当着大家的面这样不实事求是地“提意见”。卢国纶说关怀是“有恃而无恐”,关怀所恃为何呢?
张祥麟还对我们讲了这样一件往事。
张祥麟提出,要香港分公司为自己买一只杯子。(我一直没有搞懂,是什么杯子要到香港去买?)不久,香港分公司经理杨成质将杯子送到重庆,同时送上了账单。童少生问卢作孚:杯子是张代表要的,是不是送给他(不要张付钱)?卢作孚回答:你要送,人家要不要呢?最后,买杯子的钱是在张祥麟的工资里扣的。张说,“卢作孚这个人很会说话,不说送,也不说不送,而是反问童,‘人家要不要呢?’”这事是童少生后来告诉他的。
张祥麟现在对我们讲这事,是为了说明卢作孚不会行贿,还是要说明卢作孚滑头呢?他当年提出要买杯子却不先付钱,是想贪便宜,还是对卢作孚进行试探呢?
这位老人对卢作孚的态度是相当微妙的。五十五年前的那个会上,他用不存在的皮大衣来“引火”,是要“烧”谁的身?不论他是不是真有想要皮大衣的念头,却引出人家确有“糖衣炮弹”——以至自己差点中了“糖衣炮弹”的想象!可以肯定,如果那只杯子由公司赠送张代表,在1952年2月8日那天的三反动员会上,就会有一枚看得见的“糖衣炮弹”了。
昔日爱将形同陌路
会议结束以后,副总经理童少生也在办公室里,他没有和卢作孚说一句话。
当年,童少生继承哥哥童季达出面主持的美商捷江轮船公司,与民生公司是业务上的对手,他任董事长的国货介绍所的货物却必定交给华资的民生公司来运。卢作孚还常常到国货介绍所的朝会上去做讲演,宣传用国货,支持几位青年实业家的爱国义举。
国货介绍所成功了,捷江公司却在川江的竞争中倒闭了。卢作孚看重童少生的才能与爱国思想,请他加盟民生公司。童少生敬佩卢作孚,以为卢先生“作事认真有远见刻苦耐劳事业心重”,所以“一点也没考虑的就参加了民生公司”。
1943年,童少生即成为民生四个处务经理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1944年,卢作孚第一次到美国和加拿大,童少生即与之随行,并实现多年愿望,在美国学习航运管理。以后童少生又三次奉派赴美国、加拿大,参与了卢作孚在美国考察和在加拿大借款造船的决策和实施的全过程。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业务重心转向沿海,成立上海区公司,以后,卢作孚向董事会郑重推荐,任命童少生为上海区公司经理,公司副总经理。民生公司与金城银行合办太平洋轮船公司,童少生兼任太平洋轮船公司经理。在民生公司,人们将童少生视为卢作孚的爱将,前途无限。
少生此时已参加民主建国会,在前不久的一份自传上,他还表示了对卢作孚先生的敬佩之情,认为自己的做事为人深受卢先生影响。
但是现在,他俩同在一办公室里却形同陌路。
此时,卢作孚应该知道,童少生的轻慢与冷漠,已不是他一个人的态度。民生公司已被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弄到人心惶惶,劳资分裂,他一向引为自豪并努力维护的和谐奋进的公司灵魂已然消失。这个时候,卢作孚还惦记着轮船。下午,他在秘书课仔细地交代了民铎轮的施救办法。
致命的延误
傍晚,在回家的路上,卢作孚在离公司不远的小十字路口,遇见了郑璧成的女婿陈克。陈克记得很清楚,卢伯伯那天对他说了一句话:“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岳父。”郑璧成被迫离开民生公司以后,断绝收入,一直由卢作孚以个人收入接济。陈克当时没有意识到,卢伯伯是要陈克这个晚辈在今后代替自己照顾老友呢。
卢作孚回到家,天还没有黑,五岁的孙子卢晓雁觉得爷爷今天回家真早。
关于1952年2月8日晚上卢作孚家里发生的事情,卢国维的记述最为详细。
“当天下午母亲因去妇女互助会(成员多是工商业者家属)开会学习,会后又去菜园坝探望三弟一家。城里家中只有我们的五岁男孩以及厨工、保姆(亲戚)各一人。下午五时许,父亲由公司回家后叮嘱厨工、保姆说他很疲倦,需要好好睡一下,招呼孩子勿吵闹,也不要唤醒他。说完即进入卧室关上房门去睡了。傍晚母亲从三弟家回来,听说情况后问睡了多久,闻知约摸一个小时,就关照让他再睡一会儿。这样又过了半个多小时仍然没有动静,方觉得不对,立即去推门。这才发现里面给闩上了。同大家一起大声敲、喊也无反应,母亲紧张了,马上嘱厨工从窗口翻进去开门。母亲一行进房后见父亲仰卧床上,呼吸极度微弱。床头柜上有两个空小瓶,母亲一看就知道那是安眠药瓶,其中一个是平日为帮助睡眠用的,只盛有少数几片,另一瓶是深藏在一只衣箱里的。果然那只衣箱已打开,里面的衣物也翻乱了。这个急迫的检视过程只经历了一、两分钟。此时母亲一面关照保姆把两个孩子带出去,一面按捺着万分惊恐的心情自己叫电话到民生公司总经理室,请他们派人带医生来急救。差不多过了二十分钟,才见童少生带了一个公司职工医院的医生从距离不过一公里的总公司(医院就在公司大楼旁边)前来,却未见有救护车跟随。医生问明情况和按脉听诊后,只注射了两针强心针,实际上新近更名为市立二人民医院的仁济医院距离父母寓所(金城银行物业)不到两百米。该院有重庆市第一流的专科医生,设备也好,民生公司与其长期有特约关系,父母亲与该院几位老医生都熟识。童少生同这家医院也多有往还。但他明知母亲正处于惊惶失措、焦心如焚,自己完全拿不定主意的关头,却不考虑联系医院,只是望着公司的医生给父亲打针,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一再延误时机,让本来可以抢救过来的父亲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那样紧张的关头,为什么完全可以避免的致命的延误却不能避免?我采访过的好多人都如卢国维一样,认为是童少生的责任,甚至认为他是有意延误。直到采访了张祥麟,并看到相关档案后,我才感觉事情恐怕不是那样简单。
张祥麟回忆:
“上午(‘三反’坦白检举会上)我检讨,也是做三反动员,边动员边检讨。下面还有欧阳平(也要做检讨),午饭后,我就去动员欧阳平,做工作,叫他上去表态,检讨检讨嘛。他又是民主党派。我到他家里去了,在他家吃的晚饭。从欧阳平家里出来,回到民生大楼,就接到童少生电话,说卢先生出事了。我想卢先生能有什么事呀?就去他家里,看到卢先生躺在床上,旁边有一个瓶子,还有个医生。我问医生有没有办法。医生说没有脉搏了。我马上找陶琦,陶琦打电话给市委书记张霖之,张霖之也派来了医生,但是晚了,脉搏没有了。”
张祥麟说,当时,卢作孚的妹夫刘华屏也在现场。
这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是,卢作孚夫人蒙淑仪的判断——卢作孚服用了过量安眠药——没错。她的第一反应是往民生公司总经理室打电话。这时离卢作孚服安眠药已有一个小时以上,待童少生得知消息,公司已下班,他找到医生,然后一起到达民国路的卢作孚家。这个医生抢救措施无力,只注射了强心针。卢国纶回忆中说,在场还有一位护士,是护士提醒医生,卢先生服用了过量安眠药。童少生只是再给张祥麟打电话,等张祥麟从欧阳平家回到公司,接到童少生电话,然后赶到卢作孚家,已失去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后来有人对童少生提出质疑,在找到张祥麟之前,为什么不主张立即将卢作孚送往距离仅200米的仁济医院?眼见卢作孚的生命一点点流失,为什么童少生竟然不能基于常识果断做出一个简单的正确决定!
以童少生在新政府领导下生活的经验应该知道,卢作孚自杀,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他必须首先请示公股代表,公股代表张祥麟到场时,卢作孚还有生命迹象,在这以后的几十分钟里,张祥麟也没有想到要将生命垂危的卢作孚送到近在咫尺的医院抢救,而是忙着向并不懂得抢救,当时又很难立即找到的上级领导请示,然后静候市委书记从更远的地方派出自己的医生!真的是“优柔寡断不知所措”!
卢作孚停止呼吸了,蒙淑仪此时已知关怀当天在公司大会上的表现,深感悲愤,禁不住说了谴责关怀的话。童少生立即说:“你要站稳立场呵!”
童少生这话,也可以理解为是好心提醒蒙淑仪,由此也可知,童少生的所有表现,都是为了“站稳立场”。后来的事情表明,民生公司所有职工,甚至卢作孚的亲属及子女,都被要求“站稳立场”!
一份“关于卢自杀的报告”写道:“(卢作孚)二月八日晚六点服安眠药片,八点多家人发觉,十一点我们得知,正拟急行抢救,因服毒过重,十一点四十分自杀逝世。”
当年只有五岁的卢晓雁记得,那天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人他认得是民生公司的。有人把家里的箱子柜子都用纸条封起来。
遗嘱
2005年,卢作孚幼子卢国纶在公开的文章里写道:
“父亲留下的简单的遗嘱,是写给母亲的。遗嘱用钢笔写在一张毛边信纸上,字迹非常清晰。这张遗嘱,事后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亲眼见到这份遗嘱的,仅有包括母亲和我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当时我根据回忆记录了下来,这份遗嘱的内容是: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这里有必要对父亲的遗嘱逐条做一下说明。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指的是我们家1948年从南京搬回重庆,我二姐卢国仪主持搬家时,误将借用民生公司的两件旧家具一起搬了回来,当时我们家除这两件误搬回来的旧家具外,并没有其他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后二姐偶然得知此事,便在信中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在意这件事,特别于1952年1月20日,亦即去世的18天前,在写给我二姐的回信中首先提到此事:‘一月九日信接到。为南京破旧东西写信给罗昌扬,尚未得回信,正准备再去信。希望能得一确实内容,以便归还或赔偿’(罗昌扬为当时民生公司南京办事处主任)。父亲一生大公无私,两袖清风,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临终时仍记挂着借用公司的家具,特别首先叮嘱母亲一定归还。
‘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父亲在这里提到的股票,主要是指由民生公司董事会奖励给父亲的、从未参加过分红的一点干股。父亲去世后,母亲遵照父亲的嘱托,将此股票寄给了在武汉的民生公司董事会。但民生公司董事会按照国家政策没有接受,后又寄还给了母亲。
‘今后生活依靠儿女’,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职业,自然也没有收入。父亲虽然是著名的实业家,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而此时,我们兄妹已陆续就业,因此父亲才叮嘱母亲今后生活依靠儿女,为母亲以后的生活做了安排。”
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卢国伦写道,“这表现出父亲对自己所担任的政治职务负责任的态度。”
另一位知情的老人也对我谈到证章,他解释说:“还要退还证章,就是胸前戴的那种椭圆形证章,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时作出入证用。”
当时我说:“卢老先生想得很周到,是怕证章被他人使用吧?”
“是这样,但也是寒心哪。”
我有些惊讶,旋即明白,与这位八旬老人对视,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送行与痛哭
1952年2月9日上午,一年前就被民生公司除名的原民生公司人事部副主任周吾达正在牛奶公司上班,接到原来同事的一个电话:卢先生死了!周吾达惊恐不已,在办公室里,不敢表露出任何情绪。等到下班后,他绕到民国路卢作孚的家,看到门前冷冷清清,不像是办丧事的样子。他不敢进去了,也不敢在门前久留,便转身离去。走到附近的罗汉寺,他遇见一位民生公司职工。这位昔日同事对他说:“这个运动还要深入,卢作孚耍死狗不得行!”
卢作孚的遗体停放在民国路家里,没有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挽联。前来吊唁的人很少。民生公司的职工们大都如周吾达,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只能在心中为卢先生送行。
1952年2月9日下午,民生公司召开了董事会,董事们因卢作孚身后萧条,决定补助卢家1000万元(新币1000元)做丧葬费,这当然并不是特殊的照顾,与前些年去世的彭瑞成相比,这些补助是相当微薄的。
10日下午,民生公司举行课长以上的行政干部会议,与会者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余的人,包括童少生在内,均痛哭失声,以至民生公司党组织向上级汇报时,说这个会“变成一个哭丧会”。但是,后来所有的回忆录里,都听不见记入《内参》里的这些哭声!
新华社向北京反映情况的《内部参考》里特别提到童少生的哭。此一哭,很可能是童少生性情的最后表露,自此以后,他谨小慎微。后来,童少生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的左派,历任长航局副局长,四川交通厅厅长,四川省副省长,民建中央副主席。
卢国维写道:“民生公司原董事长郑东琴老先生(东翁)和一些高级职员都来悼念和安慰母亲。”
2月11日下午,卢作孚的棺木盖上了。这时,邓华益来了,还带来了他的儿子邓安澜。邓华益要求将棺木打开,命儿子跪下,待十二岁的邓安澜给卢伯伯磕完头,棺木重新合上。邓安澜很多年以后还记得,卢伯伯家气氛紧张,好多人很警惕地盯着他与父亲的一举一动,还不时耳语。
卢国纶回忆,“2月12日,是父亲出殡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关部门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队伍人数很多,灵柩从民国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龙门,再由父亲创办民生公司时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载运到南岸”。
对于这个细节,卢国维没有用“送葬”一词,他写的是,“灵柩运送去南岸民生村旁墓地安葬时,公司职工和船员数百人自发地排列在望龙门码头路旁目送,频频向家属点头、挥手招呼,望见他上了‘民生’轮船,渡过长江并到了南岸,直到看不见送灵队伍时才散去。”
卢国纪写的是:“当我们护送着灵柩到达长江边时,‘民生’轮的船员们默默地站在岸边和船头,照应着灵柩上船。渡江以后,又照应着灵柩下船,然后默默地站在船舷边,目送灵柩上岸远去。”
老民生人陈代六说,那时大家都想去送卢先生,就是去看看,没有人讲话,不敢讲。那么,就只能是“目送”,而且是“自发”的了。
民生轮在江面上默默驶往对岸,突然,江上有轮船拉响了汽笛,不知是哪一条轮船上的职工,自发地以这种方式为卢先生送行。顿时,蒙淑仪和孩子们热泪沾襟。
另一只轮船上的职工,竟自发地为卢作孚先生举行了追悼会!那是一只老式的钢壳小轮船,它的名字叫“生存”。
卢国伦的回忆中还说,“2月11日,我二哥卢国纪一家从北碚赶回重庆,其他兄姐或不及赶回,或尚不知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未能回来为父亲送行,至为遗憾。”
卢作孚长眠在长江边民生新村旁的小山岗上。三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大女儿国懿从海外回来为父亲扫墓,他的孙子卢晓雁和朋友们在那一带荒草丛中寻找,却难寻爷爷安息的墓园。又过了一些年后,人们在北碚为卢作孚捐资修墓立碑,不少如周吾达这样的老民生人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有了现在的作孚园。
《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