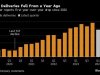大陆又起民变,涉及高层权斗,香港爱国蓝C鬼祟缩头,等待定性号令,不敢重复1989年64时押错注赵紫阳胜出而过早刊登“愤怒谴责屠城”之类的广告之愚蠢行为,“忠诚”处若学精了一点,“废物”指数若略降低,或可赏以一点掌声。
反而有深黄人士冷嘲热讽,“你们也有今天”,是另一种不成熟的躁动。不错,两年前大陆有大量大学生与小粉红大骂香港“黑暴”,支持警察严打“港独”,他们自己今日经受举国“动态清零”的封区钉仓报应,在某种程度或确令旁观者不无反讽的快意。最中国式黑色幽默之处,是三年之后,上天和习主席联手为“港独分子”报了仇。
不过私下片刻享受命运之神带来的Poetic Justice是一件事,对大陆各地的抗议者公然幸灾乐祸,是一种幼稚而过度的犬儒(childish and excessive cynicism)。
首先,并无证据显示当前十几个城市近百家大学为数众多的中国抗争者,两年前个个都谩骂过“港独黑暴”。或者其中有过,或者没有。即使有,他们处于资讯封闭的环境,即使今日终于自受现世的共业果报,由佛家俯瞰众生的超然角度,拈花微笑的会心怜悯,一定比拍掌称快的幸灾乐祸,境界更高。而境界,是一种小农社会无可攀升得的视野涵养。要证明你不属蓝C,不是仇恨蔽目的大妈低端人口,是高尚的少数,此时此刻,即使带一点创伤(trauma),你要强行显示一点高贵。
不错,西谚有云:“在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与中国俗话之“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在哲学的辩证层面,确实有令人迷惑之处。
但鲁迅对中国人陋劣民族性的概泛(generally)批判,不妨碍鲁迅对林语堂、胡适、郁达夫、章太炎、蔡元培等杰出的中国人在个人层面(individually)的交谊和欣赏,两者并无冲突。“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千夫”,是鲁迅鄙视大量愚昧而凶残的中国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孺子”,是鲁迅支持当时无辜而纯洁的中国青少年,甚至是农夫、工匠、在社会的底层被欺凌的穷人。
这两者之间,无论鲁迅、梁启超还是柏杨,其实都分得很清楚。在民国时代的读者市场之中,也很少人混淆。
因此,一听到“普通话”即生厌恶之情,甚至分不清是台湾国语还是星马的华语,会令一个香港“本土”人士陷入情绪的死胡同,甚至为孤独的仇恨绑架。Don't get me wrong:我承认,如果在巴黎米芝连Guy Savoy餐厅或伦敦的East India Club,忽然听到一桌喧哗的普通话,然后见到彼桌间有一堆Chanel包包,如果你觉得反感,你没有错。
大陆各城市发生的事情,你确实不必太过感情反应,即使内心极为感性澎湃,为了你自己的现实安全,至少暂时也要抑制,要学会喜怒不形于色。然而另诉极端,将普世价值观的人性当做仇敌,是不对的——it's dead wrong。
在某种时候,人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隔阂。但在时势转变之际,你会发现,不分地域、种族、文化,人之间有某种相同的契合。
罗马思想家塞奈卡(Seneca),生活在暴君尼禄的时代,面对凶险的逆境,他很能忍耐,也很冷静。塞尼卡说过一句话:“把我丢进一个狼圈里,我也能将狼群领回来。”(Throw me to the wolves and I will return leading the pack.)
不懂得此言的真谛,勿轻言政治,更不要沾惹什么“社运”,因为永远不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