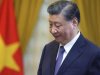拜读邹幸彤女士就“支联会拒交资料案”在法庭的自辩,这是我近年来读到最精采﹑最慷慨﹑也最雄辩的自辩文。邹幸彤不愧为律师,她从不同角度反驳政府的指控,以事实为根据,以严密的逻辑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主控官直逼到墙脚,置法官于无地自容之地。
支联会在一次数百万元的筹款中,收到一笔来自“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两万元“咁大把”的捐款,作为支联会六四纪念馆扩馆工程的众筹。政府根据这两万元捐款,再加上支联会与该“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都系因为六四而成立,再加上二者之间有相同目标,凭此三点,即宣告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
也就是说,因为支联会收了这两万元,便成为“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的代理人,这是正常人逻辑的推断吗?当然不是,这是“中共逻辑”的推断。
控方的理据荒谬至极。其一,两万元就想让香港支联会当它的“代理人”,捐款者有那么大的想头吗?控方至少应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对方曾指令支联会做一些事,而支联会也遵旨办理,这才有资格成为对方的代理人;其二,全世界有多少民间团体以“平反六四”为诉求,如果仅仅因为诉求相同,就成为其他团体的代理人,那支联会岂不是“好唔得闲”?其三,全世界反对专制独裁的团体数之不尽,仅仅因为目标相同,就要成为各种不同政治团体的代理人,那支联会如何运作?
支联会是百分之百香港市民的组织,由二百多个民间团体组合而成,会员大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日常运作由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常委会负责,其创会宗旨便是因六四而起的﹑对大陆民主运动的支持。支联会每年活动经费动辄七八百万元,已活跃了三十多年,其间举办无数活动,每年六四集会与示威游行,都得到广大市民包括游客在内的捐款,区区二万元捐款就使支联会变身为它的“代理人”,香港法庭已经沦落至此?
邹幸彤详述支联会的架构﹑历史﹑规模与决策机制,指斥强加“外国代理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妄顾事实与常理,违背思维逻辑的野蛮行径。
邹幸彤尖锐指出:“个逻辑似乎系只要将所有嘢归罪比外国势力,就可以抹杀任何诉求的正当性,可以盖过六四屠城的罪行,妖魔化追求民主的声音。”
邹幸彤以无可辨驳的证据,证明警方邓炳强与左媒早在案情正式审理之前,便未审先判地将罪名强加到支联会头上,“外国代理人”这项罪名,根本是为支联会“度身订做”。先有这个罪名,再去找证据,结果绞尽脑汁,也只找到区区二万元勉强可用,只好“夹硬嚟”。
邹幸彤指出,“合作并非从属”,即是不同团体有联系有合作,并不等于要听命于对方,不等于要由对方发号司令来开展活动,因此也绝对不是任何人的“代理人”,更不必说是“外国代理人”了。一个孩子吃了另一个孩子一颗糖,不会因此就叫他爸爸,这都是常识,可惜在中共与港共的逻辑里,一颗糖是有充份理由变成“爸爸”的。
以一间“三唔识七”的团体(邹幸彤以证据说明事实上与日本捐款者没有一丝一毫联系),一笔微不足道的捐款,裁赃支联会,硬套一项“外国代理人”的罪名,以此置支联会于死地,这便是特区政府秉承中共意旨明火执仗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样的控罪与审理过程,在以往香港普通法法庭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国安法之下的香港法庭的荒谬现象,是香港法治寿终正寝的明证。既然“外国代理人”的指控不成立,那么支联会拒交相关资料,便是义正词严的回应。以正义立场而拒绝配合,承担专制政府的迫害,这对邹幸彤与支联会诸君子来说,便是一种道义的选择。
邹幸彤说:“我们无法承诺天明,却能承诺同行,直到六四真相大白,刽子手面对审判的那天。直到一党专政终结,政治滥捕结束的那天,我们会一直坚持: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建设民主中国。”
千古道义在民间,历史是人民写的。今日在庭上受审的是邹幸彤们,来日香港人将在民主法庭上,审判这些加害邹幸彤们的政治打手。百年以下,没有人会记得法官主控官的名字,但邹幸彤的名字将光耀在香港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