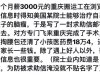《纽约邮报》专栏作家、《被偷走的青春》一书的作者卡罗尔‧马科维茨谈美国文化中出现的“苏联模式”,她呼吁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负责,抵制觉醒主义对家庭和价值观的破坏。(《思想领袖》提供)
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
卡罗尔‧马科维茨:这发生在一块红色的飞地,一个红色的小村庄,一座红色的小镇,一座红色的县城。就像……我需要这些人明白,这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
杨杰凯:《纽约邮报》专栏作家卡罗尔‧马科维茨(Karol Markowicz)曾自称是“纽约至上主义者”,她的一生都在纽约市度过,但在新冠疫情之后,她看到了美国文化中的苏联模式,于是举家迁往佛罗里达。
卡罗尔‧马科维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非常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自由的人也可能像独裁者一样行事,在一瞬间就把矛头对准他们的邻居。
杨杰凯:她与贝瑟妮‧曼德尔(Bethany Mandel)合写了《被偷走的青春:激进主义者如何抹杀纯真并洗脑一代人》(Stolen Youth: How Radicals Are Erasing Innocence and Indoctrinating a Generation)。
卡罗尔‧马科维茨:觉醒主义者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却能控制那么多的人,他们通过这种强迫性顺从来做到这一点。当我们把孩子们当作小大人时,我们就把自己所有的麻烦和问题都灌输给他们,这确实会让他们以后的生活变得一团糟。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一场更大的文化革命
杨杰凯:卡罗尔‧马科维茨,很高兴你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马科维茨:非常感谢你的邀请。
杨杰凯:我非常喜欢读你的书。我做过的很多采访,主题涉及觉醒意识形态,所谓的性别肯定治疗,围绕新冠肺炎的灾难性的疫情政策,类似的话题我自己有过很多的思考。而你把这一切都汇总到一本书里去,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么,请跟我讲讲你一开始看到了什么,所有这些事情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马科维茨:正是新冠肺炎让我了解了很多事情,我开始在我们的文化中发现一些模式,我认为这是一场更大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而这场革命正在美国发生。比如新冠疫情期间,不允许你讲出、说出你真实的想法,而你必须隐瞒你真实的意见以免受到所在社区或邻居的孤立,或者更糟,你可能会被解雇,等等。这让我想起了从自己家人那里听到的故事。我出生在苏联,我从我的父母、祖母那里听到的故事,好像突然以某种方式引起了我的共鸣,这种体验以前从未有过。我意识到美国文化中正在发生的、我感受到的事,与那些苏联发生过的故事非常相似。虽然我一直都有点不敢去想美国文化中可能有什么苏联的内容,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非常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自由的人也可能像独裁者一样行事,在一瞬间就把矛头对准他们的邻居。所以我和我的合著者贝瑟妮‧曼德尔开始讲述我们听到的故事。
当时我们没有一个总的主题,只是说一些不好的事发生在孩子们身上,对此我们需要说点什么。我们的书原标题是“让你的村庄远离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我们当时在写作时的想法。我们看到新冠肺炎暴露出很多不同的方式被用于对孩子们进行灌输,孩子们在我们的社会中受到了怎样的虐待,我们觉得必须说道说道。
我在书里也谈了很多苏联的情况。在苏联,孩子们被看作是革命的接班人,他们是前途光明、继往开来的一代人。对孩子下手并非偶然,让家庭破裂并非偶然。为了便于灌输,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与他们的父母分开。即使在像苏联这样的地方,那些人也不得不为自己狡辩。比如他们不能说,“现在这些是我们的孩子了,这些孩子属于我们所有人。”而乔‧拜登最近就这么说了,他说,“这些不是你们的孩子,这些是我们的孩子。”
乔‧拜登:“什么别人家的孩子,没有这回事。没有别人家孩子这回事。我们国家的孩子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孩子。”
马科维茨:我想即使在像苏联那样的地方,这种思想也会遭到抨击。所以他们不能那样做。他们得这么说:我们在一起,我们会帮助你抚养孩子。这不是要把你们分开,而是要让你们共同成长。
保护孩子免受觉醒意识病毒的侵害
杨杰凯:没有什么一刀切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的感想。比如有些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有难以置信的责任感。与他们建立这种关系几乎是合理的,当然,要有一些界限。但他们已经在拓展自己的界限。还有一些孩子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像零一样,是吧?你需要非常……
马科维茨:是的,你看,我有三个孩子。他们差别太大了。他们看起来简直就像不同的爹妈生的,个个都不一样。他们生来就这样,这是事实。我们帮着他们塑造应对的方式,只要不是个性方面的原因。当然,他们的个性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有韧性的孩子,让他们能够走向世界,而不是让他们感到某种程度的焦虑,从而使他们变得虚弱,或者让他们在大学里对气候变化感到极度担忧,使他们无法过上充实的生活。所以当我们把孩子当作小大人对待时,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麻烦、问题灌输给了他们,这确实会把他们今后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杨杰凯:我认为认可这种意识形态的人会说,大家都在灌输。实际上,卡罗尔,你在向孩子们灌输你的意识形态。我有一个更好的意识形态,我希望把我的意识形态灌输给他们。这就是一个事实,对吧?那么,你没有给你的孩子灌输思想吗?
马科维茨:嗯,我肯定在影响他们。请注意,我很乐意给我的孩子灌输思想。但是如果孩子什么都听家长的,那肯定不合理了。如果社会上每一种力量都把孩子们推向一个方向,那力量是巨大的。但是,你认为你应该能够向我的孩子灌输东西,这种想法也是我憎恶的。不,你不可以这样,你不是他们的指路人。你是他们的老师,你是他们的医生,你不可以把一下想法灌输给他们,然后我在家里却需要把它们消除掉。
不得不说,我的孩子们确实过着他们自己的生活,不管什么原因吧,你可以说由于我的灌输,随你怎么叫吧,总之就是因为我的教育。他们确实过着自己的生活,当有人试图说服他们信什么的时候,他们头脑是清醒的。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放学回家,就会说,今天我在课堂上听到了这个,我需要考虑或担心这个问题吗?我开玩笑地称他们是“觉醒警察”。因为当一个概念强行推给他们时,或者当他们听到某人的观点而不是事实时,他们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这很好,我希望他们头脑清醒。
你知道,我和贝瑟妮,我的合著者,我们走的路大不相同。我有三个孩子,他们都在公立学校上学,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一个现在在私立学校。贝瑟妮有六个孩子,她在家里教他们。她会预先观看他们要看的电影,她预先阅读他们要读的书。这些我都不做。我给了他们一条长长的绳子。我说,我相信你们。我想听听你们在外面学到了什么。但我也在家里提供基础学习内容,我们两家都这么做。但贝瑟妮想说的是,无论她如何保护自己的孩子,她都无法从各个方面保护他们免受觉醒意识病毒的侵害。在儿科医生办公室里,她说,我在家教育他们,我们什么都能做,文化之外的事,但我仍然需要带他们去看医生。如果你的儿科医生被意识形态俘虏了,许多儿科医生已经这样了,你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在觉醒体制下,每个人的思考方式都必须完全相同
杨杰凯:是的,这很有意思。我喜欢你这么讲,你想给他们接种某种程度的觉醒主义,对吗?这样他们就能真正看清楚。你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区分。对于你应该相信什么,有一种整体的看法,对吧?我一直在想,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感知到的共识正在朝着某个方向推进,你被教导说它完全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说,嘿,我要教给你评估那些东西的技能,这听起来就像你在做的事情,区别很大。
马科维茨:很难搞,是的。嗯,我可以肯定,这肯定是目标,就是给他们提供工具来评判他们在外面的世界听到的东西。但我也要说这种新的觉醒主义,与自由主义或老式的左派相反,它走的是一条窄路,你得照他们的话去说,完全照搬,分毫不差。你在描述那些思想时也需要非常地具体,你只能以非常明确的方式来谈论它们。比如,你不能说“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你得说“我反对种族主义”。所以我对我的孩子没那么死板僵硬。我希望他们探索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观念。而这曾经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获取广泛的观点,这样他们就可以选择自己的观点,自我学习。而现在我们还做不到,因为在这种觉醒体制下,每个人的思考方式都必须完全相同。
从纽约搬到佛罗里达州的原因
杨杰凯:请解释一下,你来自哪里,也许还有你父母教给你的一些理念,让你觉得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马科维茨:我出生在苏联,很小就来到了美国,当时我还不到两岁。我在布鲁克林长大,我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纽约,虽然有时短期离开一下。我原本想一辈子都生活在纽约,我们打算在纽约抚养自己的孩子。一年多一点以前,我们决定搬到佛罗里达,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我们刚刚在布鲁克林建造了自己梦想中的家园,我们确实计划在那里度过一生。但是后来我们觉得纽约的现状已经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在疫情之下,而且在围绕疫情的许多问题上也是如此。
不仅仅是因为疫情,但疫情确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我们觉得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正在做一些真正的、理智的正常决策,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所以我们就搬家了。事情闹得还挺大,因为我是《纽约邮报》的一名专栏作家。再说一遍,我是纽约至上主义者。因此,我要离开纽约的想法很轰动,人们都想听听这个故事。所以,真是太棒了,真的很自由,我们一家人真的找到了一种自由的方式。
杨杰凯:你的报导,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从那时开始更多地阅读你的文章,因为我认为你比很多人都要超前一点,非常有见解。但是,我想知道,你的父母告诉过你什么,以致你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因为我想一定有那么一个时刻,你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你周围的人却说,你在说什么呢?
马科维茨:是有过好几个这样的时刻,但我想说的是,像在脸书群组里,我们那个非常开明的社区,对于给最贫穷的成员提供教育突然不再感兴趣了。他们根本不关心纽约市各地贫困社区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事实上,不让贫困社区孩子上学成了他们理念的一部分。同时,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把他们送到私立学校,当时是放开的。显然,公立学校非常危险,但私立学校是允许上的。或者他们给孩子找家庭教师,或者他们搬到自己的度假屋,让孩子上当地的学校。但他们对全城贫困儿童却只字未提。我觉得那一个时刻对我来说非常像苏联,就好像你说的是一套,但你相信的完全是另一套。还有,告发邻居,人们会报警说,这家后院人太多了。他们似乎非常喜欢这样,真的热情高涨。
另外,当有人说“我认为学校应该开放”时,谈话就会中断。我觉得就像,我不明白为什么自由的欧洲开放学校,但这种理念在美国只有唐纳德‧川普(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才认可。他们基本上都会说,“哦,你是右翼分子。”搞不好他们会把他们从俱乐部踢出去。这个人会说,“我一辈子都是自由主义者,你信的一切我都信,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开放学校呢。”那些人就会感到受到了严重的骚扰。有些人因为这些理念被解雇了。那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但随后犯罪率真的开始飙升。
长期以来,纽约一直做得很好,我们都期望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然后,当它没有继续时,就像,他们拒绝接受,他们拒绝承认犯罪率在上升。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帖子,“我就是害怕天黑后自己一个人走路”,或者“我十几岁孩子的手机在当地地铁站被偷”,等等。他们会收到这样的留言,“不,不要相信右翼媒体关于犯罪的言论。”我会说,统计数据就是统计数据。他们会说,但是请注意,在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更高。嗯,是的,但你谈的是纽约市历史上极其糟糕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我们有过二十多年的相对无犯罪的时期,不是没有犯罪,而是纽约市犯罪率较低,你就因为意识形态而忽略这个?你会说这不存在,因为你是站在想假装这些不存在的一方?我真的看到了我一生中都在听说的顺从,你不得不相信,你必须让它表现一下,我在书里谈到了这一点。
我在《被偷走的青春》里讲了很多,表现一下就是为生存下去。极权主义国家之所以蓬勃发展,这是部分原因。比如,当乔治‧弗洛伊德致死案发生时,引发了骚乱,大家纷纷在橱窗上打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标语。我心里就在想,我在书里也这么说,“黑人的命也是命”真的是一个没有争议的理念。当你把这个标志贴在窗户上时,在你那个意识形态相同的社区里,你说话的对象是谁呢?比如,你想用你的标语说服谁呢?当然,他们并不是要说服任何人。他们想要表达的是,咱们是一伙的,我是其中的一员,请不要冲着我来。因为,你看,我的窗户上都贴着这样的标语了。在我看来这“很苏联”。我的曾祖母,抱歉,我祖母的父亲,我曾祖父死于斯大林的古拉格集中营。然而,当斯大林去世时,我祖母和她的妹妹把斯大林光辉的一生做成了一本剪贴簿,因为当重要的是要看表现的时候,你就这么做了。我从很多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它,想不看都不行。
觉醒主义者是非常小的群体,但通过强迫性的服从控制了很多人
杨杰凯:我们继续与卡罗尔‧马科维茨交谈,她是《被偷走的青春》一书的作者之一。你之前提到有些人热衷于对他人进行所谓的告发,或者说告发让那些仿佛着了魔的人威风起来了,他们通常没有多大的权力,但突然间他们可以成为管事的人。而且,在每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里,这些人都是共产党队伍中能往上爬的人。每当我看到那些人兴高采烈地告密的时候,我就想,为了什么呢?值得这么高兴吗?
马科维茨:是的,感觉他们好像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似的,告发自己的邻居,并且……
杨杰凯:这不令人不安吗?
马科维茨:是的,是的。因为我认为在COVID之前,我不会想到在美国社会中我会遇到这种情况。这令人不安。令人不安是因为那么多的人那么快、那么容易地就陷入其中,告发自己邻居,让人们因为意见错误就被解雇,叫停人们的工作,等等。是的,难以置信的是,它发生了,而且正在美国发生,而人们就站在那,支持它。感觉觉醒主义者是人口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但他们却能控制那么多人,他们通过强迫性的服从来实现这一点。
杨杰凯:嗯。你知道,有这么一种观点,自由永远只有一代人的距离。
马科维茨:能来到这里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当然了,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但我觉得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趋势正在美国社会出现。你是对的。这不是我们可以忽视或不去关心的事情。也许明天我们就完蛋了。这已经是世界历史上运行时间最长的民主和自由实验之一,即使它不是最长的。我认为这是最长的,是吧?我认为没有人打败我们。也许它明天就结束了。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杨杰凯:这可能发生在选举中,而且已经发生了,你知道,就在我们周围。我只是……你不能……你看看委内瑞拉,这个真正繁荣的自由社会楞是投票把自己投成了一个独裁政权。
马科维茨:嗯,有一个笑话,你可以把自己投进去,但是你得开枪杀出一条路来。
《被偷走的青春》一书描绘出了觉醒主义的整个画面
杨杰凯:你和贝瑟妮描绘出了觉醒主义的整个画面。这是怎样的一个画面?当然,你提到了各种各样做了出色工作的人。
马科维茨:觉醒主义是左派意识形态与这种强迫性服从的结合体。因此,过去的左派肯定努力推动着他们的计划,而且做得很成功。比如在大学这个层面,新觉醒主义不允许在这种对话中有任何空间,这就像左派不能与左派争论不同的观点。觉醒主义走的是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所以这就像老式的左派,对此我开了个玩笑,你可能会获得女性研究的学位,但新的觉醒主义是你获得了女性研究的学位但你定义不了什么是女性。这很重要。有点像,老式左派们会感到震惊的是,觉醒主义者现在说,他们不能确定到底什么是女性,他们不确定成为一名女性意味着什么,他们无法定义。像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会觉得这很让人震惊。所以对我来说,这就是老式的左派意识形态和新式的觉醒主义之间的区别。
另外,关于平等与公平的讨论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认为老式左派曾经支持“平等”,而“公平”是觉醒主义的流行语。它不讲机会平等,而是讲结果平等。任何曾经在共产主义国家生活过的人都可以告诉你平等的结果是不存在的,它不会发生,这是不可能的。某些人的结果会不同于其他人,就是这样。
杨杰凯:在阅读过程中,我记下了脑海中出现的一些主题。其中一个主题是关于对儿童的荒谬的医疗处方。
马科维茨:是的,我们在医学上对孩子们所做的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男孩。我认为我们对他们治疗过度了,我们正在剥夺男孩们非常自然的行为方式。再说一次,我有一个女孩和两个男孩,他们是不同的,他们是不一样的。我女儿可以坐着看几个小时的书,而我两个儿子,如果逼着他们坐下来看几个小时的书,会毁掉半座房子的。而他们都是同一对父母所生。所以我认为对男孩的过度医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在性别意识形态的辩论中,你也可以看到对孩子用药的情况。比如,对孩子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阻止他们青春期的到来是否妥当,或者激素治疗。这很疯狂,因为直到最近我们才真正开始说这样是不行的。我认为对孩子进行激素治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任何表现为性别焦虑的孩子来说都很普遍。现在这种做法终于受到了挑战,而且挑战得相当好。让我吃惊的是,我们居然让它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欧洲免受了很多觉醒主义的影响
杨杰凯:在欧洲,无论是在性别医学方面,还是在疫情治疗方面,都制定了更多基于科学的政策。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这里并不了解这些。
马科维茨:我们听说了,但我们只是选择了完全无视。对我来说,如果说欧洲在某些方面干得漂亮,这很疯狂,但他们在疫情防治方面的表现比我们好得多。我之前在观察,惊讶地发现,欧洲那么多国家从来没有给孩子戴过口罩。然后当疫苗出现后,他们说,不,孩子们不需要这个。我以前也是这么说的。有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极端的事情。我过去是支持疫苗的,我只是认为孩子们不需要疫苗。如果我不得不再来一次,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支持打疫苗,但当时我就是那样。对我来说很明显,孩子们,他们新冠肺炎结果不佳的风险已经为零了。再降也没法降了,这不像到零之后你可以接着降。
然而欧洲非常快地就想明白了,他们也确实让自己免受了很多觉醒主义的影响。他们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大陆。那里的大多数国家都相当自由,这就是全部了。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没有觉醒主义运动,他们没有陷入狂热之中,而那种意识形态真的很疯狂。而且他们没有遇到与我们同样的问题。他们性别焦虑的人数远低于我们,这恰恰表明那是一种社会传染,不是自然发生的事情。例如,大体上欧洲对变性儿童的接受度很高,但他们的孩子中变性的发生率远远低于我们。
而且说真的,美国的左翼人士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他们曾经什么事情都追随欧洲,而现在却不追随了。但没有人可以提出任何问题。
杨杰凯:而且还出现了一种转变,现在正在加速摆脱这种性别肯定治疗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如果你的想法跳出了常规思维,它就“肯定你,肯定你,肯定你”。
马科维茨:欧洲正在抛弃这种观念,英国肯定正在远离它,因为……
杨杰凯:因为那种做法不起作用,造成了巨大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他们发现了。
马科维茨:是的。这方面带来了巨大的问题,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共产革命中的让家庭分离正在美国上演
杨杰凯:我注意到的第三个主题就是这个普遍的想法,同样,在性别方面,在新冠疫情方面,坦率地说,在其它方面,就是这种认为父母应该被排除在关于孩子的决定之外的想法。实际上这种做法居然是可以的。
马科维茨:是的,这应该让父母们感到害怕。我们以前的理解是,如果有人要求孩子保守秘密,别让他们的父母知道,这个人就是在对孩子们干坏事。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接受的地步了,作父母的不需要知道孩子在学校做什么。如果孩子决定在学校里成为不同性别的人,使用不同的性别代词,打扮成异性,这应促使父母们认识到,这里存在着一个更广泛的问题。让家庭分离是这类革命中发生的事情。如果父母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了,有人要求他们的孩子对他们保守秘密,我认为他们应该自己想像一下,还发生了什么?如果这种事都发生了,还有别的吗?
杨杰凯:这是文化革命吗?让人不敢相信。我们在苏联看到过,我们在共产主义的中国见到过。是的,是年轻人,我不知道我刚才说过没有,是的,红卫兵,毛泽东的红卫兵是青少年,基本上把那些不按规矩来的老一辈人置于死地。
马科维茨:对,一场文化革命正在我们这里发生。我认为与那些革命非常相似。而唯一真正的区别是,我们知道它正在这里发生,我们意识到了这种现象。因此,阻止它应该比其它地方更容易。我们在书中找出了这些历史的相似之处,因为我认为它们很有启发性。他们正试图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实现他们的愿景。如果我们放任他们,一旦他们成功,我们就无法阻止了。这就是说,现在就必须阻止这种现象。当你看到它在我们社会的不同方面发生的时候,应该尽快制止,而且人们不能掉以轻心。
我在写这本书之前,我觉得我不会认同一场文化革命正在发生,但现在我看得很清楚了。我看到它已经无所不在了,这不是阴谋论,而是正在发生。
还有一件事,我们谈到比如左派利用儿童成为他们的积极分子。我们收到了大量的留言或邮件等等,说这太荒谬了。把正在发生的事情想像成阴谋论,这是很荒谬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最近出版了一本书说,“是的,我们应该让孩子们成为积极分子。”千真万确,这就是他们的目标。这就好比,是一个阴谋论,还是一位左派高层领导刚刚承认了这一点?你不可能事事都得到承认,所以你必须得想清楚。你知道,父母们必须自己把这件事想个明明白白,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
杨杰凯:好的,卡罗尔‧马科维茨,很高兴你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马科维茨:谢谢,杨,非常感谢。谢谢。
杨杰凯: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对卡罗尔‧马科维茨的采访。我是主持人杨杰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