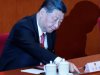我在加州大学开课,有不少学生是中国大陆来的。上个学期我教过一门“中国文明史”,一百五十个学生注册,几乎一半是中国同学。有的念得很认真,考得也很高,但相当一部分是不太认真的,似乎是想“混”一个容易的学分(“我是中国人,何必上课去听美国人对‘中国文明’的印象?”)。考试的时候,我发现这批学生特别善于互相帮忙,用手机或平板电脑把答案传来送去,甚至集中在讲堂的一个角落里一块儿研究小考的正确答案应该怎么写。
不问对错,只问得失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正确答案”的态度。他们衡量一句话的价值,用的好像不是一个真与假的标准(“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也不是一个道德标准(“我应不应该写下这句话?”)。用的标准是“这么写是否对我有利?”似乎认为把小考分数弄得更高是“聪明”的行为,上大学的目标是学会用聪明的方法。
作弊不是中国大陆学生特有的问题。哪儿来的学生里都会出现这个现象。但中国大陆学生还是有特殊性。要是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来的学生,很少看到那种“作弊作得成功就是本事”的态度。港台同学要是作弊,更会觉得是难为情的事情。
因此我们可以问: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不要轻易地责备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而且他们成长的语言环境早在他们出生前已经设定好了。
回头看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任何社会有“官话”与“日常话”的区别,但中国共产党在50年代推广的政治语言是个极端的例子。当时,不管你恨不恨地主,你得学会在斗争会上大喊“打倒地主XXX!”。万一喊错了,大会把批评的矛头转向你自己,你不但得承认错误,还得“感谢党对我的教育”。这是你的“表现”。日子久了,怎么对付官方语言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技能,或说是一种语言游戏。衡量一句话的价值的标准变成:下棋下得对不对?语言处理得聪不聪明?“真”与“假”不是标准了。到了60年代的下一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恶化了语言的堕落。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观把尊敬长辈和认真读书放在首位:孝顺父母,听从老师。但毛对年轻红卫兵说“造反有理”,鼓励他们批评父母(“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侮辱老师,甚至打死老师,这样就摧毁中国社会的最深最基本的价值观。到了文革,不只是“真”得让步给“实用”;连“道德”也得让步。“利”压倒了“义”。不问是非,不问对错,只问得失。
出了门效忠政权,关了门骂习近平
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理想稍微能够恢复一点,但在六四屠杀和邓小平南巡以后,公共价值观只剩下了赚钱和民族主义这两条。“义”还是输给“利”。宗教(佛教,基督教,法轮功等)的再兴起说明中国老百姓还继续向往人本的价值观,但这些信仰都处于官方价值之外,甚至是官方打压的对象。
到现在,官方的语言还摆设在社会的表面上,不管多么虚假,老百姓只好配合它,必要的时候在“语言游戏”里下一招棋。不少人注意到了当代中国“精神分裂”的现象。关了门骂习近平,出了门效忠政权。对西方呢,骂它是霸权主义,想压制中国的,同时盼能有绿卡。
前几天在中国的微信上有人发了这么一条短信: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在加沙地区旅游或是务工碰到了危险,在暂时无法联系到咱们国家的大使馆时,你会选择向以色列政府求助还是向哈马斯求助?你的选择代表了你最真实的立场。”
马上有网民回答:“很大一部分中国人会向以色列当局求助,但永远站在哈马斯一边。”更有人补充说:“就像很大部分中国人会送子女去美国留学,但永远站在俄罗斯一边。”
这不是简单的“自我审查”问题。这种矛盾心理的两头都是真实的。但我们也可以问哪方面的认同是更深的?我有个很出色的中国朋友(不便透露姓名)说她的同胞考虑自己的得失是“无条件”(unconditional)的,效忠政权的价值观是“有条件”(conditional)的信仰。换句话说,哪天官方的价值观与个人的“得失”利益没有关系的时候,价值观就垮了。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话说到点子上了。
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吧。要是习近平明天出来,站在中南海门前宣布(他绝不会这么做,这只是“思想实验”而已):“我决定下台,而且从现在起,我们要设立民主制度,有普选,宪法,人权,等等”会有多少老百姓上街抗议,说:“不行,不行!你们共产党多少年干得这么漂亮!你习大大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那么宝贵!不能下台!不行!”?
要是站出来这么说的人不多,那我们就得面临一个事实:中国人效忠中共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母爱是无条件的,但“爱党”有条件。条件一走,爱会继续吗?
习近平知道老百姓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吗?肯定知道。要不然为什么那么怕事?那么偏执狂?那么愿意花大笔钱在“维稳”工作上?
我的意思不是说政权脆弱。所有的媒体,警察,军队,大钱都控制在中共的手里,不能说它脆弱,而是一种坚硬的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