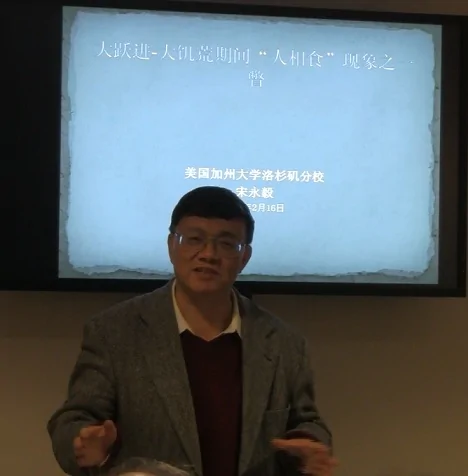
宋永毅先生在研讨会上做主题演讲
关于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期间(1958-1961年)出现的“人相食”的悲惨现象,目下噎有不少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亲历者开始一一揭示历史真相。 但是,对这一惨绝人寰的民族灾难的严重性的认识和研究,却还大都停留在控诉和谴责的层面。在不少著述中,作者都引用了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初夏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毛泽东说的话:“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1 其实,刘少奇的话从另一面提醒了我们应当做进一步的逻辑推断:如果“人相食”现象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只是一些个案,刘少奇是否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中南海向毛谏言。以刘少奇饱读史书的学识和他直接负责宣传部门(以掩盖历史真相为主要职责)的中共第二号人物的高位,如果他不认识到那个年代的“人相食”的现象噎严重到了在历史上无法掩盖的程度,又怎么可能向毛说出这样的直接得罪他的话来?更发人深思的是:即便是刘少奇在五十年前就坦陈的“要上书的”“人相食”现象,至今还在官方的正史中被掩盖和年轻人的记忆中被忘却,这是否又在今天凸现出了这一研究的急迫性呢?
一、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人相食” 现象波及各地的普遍性
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记载中,因饥荒而造成“人相食”现象并不少见。纵览二十四史,大约最早记载这一现象的是《汉书》和《隋书》。据班固撰《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2 在魏征主编的《隋书》的“五代灾变应” 中也有如下记载:“九江大饥,人相食十四五。”3 以后自唐到清的千余年的正式史书记载,中国和饥荒有关的的“人相食”的惨剧大约有数十起之多。
《隋书》是唐初所修五代史中较好的一部。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在《隋书》的“志第十五”中,对“人相食”现象的出现,还有过除了天灾以外的原因总结:“狼一星,在东井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变动也。角而变色动摇,盗贼萌,胡兵起,人相食。”4 自然,古人把出现“人相食”的灾难的根本动因归结为星象的异动并不可取,但它毕竟还揭示了大规模天灾和个别食人魔以外的另一现实原因:“盗贼萌,胡兵起”、即两种战乱的发生:1)暴民起事,2)政权更迭的内战或异族入侵。
确实,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中有着大量“人相食”的案例。例如,唐末的黄巢起义就创造过一份大概可称为世界之最的食人纪录。据《旧唐书》记载:在黄巢攻入长安当了大齐王朝的新科皇帝后,曾“围陈郡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5 换句话说,黄巢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一百天的时间里,采用过的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粉碎,以人肉作军粮,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一天杀食一千人计,也至少吃了十万人! 这位农民革命领袖大规模吃人不吐骨头的行径,其野蛮,残酷,恐怖,实在是骇人听闻。
黄巢的人性沦丧和他的自身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是文人当中痞子型(农村流氓无产者)的知识分子:由一个不及第的秀才成了一个残忍狠毒的私盐贩子。黄巢这样的流氓无产者式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性,野蛮性,破坏意识,盲动力量,亡命的痞子精神,则很容易在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农民革命的领袖。
在中国被蒙古军入侵后的元朝,也是一个有大规模“人相食”现象的朝代。蒙古军本身就有食人传统,以后的历代元朝统治者又根本不把百姓当人,大规模破坏生产力。造成饥荒遍地,“人相食”连续发生。其后的以刘福通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红巾军”,又开创了自黄巢以降的新的大规模吃人当美味的人性灭绝的屠杀……6 但是纵观这些“人相食”的现象,毕竟一是和战乱(不管是农民起义、内战或异族入侵)有关,二是在饥荒中发生都是局部性、地区性的现象。
然而,发生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人相食”却不是处于任何战乱之中。那时的中国既没有内战又没有异族入侵。作这一如是观,对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人相食”的造成,当时的执政者就要负更大的责任。如果说中共政权和历史上的“盗贼萌”有一定的关联,那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政权,其领袖毛泽东也是一个黄巢式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虽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毛没有过黄巢、刘福通式的“食人”疯狂,但是他也是从来不把百姓的性命当一回事的。1959年3月25日,大饥荒初露端倪之际,毛却在上海会议的插话中指出:“粮食收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7
另外,我们更不应当漠视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人相食”现象其实和天灾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如同中共当局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大饥荒的造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实至少是“九分人祸”)。但是它却具有蔓延全国的普遍性。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先生在“安徽特殊事件的原始记录”一文中指出: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 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汤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 8个县共发生 10起。8
他还进一步见证说:
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煌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9
在读了尹曙生文章后,一位1942年参加抗日,1990年离休。但任检察员38年的萧磊先生也在《炎黄春秋》上撰文作证指出:
1960年冬,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受 到批判。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到山东主持处理。……批判省委负责人会议的最后阶段,曾希圣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破坏耕作制度”、“大刮五风”、“大批饿死人”等严重错误,还特 别提到:“据初步发现,全省人吃人事件七十余起。”曾的《总结报告》书面材料发至全省各县委及省委派出的工作组。省委驻金乡县工作组长刘若克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读了曾的《总结报告》。报告中提到人吃人的问题时,引起了他对金乡县是否发生过人吃人事件的注意,为此派工作组员肖锡宜到金乡县胡集公社胡集大队调查摸底。胡集大队十五个生产队,有两千多人。经座谈会调查与个别访问,1959年冬到1960年冬,全大队发生人吃人事件九起,支部书记四岁男孩饿死煮熟后,全家吃了一天。这九起人吃人事件,直至曾希圣总结报告时未能发现。
三年严重灾害期间,山东各地都曾发生人吃人的事件,虽然缺少全省的统计,但远不是曾希圣报告中所提到的七十余起。1961年 春,笔者参与省政法工作组检查莱阳县检察院批捕、起诉质量时,阅卷中,发现二起卖人肉案件。二起作案人均是复员军人。……
据莱阳县检察院介绍:1959、1960这两年,全县盗挖尸体案件时有发生。已破获七、八起,还有五、六起未破。有的盗尸体吃了自己死亡了,还有的死亡在盗尸现场。…… 10
为此,萧磊先生的结论是:“史料记载,各朝各代都有过灾荒,有过饿死人,也有人相食。但如三年灾害期间饿死人之多,其规模波及全国,人相食事件之惊人,都是绝无仅有的。” 11 最近,另一位亲历者、原国家统计局干部杨德春的文章“太和县饥荒报告的产生 ”又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波及”性。该文披露“安徽省太和县宫集区赵寺大队29个自然村中,有26个(约占89.6%)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如涧南生产队,7个生产组,组组都有;该队144户,604人,吃过人肉的有37户,144人。严重的韩小寨全村18户,85人,吃过人肉的有13户,55人,占全村人口的65%。又如谢寨生产队,吃过人肉的约占40%。”12
四川、江苏等地都是鱼米之乡,在1958-1961年间也根本没有天灾。但是也都发生了规模甚大的“人相食”的惨剧。原中共四川省瀘州地委第一書記鄧自力1959年反右傾時被撤職。他是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堂弟,1962年得以復出任宜賓地委副書記。他回忆大饥荒时当地的“人相食”现象說:“……饑荒越來越嚴重,後來,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謠傳吃人肉能治腫病,於是有腫病的人就從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13
宜兴是江苏最富饶的地区,谁也不会想到这里不仅饿死了人,还有人吃人的记录。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1960年12月27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和刘耀华同志到和桥公社,听到有些社员谈去冬今春饿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这个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为死人太多,人死后连稻草也不包。高楼大队有一户人家一天死了两个人,就用一副担子把两个死人挑出去了事。个别公社甚到发生过把丈夫、儿子害死后吃人肉解饥的事。14
在一个没有大规模天灾和任何战乱的和平年代,全国各地的许多地方却都同时发生相当规模的“人相食”的现象。这噎无法用外部的灾难来解释它的成因。这又使人们对“人相食”惨剧的理解,由个别现象发生了质的飞跃到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对那一时期“人祸”的鞑伐,也有了新的升级。换言之,只有一种解释才是合理的。那就是:这是一种全国性的内政所导致的人为饥荒,又是各级领导层的“人祸”所直接逼迫激化出来的人道大灾难。
二、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人相食” 现象的几种主要形态
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的生存竞争的漫长历史中,异类和同类之间的残杀吞噬并不令人奇怪。但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仍然出现“人相食”的现象,这说明人类的人性向兽性的沦丧倒退。由于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社会意识,所以“人相食”就比动物相食更显得野蛮和残酷。
中国历史上的“人相食”可大致分为两类情况: 一是由于天灾或战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饥荒,人们为了生存而被迫以同类为食。这种现象当然是违背人性的,但在那种每个人都面临著饿死威胁的情况下, 靠吃人肉来活命还能够使后人理解。 二是不是由于生存的挣扎,而是出于某种主观目的的残忍的暴力行为:或是以食人炫示“革命”暴力;或是听信左道邪术以食人来养生;或是以人肉为“美味”,等等。这些同饥荒时期被迫食人相比,都更带有食人魔偏嗜的野蛮性和残酷性。
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其动机都比较单纯。大都是中国农民在树皮草根全部啃完的极端绝望的生死线上做出的一种被迫的人性向兽性的沉沦。 如果我们把它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中国农村的“人相食”的现象做一对比,便不难发现它们有很大不同。 文革中广西在1968年出现过相当规模的吃人狂潮,这一人道灾难有如下几个特点:1)明显的派性和阶级性--吃人者大都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韦国清和广西军区支持的“联指派”(保守派)和党团员积极分子,被吃者则是反对派“四二二”(造反派)或所谓的“黑五类”及其子女,即“阶级敌人”;2)吃人事件一般发生在各级中共领导和军队掀起的大规模“镇压阶级敌人”(实质是乱打乱杀)的浪潮后,受到当局的唆使、纵容和默许;3)吃的主要是受害人的心肝,因为据说这可以“壮胆壮身”。第一位揭露这一“万人吃人运动”的作家郑义和当年组织吃人者的凶手谢锦文有过一段如下的访谈,很能说明两者的区别:
他是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后又任大队支书。……见我只问吃人细节,顿时轻松起来,主动谈起他光荣的吃人历史。谢参加过中共游击队。一九四八年,一奸细带国民党警察来抓人,他们杀了奸细,剖腹取肝分而食之。(有史料记载:井冈山红军亦杀人吃心,尤其是新战士。原由与谢锦文一般:壮胆壮身)……我突发异想,问道:“过去用瓦片烤的肝好吃还是这次煮的好吃?”答:“好事烤得好吃,香,这次是腥的。”除了心理生理的极端厌恶之外,对这位食人者我还有几分谢意。感谢他点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吃人是历史的继续。可以吃奸细的的肝自然可吃“二十三种人”的肝,可以吃国民党的肝自然也可以吃对立派和“走资派”的肝。红军、游击队可以吃人肝,“革委会”、“贫下中农”、“革命群众”自然同样可以吃人肝。只要是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便可!15
很明显,这种吃人绝非饥荒所迫。至于说到以吃人的心肝来“壮胆壮身”,除了表现了人性中遗留的兽性的凶残,更表现出动物式的愚昧。因为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人肉或人的某些器官同其他动物相比,其组织成分没有根本的区别。而且,不少动物及一些虫类身体内所含的微生素、微量元素或可作药用的有机物质都优于人体。
应当承认: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人相食”现象中,也有一些吃人心肝的案例。贵州省赤水县是“人祸”的重灾区,饿死了超过10%的人口。1961年5月11日也有过一起案例:“隆兴公社马临管理区新华大队第三生产队于5月11日贫农妇女王志珍将自己六岁女儿罗三女死后,用刀解剖尸体,取出心肝煎吃,[并]企图将肉体全部吃掉的问题。”很可能,作案者王志珍也受了吃人的心肝可以“壮胆壮身”的异端邪说的影响。但是根据当时中共赤水县监察委员会的调查,至少和广西中共干部谢锦文的吃人有三点不同:1)她吃的是噎死了的女儿,谢剖腹取肝的是活人;2)赤水县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指出:“住队干部工作不深入,对群众生活抱着不关心的态度,王志珍在小孩未死之前,曾向住队干部罗永联同志说过因口粮被偷一筒半而没有粮食,但一直未进行了解,致使小孩因断粮引起病亡,罗三女之死,住队干部也有一定责任。”16 换句话说,王和她的女儿噎到了饥饿致死的生存边缘,而谢完全没有饥饿致死的危险,只是觉得人的心肝是一种可食的“美味”。3)王是被权力机构的断粮的逼迫、为了生存而偷偷吃人,而谢本人就是权力结构的代表。是一种以“革命”名义的堂而皇之的食人。
在看了数百份绝密档案、个人回忆、县志记载的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人相食”现象后,我们可以大概地总结一些当年“人相食”的特点:
第一, 大都是食死者:即并不具有暴力杀人而食的恶性倾向。从中也可看出中国农民的饥不择食的被迫和人性沦落前的最后一丝未泯的善良。
第二, 大都是“食子”:这噎从不具有恶性倾向的“人相食”到具有暴力杀人而食的恶性转换,但大都还是在家庭的范围内。
第三, 不少转化为“易子而食”。 也有暴力杀人而食。
在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发生在四川省石柱县桥头区十七起“人相食”的个案中,很能说明以上的第一种形态,因为基本上都是因饥馑而被迫吃死者的尸体。值得注意的的是:出现食死者的前提往往是大面积地饿死人。例如,在1961年的秘密档案中,四川省委整风整社工作团涪陵分团,涪陵、石柱、西阳县工作组在向省委书记廖志高报告石柱县桥头区的“人口死亡问题”如下:
桥头区在59年公社化后共有人口28,352人,现在经查对实有人口21,018人,其中男的 9,425人,女的11,593人。这里在59年至60年冬遭受旱灾,又加上人祸因而死亡人口竟达7,334人,占原有人口数25.86%。全区有桥头、三永、三益等六个公社,44个管区,集中人口死亡最多的是桥头公社,社内仅兰木管区原有人口855人,现有404人,死亡451人,死亡率达 52.74%。其中死亡绝户的51户。由于兰木管区人口死亡太多公社将桥头街上附近农民迁移48户167人在管区内,但也遭到严重的死亡,现有的仅8户 16人,死亡率占95.8%。还有洞塘管区第一队原有61户244人,现有41户90人,死亡154人,死亡率63.1%,其中死绝户的20户78人。第二队原有32户153人,现有26户76人,死亡77人,死亡率50%,其中死绝户的5户30人。这批人口中死亡的大多数是男劳动力,其次是儿童,如兰木管区原有孩子82人,现剩公社托儿所20人,家中3人,死亡率竟达73.7%。17
看了以上这些触目惊心非正常死亡的比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人相食”的惨剧了:大规模的饥馑,是“人相食”的物理主因。无独有偶,在大跃进-大饥荒年代担任了安徽亳县县委农村生产福利科科长和县人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梁志远先生,曾经写过一份《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的内部报告。见证了当时大规模的食死者的现象:
在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这个严重问题是由少到多,到1960年4月达到顶峰。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 18
梁的报告还透露,因为上述食死者的现象纯出于极端饥饿的生理原因,连公安机关 都无法处理:
1959年春,城关公社涡北派出所抓获了一起正在煮死小孩肉的盲流农民,遂将“犯人”和小孩肉送到县公安局。公安局当时不知如何处理。一位副局长向县委第一书记赵建华作了汇报(当时梁志远在场听了汇报),当即定为“破尸案”,并决定逮捕“犯人”。县委政法书记李庭芳亲自审讯后认为,“犯人”身体瘦弱,无政治目的。于是未经请示县委,发了两个馍,将“犯人”教育释放。县委知道后,李庭芳受到严厉批评。李又让公安局将“犯人”抓回,重新入狱。经过半个月的审讯,确定“犯人”没有政治目的,县委批准将其释放。19
因为“人祸”愈演愈烈,饥荒自然就无法停止。死者的尸体又数量有限,农村中的“人相食”现象便出现了第二种形态: “食子”。这噎从不具有恶性倾向的“人相食”到具有暴力杀人而食的恶性转换,但大都还是在家庭的范围内。因为农村中男尊女卑的旧风俗的影响,一般年幼的女孩子便成为家庭成员中的最常见的受害人。因为自己的孩子下不了手,又出现了“易子而食”或暴力杀人的第三种恶性形态。当时四川省崇慶縣農村工作組副組長鄭大軍就记载和见证了当年发生在東陽公社五大隊第一生産隊的“人相食”形态的恶性转换:
1959年底,公共食堂無糧下鍋,經常「變相斷炊」。所謂「變相斷炊」,即灶房只供應白開水,而把強制節餘的社員口糧供黨員幹部們夜半三更時享用。因為「群衆垮了幹部不能垮,否則就失去革命的主心骨。」幹部們半夜需外出巡邏,以確保家家房頂不冒烟,户户屋裏不見火。
一天下半夜,全家八口人已餓死了兩口的貧農莫二娃半夜殺了自己的親生么女、三歲的樹才妹。烹煮時屋頂飄煙,被巡邏的生産隊會計王解放和出納、保管見到。將其一家老幼五口綁成一串,押到大隊。
莫二娃叫冤説:樹才妹生下來就缺奶,連米湯都没喝飽,好不易熬到三歲,連路都走不穩,命裏只該活這麽大。
支書:曉不曉得隨便殺人,國法難容?
莫二娃:與其餓死,不如讓她提前咽氣救全家。
二娃婆娘磕頭哭訴:我們全家都吞了觀音土,没油葷過不去嘛,媽心疼的樹才妹喲,下輩子投胎莫變人了。
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釋放了,大隊幹部們再三研究和權衡,决定為了官帽而壓下這起吃人案。
莫二娃一放,大夥私底下奔走相告,以為政府默許這様做。由于重男輕女的傳統,非勞動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操傢伙在自己家裏下手;不忍心的,就抹把淚與鄰居约定交换着下手。
全隊共82户491口,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間,就虐殺并吃掉七歲以下的女童48名,佔全隊同一年齡綫出生女童人數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20
“人相食”当然是一种人性向兽性的倒退和耻辱。但是,它直接发端于人为制造的极端的饥饿,更是人类的双重耻辱。一方面,无论是出于他们的奴性软弱还是最后一丝未泯的人性,参与了“食人”的中国农民毕竟大多数没有制造恶性的杀人而食案件。在他们杀了并吃了自己的亲人后是无穷无尽的悔恨。例如,湖南澧县如东公社有一个很有名刘家远杀子而食的恶性案件。刘在一天夜里杀了自己“躺在铺上的、饿得就快要断气”的儿子,煮了吃了。
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21
另一方面,处理这些事件的中共干部有时也表现出一种最低限度的人性的理解。例如,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22
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人相食”惨剧中,当然也有一部分暴力杀人,贩卖人肉的恶性案例。但是从比例上来讲这毕竟还是少数。我们今天固然可以指责那些食人的中国农民的沉沦、耻辱和奴弱(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了他们的老实、善良和他们在绝望的沉沦过程中的最后一点未泯的人性。
注释:
1、王光美、刘源等著《历史应有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2、240页。
2、《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一册》,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第489页。
3、《二十四史全译?隋书第一册》,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3年,第522页。
4、同上,第485页。
5、《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六册》,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3年,第4644页。
6、有关刘福通的“红巾军”的食人兽行,史书里有大量的记载。例如,《明史卷122:韩林儿传》记载:“是时承平久,州郡皆无守备,长吏闻贼来,辄棄城遁,以故所至无不摧破。然林儿本起盗贼,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诸将在外者率不遵约束,所过焚劫,至啖老弱为粮。” 元末黄巖陶宗仪与刘福通是同时代人,他在《南邨辍耕录卷9》云: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即淮北)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 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灌,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制作事件(鸟兽之内脏叫事件)而腌之;或男子则只断其双腿,妇女则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换句话说:红巾军食人是偏嗜,认为人肉是种美食,越食越想食,成为恶性循环。这些所谓的“义军”其实与禽兽无异。在网络文章“食人族祈祷丰收食人 :盘点中国历代食人族”(http://www.wmxa.cn/a/201110/9365.html)有较为详细的考证。
7、《主席在上海会议讲话记录整理》(三月二十五日)[绝密:只发到会同志,会后务必交回],中央文件原件。
8、尹曙生:“安徽特殊事件的原始记录”;北京:《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8、同上。
10、萧磊:“我所知道的‘特殊案件’”;北京:《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
11、同上。
12、杨德春:“太和县饥荒报告的产生 ”;北京:《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
13、鄧自力:《坎坷人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0頁。
14、孙海光:《给辛、孙部长并报省委》,1960年12月27日,江苏省档案馆档案。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上篇),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353-354页。
15、郑义:《红色纪念碑》, 台北:华视文化公司,1993年,第26-27页。
16、《中共赤水县监察委员会关于新华队发生吃小孩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年5月31日)》,贵州省档案馆文件。
17、《四川省委整风整社工作团涪陵分团,涪陵、石柱、西阳县工作组关于整风、整社、生产、生活安排及分配等问题的情况报告(1961.1.21-5.9)》和《四川省委检查团石柱工作组关于人吃人的调查报告》,四川省档案馆文件。
18、该报告因为内容过于敏感,被《炎黄春秋》编辑部在2006年发表于他们内部版的《春秋文存》中。见杨继绳《墓碑》(上篇),第266页。
19、同上,第275页。
20、成都崇州市離休幹部鄭大軍口述:“幾椿人吃人的案例”, 载电子刊物《往事微痕》第13期,2008年12月25日。
21、余习广:“吃人饿鬼: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见 “余习广博客”http://yuxiguang.blogchina.com/496438.html)
22、杨继绳:《墓碑》(上篇),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