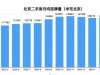北京老百姓有一个共识:这些衣着简朴、稚气未脱、才华出众的学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用绝食这样损害自己的方式来表明自己要求政治对话和政治民主的诚意。所以绝食期间数不清的市民日夜到广场送水、送衣、送钱。游行的市民打出“小弟挨饿,大哥心疼”这样的横幅,朴素而真挚。有一家北京人在学生游行的时候在西单附近设立水站,供路过学生饮水,水桶边有一对联:“愧无美酒酬壮士,凉水热心慰亲人。”至今想来,此景此情,令人对北京市民的同情心和民主意识感佩有加。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我不知道当年国共交战的时候解放军是否真的赢得过人民真心诚意的支持,但六四期间学生从北京老百姓那里得到慷慨的支持,却是我亲眼目睹,没齿难忘。这是人民的城市,这个城市不属于邓小平、李鹏。本文摘自纵览中国网站,作者张守东,原题为《黑暗抹不去的记忆——一个六四青年的回忆》。

1989年4月22日,邓小平(前排中)、赵紫阳、李鹏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会
黑暗可以模糊人们的视线,淡化人们的良心,
但不能抹去人们心中的记忆。
谨以此文纪念赵紫阳先生,他宁肯放弃手中大权,也不愿听任向和平请愿者开枪。他让我对良知有信心。
谨以此文献给为中国的政治民主而英勇牺牲的北京师生与市民,他们的鲜血淹没了我的乌托邦家园,促使我另谋出路。
——题记
1989年6月4日凌晨,当我和大约5,000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沿着长安街走到复兴门,我回首东望,太阳从晨曦中升起,天边一片血红,衬托着长安街上还在燃烧的公交汽车和坦克冒出的黑烟,为我的记忆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红色与黑色,也使那个早晨格外悲壮。那时我在这格外醒目的红色与黑色共同的映衬下告别了那个曾经象征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广场,从此,广场对我不再是民主的摇篮,而是一党专制的象征。那曾经象征共产党革命的红色,也随着这个早晨的到来,变成了红色恐怖的颜色;那黑色,则仿佛我当时的心情和对于未来的感受:被邓小平和李鹏逐出那个曾经带给我民主向往的天安门广场,一时不知何去何从。
六四那天早晨还有辉煌的日出,下午却下起小雨。又为那个悲痛的日子平添了哀伤。意味深长的是,这次天安门民主运动开始的日子,也就是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的日子,北京也下了小雨。是小雨为胡耀邦送行,也是小雨为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画上了句号。
20年过去了,再回到那个小雨迷蒙的初春之日,一切还是那么熟悉,又是如此陌生。熟悉是因为自己曾经自始至终参与;陌生则是因为每一次反省似乎都有不同的心得。以下是我对自己经历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简短回忆。这个回忆完全是我个人经历的版本,并不试图全面回忆那个运动。我不是在写六四史。
一、悼念
1989年4月15日。只记得那一天下了小雨。傍晚的时候听到了胡耀邦去世的消息。觉得太突然。因为胡耀邦也就七十来岁。不久从中国人民大学传出“不该死的死了”这个说法,一下子把大家对胡耀邦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我们当时的校园中人来说,胡耀邦是因为在1986年的学潮中支持学生而被李先念、薄一波这样的毛泽东式政治老人赶下台的。而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学生和知识分子无能为力。大家总觉得亏欠胡耀邦。如今胡耀邦却在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的时候撒手人寰,加上当时有关于胡耀邦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被政治立场僵化的强人气死的,更让大家悲痛莫名。
所以,在胡耀邦去死最初的两三天里,校园里贴告示的地方,比如学校的食堂,有很多悼念胡耀邦的挽联和大字报,表示对胡耀邦的人格与政治功绩的缅怀。当时大家还有一个隐忧,害怕被中共强硬分子赶下台的前任总书记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于是大家特别关心官方怎样写胡耀邦的悼词,也非常关心胡耀邦的追悼会何时召开。当时大家心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官方给胡耀邦一个客观、正面的评价。
就我自己而言,我当时还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虽然我已不再想加入中共。胡耀邦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为了民主和正义敢于牺牲个人政治权力的好人,他也是我仍然对中共有信心的因素之一。我在那时写的挽联中特别提到他从一个革命的红小鬼成长为中共头号人物的传奇历史,贴在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食堂门口。但我没有想到悼念胡耀邦只是一个开始,更没想到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纪念也没有为八九年的学生民主运动画上句号,虽然大家在1988年就已经知道,为了纪念五四,1989年必有学生民主运动。
在焦急的等待中,胡耀邦追悼会的消息终于传来:4月22日。由于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是最接近官方追悼会的地方,所以大家决定去广场追悼胡耀邦。21日傍晚,各学校就开始出发了。提前去,是因为大家估计22日当天广场一定会封锁。政法大学游行的策划者是当时宪法教研室的青年教师陈小平。因了他,法大那天的游行得到了精心的布置:从蓟门桥的老校出发,游行队伍前方由四个学生抬着胡耀邦画像,出自一位女教师的手笔,胡耀邦的嘴角画得恰到好处:有一点冤意。接着是四个学生抬着宪法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游行的权利。
在新街口,在西四,沿途都有旁观市民赞赏说“毕竟是学法的”。这种依法游行的方式,为北京市民留下了好印象。由于学生队伍两边都有学生以纵队的形式手挽手组成纠察队,没有本校学生证不得进入,就使官方没有理由说学生队伍里混有“社会闲杂人员”。所以,法大学生的游行使得法大这个原本在北京这样名校云集之处很不起眼的学校,从此变得引人注目,后来每次学生游行到广场的时候,都有市民爬到树上观察,或者打听,看法大的来了没有。
在宪法牌子之后,是用整齐的白布写的黑色大字:“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让我们再送耀邦一程”。这些横幅突出了学生这次游行到广场的目的,而且写的情深意切,非常感人。所以,当时戈扬老前辈主编的《新观察》杂志关于悼念胡耀邦的报道,就引用了法大学生的横幅。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游行。86年冬天学运期间,北师大的学生曾经跑到法大动员我们参加,我没有为之所动。那时我对中共还很迷信,相信党和政府做的都是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有人游行。游行在我心目中跟犯上作乱差不多。那时我在上研究生,非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我几乎不读。因为既然马列主义是唯一的科学,我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读不科学的理论?我们宿舍其他四位同学都不信马列,我们晚上经常辩论,只有我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我很孤独,但很倔强。也为马列主义正在失去影响力而难过。
数万师生在21号晚上寒冷的天安门广场守了整整一夜。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广场上满眼都是各校红色的校旗和悼念胡耀邦白色的横幅。这是我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过夜,为了守候一个政治清明的早晨。但是我错了。
当胡耀邦追悼会开始的时候,大家齐唱国歌,然后全场一片肃静。虽然一夜未曾合眼,但广场上的师生还是那么专注,生怕对胡耀邦丝毫的不敬。追悼会结束的时候,大家还在等候,12时45分,有学生代表试图把请愿书交给李鹏,甚至下跪,但一直无人理睬。到下午一点半,学生代表见请愿无果,即返回学生队伍。这时,大家听说邓小平等人已经从地下通道离开了大会堂。于是现场群情激愤。学生愤怒了。
就我当时在场的感受而言,追悼会之后,只要邓小平等人出来见一下学生,跟大家表示政治体制改革仍会继续下去,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肯定,那么追悼会之后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然而,邓小平等人竟然拒绝见学生一面,跪求的结果竟然是这些领导人从地下通道扬长而去,这让学生产生前所未有的屈辱感,他们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爱国民主热情竟然得不到起码的承认,这不由得让大家感到无助,甚至绝望,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心忡忡。我相信,这种无助感和屈辱感,是胡耀邦追悼会之后紧接着出现的民主诉求最直接的诱因。
邓小平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青年学生的请求还需要他这样主宰一个国家政局的大人物认真对待。他错了。
学生期待的民主对话落空了。他们的请愿无人理睬。于是,经过一夜无眠,经过追悼会的悲痛,经过被这个国家的“公仆”的拒绝,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有所行动。大家喊着“通电全国,一致罢课”的口号开始回各自校园的徒步旅行。
当晚,我到北师大去,那里的学生已经敲锣打鼓,在教师宿舍区宣传“老师罢教,学生罢课”。校园民主宣传正式开始。悼念胡耀邦已经告一段落。正如法大一个85级学生在大字报中所写:“对一个伟人(胡耀邦)最好的悼念,就是继承他未竟的事业。”胡耀邦曾经热诚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4月22日以后,北京校园的唯一话题。这与其说是胡耀邦推动的,还不如说是邓小平。他和他的政权对待学生的那种傲慢的态度,把爱国心切而又感到报国无门的学生朝政治行动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就我个人而言,也正是邓小平在1987年初坚决要开除敢于为民请命的刘宾雁等人的党籍,使我开始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我彻底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是在我从1989年6月4日早晨被荷枪实弹的军人赶出天安门广场——那也是邓小平的举措。
二、“对话”
四月下旬的那些天里,我每天都在北大、清华、人大、师大、政法看大字报。那是我从1988年秋天开始任教以来实际任课的第一个学期,上了没几次课,学运就开始了。人大学生写的大字报最好,北师大写的诗最好,法大的游行每次都有最精彩的设计。四二七游行,法大学生的游行队伍再一次引人注目。这次游行,为的是抗议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这篇社论把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对学生来说,这个定性无异于把白说成黑。本来学生只是在校园议论民主,这次他们发现必须搞一次全体大游行,再次走上街头为自己鸣冤叫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四二六社论,就不会有四二七游行。
1989年4月26日傍晚,法大学生在蓟门桥校区教学楼北侧誓师。鲜红的校旗、系旗在夕阳的映衬下格外醒目,扩音器播放的国际歌对学生似乎从未如此真实: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讽刺的是,这本来是中共的党歌,如今却成为学生抗议中共诬陷自己的民运之声。整个六四学生运动期间,这支歌都是学生的最爱。
在七号楼学生宿舍的二层楼道里,有学生在精心准备第二天游行用的巨幅横幅:“誓死捍卫宪法尊严!”为了表示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死”字还被泼上了红墨水。这个字上泼的虽然不是鲜血,但当晚的确有很多学生写遗书甚至血书。因为四二六社论写的杀气腾腾,大家觉得如果游行抗议,必然遭到血腥镇压。只是大家豁出去了。之所以说是为了捍卫宪法尊严,因为学生认为自己发动校园民主运动只是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政府却说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就我个人所知,当时学生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其实,正是邓小平在六月四日凌晨开枪屠杀之后,才多了起来。
4月27日早晨,法大的学生准备好上街,江平校长赶来劝阻学生,因为学生上街有可能遭到真枪实弹的镇压。江平表示,学生要上街,只能从他身上踩过去。于是法大学生只好在校门口一字排开,把横幅、校旗打开示威。见状我转向北京航空学院(后来改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钢铁学院(如今叫北京科技大学)。我到北航的时候,警察和学生正在街上对峙。街道两旁的房顶上、树上站满了给学生助威的市民。大家齐声高唱歌颂警察的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电影《便衣警察》主题歌,刘欢演唱)。警察看起来也并不想竭力拦阻——他们只是奉命行事。前面的学生一边正面跟警察对峙,后面的学生则悄悄从校园里绕回大街上,从警察后面出现,这样两边夹击,警察也就被冲散了。我跟着北航的学生沿学院路往西,到法大的时候,法大学生早已经不见了。
比起四二二,这次四二七游行得到了市民更多的支持。在西直门立交桥(当时北京最大的立交桥),学生由东往西经过桥下,市民则在桥上欢迎学生。学生喊:“人民万岁!”市民喊:“学生万岁!”声音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由于这次参加游行的学生远远多于到广场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学生,所以政府最后还是没敢开枪。
镇压不成,政府只好接受学生的建议,开始“对话”。学生要求跟赵紫阳、李鹏这样的实权人物对话,结果只有作为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的袁木出面。袁木的话语是百分之百的官腔、官话,令学生十分反感。学生要求直播对话,也遭到了拒绝。经过多日关于对话的拉锯战,学生逐渐失去了对话的信心。这时,柴玲等人开始筹划绝食,试图以此唤起政府对学生要求民主的诚意的认同。因为政府缺乏对话诚意而在学生方面掀起的绝食运动,把政府和学生朝对立的方向推得更远。
三、绝食
我本人始终没有绝食,只是在广场帮助照看绝食的学生。学生绝食期间,我经常来往于广场与新华门前。因为法大的部分师生也在新华门前绝食。我们的任务是,晚上每隔一小时叫醒绝食学生,免得有人在绝食体弱的情况下昏死过去。白天,广场很热,很晒,学生常常要打着伞;晚上,广场上很冷,需要盖被子。每隔一分钟就会有一辆救护车从广场上开出——昏倒的学生越来越多。救护车凄厉的笛声日夜在广场响起,至今犹在耳际。我们这些在广场上照顾学生的人也非常疲惫,有一次我累的坐在长安街路边的石墩上,疲惫的样子让救护人员误以为我是绝食学生,几经解释,他们才放过我,没有送我上医院。
北京市民在四二二、四二七、五四游行的时候,还都是在一旁观望。绝食使市民和学生走得更近。北京老百姓有一个共识:这些衣着简朴、稚气未脱、才华出众的学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用绝食这样损害自己的方式来表明自己要求政治对话和政治民主的诚意(在李鹏、陈希同眼里这是学生在“要挟”“党和政府”)。所以绝食期间数不清的市民日夜到广场送水、送衣、送钱。游行的市民打出“小弟挨饿,大哥心疼”这样的横幅,朴素而真挚。有一家北京人在学生游行的时候在西单附近设立水站,供路过学生饮水,水桶边有一对联:“愧无美酒酬壮士,凉水热心慰亲人。”至今想来,此景此情,令人对北京市民的同情心和民主意识感佩有加。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我不知道当年国共交战的时候共军是否真的赢得过人民真心诚意的支持,但六四期间学生从北京老百姓那里得到慷慨的支持,却是我亲眼目睹,没齿难忘。这是人民的城市,这个城市不属于邓小平、李鹏。
绝食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学生拒绝为了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大陆而撤离广场。这一举措使得这个运动朝不利于赵紫阳的方向无可逆转的进行下去。
5月14日晚,当时在学生中声名显赫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等人怀着焦急的心情来到广场,劝学生离开。因为她知道,如果学生不离开,李鹏等坚持对学生严厉镇压的人就会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的支持之下得势,而赵紫阳这样坚持“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改革派就会被剥夺权力。学生当然不能懂得这背后的政治游戏。学生只是觉得,他们更愿意在广场上欢迎戈尔巴乔夫这位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有权势的改革派。而且,对学生而言,在其改革主张未被政府作出明确回应、四二六社论也未明确被否定的情况下离开广场,无异于半途而废。这一事件也使得戴晴后来对学运做了不利于学生的解释。在我看来,戴晴本应谅解学生对政治的陌生。当时我在广场,我知道在场的学生很少有人能够明白他们和赵紫阳之间需要彼此的支持和帮助。
六四之后邓小平、李鹏等人硬说学生是被人利用的。这是天大的笑话。正因为学生没有被利用,学生也害怕被人利用,他们才坚持呆在广场上不走,从而使赵紫阳回天乏术,给了李鹏等人借口,认为你赵紫阳来软的不行,我们就来硬的。
的确,如果学生在5月14日晚上听戴晴等人的建议,撤离广场,使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大陆顺利进行,也使赵紫阳的温和政策被证明有效,而不是坚持要求官方明确否定四二六社论,则赵紫阳不会失去权力,而民主改革就有可能继续进行。可惜学生作为一个自发的、成员变动不居的无组织力量(“高自联”这样的组织实际上是学生领袖的组织,而不是学生的组织,因此它不可能掌控学生运动)不可能始终做到协调一致、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始终如一的政治斗争,因此很难像胡平先生所建议的那样“见坏就上,见好就收”,妥善地应用政治战略和策略。于是,在激进的主张总能占上风的情况下,学生民主运动就朝着和共产党内反对宪政民主的顽固分子决一死战的方向不可逆转地前进了: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和共产党的顽固分子(主要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老人)都认为不能妥协,所以只能以冲突告终。
邓小平做好了开枪的准备。
而学生只能用牺牲生命证明自己的良知和勇气。
其实,在这次学运的任何一个阶段,只要邓小平出来见一下学生,表示对学生爱国民主热情的赞赏,表示将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发表或收回四二六社论,学生就不会继续上街游行,更不会在广场不走。邓小平没有这样做。很多人没有看到,邓小平其实是毛泽东式的专制君主,他和毛在政治理念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一个人认为搞专制也需要老百姓富裕一些,而毛泽东则认为贫穷更有利于专制。他们都不是五四民主精神的传人。
看看邓小平等人怎样选“接班人”,就可以了解他们的“民主”是什么。
1989年5月27日晚,政治老人齐聚邓家,推选总书记:
李先念:“小平同志,大家想听你对总书记人选的考虑意见。”
邓小平:比较来比较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的确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我认为他能够胜任这个角色。在总书记人选上,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于江泽民同志,大家有什么意见?
王震:“你们三人说定了就定了,我对江泽民不了解,但我相信小平同志的眼力不会错。就选江泽民当总书记。”(《中国真相》)
吹捧邓,对毛泽东不公平,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同路人。不能因为其中一个突出经济就忽视其雷同。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顶多只能将其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洋务运动”。
四、屠戮
邓小平和李鹏对学生绝食的回应是动武。为此他们在北京发布戒严令,招来野战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
北京人民用实际行动证明戒严的荒谬。
我听说,当军车开到进京的几个路口,老头、老太太就躺在路上拦截,然后有人开来加长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中间,将车放气,人坐在车轮边——北京市民抗议戒严、阻止戒严的人体屏障就这样形成了。
这是1989年5月19日。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里,学生和市民联合行动,维持了首都的治安和秩序。
而且,北京市民还保障了被围军队的饮食供应。
在六里桥,我亲眼见当地群众给军人提供饭菜、水果、饮水。大家一边招待军人的日常饮食,一边做说服教育工作。比如,有一位妇女把两岁的孩子抱到军车上,跟孩子说:“你说,解放军叔叔回去吧!”孩子很腼腆,于是妈妈说,“你不说,长大就不让你做解放军了。”
不少地方,当地百姓还和军人对歌比赛。
北京市民和学生用实际行动证明,北京的秩序无需用戒严来维持。这只能说明,邓小平和李鹏的戒严,只是为了阻止人民对他们专横地行使权力的方式提出的挑战。
1989年6月3日下午六点左右,广场上开始出现官方的广播:不离开广场的,将不保证其生命安全。
这等于说格杀勿论。
最后的关头来到了。
那些日子我一直穿着拖鞋,于是我回到法大蓟门桥校区,换了一双布鞋,又回到广场,那时已是八点多钟。广场上的气氛已经不一样,大家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大家开始往纪念碑聚集。有位女生带领聚集在纪念碑上的学生一起宣誓:“头可断,血可流,天安门广场不可丢!”
晚上10点多钟,我亲眼见一位男生拿着一件尽头了鲜血的绿色军大衣来到广场。绿色军大衣是那个年代大学生冬天御寒的标准衣着。
我们知道真的开枪了。大家情绪激动。
11点多,我和一位朋友到珠市口去看情况,结果看到一辆装甲车飞速朝广场开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装甲车可以开的那么快。我们赶紧往广场方向走,到了正阳门,看到头戴钢盔、手持武器的军人跑步往广场开去。军人过后,我们又赶快回到广场。在凌晨一点左右,军人已经从四方围住广场。
在影影绰绰的灯光之下,从纪念碑基座上远看天安门前、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到处都是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士兵把我们围在中间,真的很恐怖。官方的广播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不保证其生命安全”的保证,天空还经常出现指挥军队行动的红色照明弹,简直是立体的恐怖。
我非常想离开广场。那年我才24岁,刚当了一年大学教师。除了两个妹妹,家里只有我一个儿子。我不想死,为了父母也不能死。那时很多学生在写遗书。我没有写,我知道如果被杀,遗书也不可能被带出去。写了白写。学生也在分发剩下的食物,还有人身蜂王浆这样的东西,一定是好心的市民送的。我没有喝。觉得喝了也白喝。要死的人了,吃喝还有什么意义?
我想离开,但觉得不能离开。我不能承受在最后关头临阵脱逃的良心责备。但是留下来看来也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大部分人不同意用武力对抗军人,因为知道这些军人也多是贫民的子孙,他们也只是奉命行事,杀死他们就等于老百姓之间自相残杀,而这种惨剧的制造者却另有其人。
大概在凌晨两点左右,我终于在心里说服自己,接受死亡的命运:我不能走,也不能反抗,只有死路一条。这时反而平静了许多。我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有一位朋友走过来,抱着我,说,“守东,你是我的好兄弟!”这句话我终生难忘。虽然,我和他最终没有成为弟兄。
我也试图劝说周围的学生,劝他们不要反抗。然而我只是无名小卒,反而招来唾骂:“胆小鬼,你为什么不早离开?”然后我只能选择沉默。
多亏了刘晓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他救了广场上的学生。他见一些学生想反抗,就站起来对大家说:“同学们,凡是今天在广场上的,都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我们多流一滴血,都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我当时坐在刘晓波身边,他的这番话我终身难忘。是他,也只有他的劝说才会奏效。他开始查收学生身边的棍棒,堆起了很高的一堆。他也劝有枪的学生把枪交给戒严部队。也是刘晓波,在清场开始的时候和军人谈判,要求他们给学生留下一条通道撤离。没有刘晓波,少部分打算武力反抗的学生肯定会招来军人对所有学生的屠戮。邓小平和李鹏不会吝惜学生的生命。
实际上,也是刘晓波的劝说和谈判,才使得学生有撤离的机会,也使邓小平在长安街的屠戮没有延伸至纪念碑,使他免于承担更重的罪责。荒谬的是,这样一位对政府减轻罪责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者,在六四以后却遭到官方肆意的辱骂,其权威报道题为“抓住刘晓波的黑手”。是非之颠倒,莫此为甚。
四点左右,广场上的灯全都熄灭。
全场一片黑暗。
借着黎明前的黑暗,邓小平动手了。
胡平先生事后评论邓小平为什么在黑暗中动手,认为黑暗可以模糊人们的视线,淡化人们的良心,可谓一语中的。但我要加一句:黑暗并不能抹去人们心中的记忆。
一小股士兵猫着腰,端着枪,从东面冲上碑座最高处。我从晚上12点开始一直坐在那里。我的身后是五四运动的浮雕。那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这个晚上我都面朝天安门,有时回头看五四运动的浮雕,遥想当年军阀统治下的学生为民族而呐喊,那声音穿过七十年的岁月在我的耳边响起。而我,七十年后,却要和五千名师生在广场上面对一个声称其继承了五四精神的政权的武力包围,仅仅是因为我们想把五四的民主精神继承下来。
1989年6月3日晚上,邓小平用武力给我上了惊心动魄的民主一课。
他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在中国,通过和平的游行、对话方式追求民主,还有可能吗?
冲上来的军人不由分说,在我身后一顿乱枪,我依然面朝天安门,弹壳落到我的后背。我没有看他们朝那儿开枪,我相信不是朝人群。也许他们是为了吓唬我们,也许是要打掉高自联的喇叭。士兵还用脚踹我们,一边踹,一边说,“看你们把广场糟蹋成什么样子!”
这是人民的广场,难道只能在这里对独裁者高呼万岁?
被洗脑的士兵把我们赶走。邓小平占领了广场。
伴着晨曦,我们撤退了。
我们从历史博物馆门前转向西,过了正阳门之后,又从六部口回到长安街。我回头望,后面是长长的学生队伍,看到大家没有劫后余生的兴奋,也没有对武力的恐惧,只有一片静默,有人头上缠着白布条,有人胳膊吊着绷带,很多人打出表示胜利的V手势。
到了长安街,天已大亮。这时突然有坦克车从广场开过来,打催泪瓦斯。在整个学运期间,我们时常担心会有催泪瓦斯,所以经常带着湿口罩(当时防备催泪瓦斯的措施),没想到最后才遇到。我正走在长安街北侧,见旁边有个大门朝南,我们马上进了院子躲避催泪瓦斯。进院子不久,有人趴头往外看,惊呼“轧死人了!”原来是这辆坦克不仅打了催泪瓦斯,还直接朝人身上开去。当场碾倒13人,其中11人死于非命。
其中,有一位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博士。
他的妻子还在法大贴出启示,希望听到在场的人对她丈夫遇难的讲述。
我悲痛欲绝。
据比较可靠的数据,约有一千名市民在军队占领北京的过程中被屠杀。
没有什么罪恶不可以被饶恕,但作恶者必须忏悔,而且,忏悔和饶恕也不能取代正义法律的惩罚。
我可以轻视自己的祸患,但不能蔑视他人的苦难;
我可以饶恕自己的敌人,但无权开脱他人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