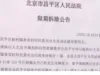在与小马交谈的二十多分钟里,我们的头顶掠过四架飞机。它们可能飞向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目标明确。
八点钟到了,小马打开车门,后备箱里装着他的被褥、几件衣服、从东坝家里带来的电暖气,他即将踏上十七岁那年来京的那条路,方向相反。
回老家之后,从事什么行业、干什么样的工作、走什么样的路,他很茫然。
“人家是记者,你给反映反映”
此时天黑透了,气温降到零下二度,冷的不止是室外。由于断电的缘故,公寓内外一样黑。
我们被领到另一栋公寓的二楼,何大妈穿着鲜红的羽绒服迎了出来,她拎着硕大的手电筒带我们拐进公寓深处,于是我们看到了掀开的天花板上被剪断的电线、一楼屋顶上被绞断的电缆……一个男人跟着我们穿梭过整条走廊,“咚咚咚”敲响每家的房门,兴奋地大喊:“来电啦!来电啦!”
越来越多还留在这栋公寓的人聚在我们身边,“我还以为真的来电了呢。”中年男人从门里探出头来。何大姐拉着他:“人家是记者,你给反映反映。”尽管我们再三解释我们还是学生,但何大妈在随后的采访中,还是将这句话重复了六次。
一群穿着制服的人27日上午在每家每户门口贴上了当日下午6点前必须搬出的通知,何大妈嗓门很大,北方口音浓重:“贴的也是他们,撕的也是他们。我们拽着不让他扯,还不好使。扯了一遍怕落下,还扯第二遍。怕人拍,主要是记者来了,扯了就走。”除了大量的社会志愿者,这天到达皮村的记者难以计数,国外的法新社、美联社,国内的社会媒体、校园媒体凑在一起,水溶于水。似乎于他们而言,记者是这一动乱迷茫特殊时期的一种寄托,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最终整个二楼公寓的十几户人家都聚集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
“真的要往外清人啊?”“不可能的事,他没有公章明白吗?就是一张白纸,没公章白搭。”“皮村不让住啦。”
断电9天,皮村南部在北京市万家灯火的时候漆黑一片。我们被请进何大妈的家里,十几个人在晃动的烛光里抱着手臂,谈论这日子是否有回旋余地。猫蜷在花布罩起来的沙发上,蜷得很紧。
“叔叔给你们提个要求”
公寓一楼的走廊尽头是房东办公室,14年在这里盘下房产开办公寓的刘老板坐在宽大的椅子里,和来访的人们大声交谈着,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两面国旗。他连说几声抱歉,“你们来,连杯热水都给你们端不了。”
除了老刘,还有三家公寓遭遇了断水断电的窘境,这些公寓的投资者此刻都坐在铺着白瓷砖的办公室里。隔壁公寓的陈老板带了醉意,用高分贝连着几次打断刘老板的话,让他“不要给孩子们讲了,他们也不懂”。他举起一盏蜡烛对着我们说:“你们都是年轻人,是不是觉得点个蜡烛很浪漫?浪漫吧?”他骂了一句粗口,“点蜡烛和开电灯,哪个消防隐患更大?”
坐在沙发上的潘老板是东北人,六十多岁,精神矍铄。也是2014年,他来到皮村,投资一百八十余万开了一家公寓,当时签的合约上显示他有十七年的使用权利。
说起断电的情况他愤愤不平。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村委会派人剪了电缆,砸了电表,拆走了电表箱。“我当时说,我一块钱买来的那都是我自己的东西,你凭什么给我拆了?你要不给我还回来,我能跟你拼命。”
在潘老板的带领下,我们看到了电缆被剪断的场景。电缆从二楼拉到一楼,截面直径近七厘米,“你看这,老虎钳都剪不动,搁你小女孩儿,让你剪,要你命你都弄不断。”寒冷让人局促,潘老板跺着脚说安全隐患他可以排查,哪里不合格都可以整改,但他很难接受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直接断电的做法:“就那‘咔嚓’一下,就这么地了。”
不久前,居民们看到穿着制服的人来剪断电缆,这些人在许多居民口中被频繁提及,他们也是当时把手机镜头对准我们的人,被称为“联防”。后来遇到的保安这样形容:“我们就是小保安。人家联防牛逼哇,什么都管。”
27日下午三点左右,村里来了一队人,贴了一溜没有盖章的告示:要求六点之前清退所有居民。潘老板问保安,为什么没有盖章。来者言辞隐约,支支吾吾,“没有时间”、“来不及盖”。虽然告示上没说具体措施,但是他们口头警告,如果不能清退,就要扒门扒窗户、把居民的物品全都清理出楼。
当时正好有两位美联社与法新社的外籍记者前来探访情况,录下了整个告示张贴的全过程,潘老板说,当时他检查了两个外籍记者的记者证,确认了身份后才让他们采访录像,“咱们中国人,都是自家人,聊聊天可以,牵扯到外国人,不能乱说。”之后大概半小时,又来了一队人,将告示全都揭掉了。“要不是那两个记者,估计你们现在能看到更热闹的场面。”
没有明确的通知、没有清退的理由,这场不打招呼的断水断电带来太多疑问。“为什么这么多家公寓,只断了我们这四家?为什么不说是什么原因要断电?”潘老板认为,如果是因为有非法行为、或是有需要整改的地方,至少要做出相应的通知,阐述合理的理由,让住户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再进行断电。
北京的冬夜里,青壮年尚能勉强熬过,但老人与孩子又该往何处去?
“你的尊严在哪里啊?你的人权在哪里啊?中国梦怎么做?就这么做?”
再被问到未来的打算时,潘老板的情绪又一次激动了起来。“我六十多的人了,老人也不在了,儿女也成家了。我光脚不怕穿鞋的。要是不给我个交代,大不了同归于尽!”
而后他的神色温柔了些:“如果你们回去要报道,就客观的把你们看到的事实情况写出来就行,不用夸张。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真的,保护好自己!”
我们回到办公室,不大不小的空间里依旧人声嘈杂。坐在椅子上的刘老板站起身来,大嗓门地说:“咱们今天就是纯粹聊天,我就把你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希望你们都能好好完成学业,长大了,要做对国家、对家庭有贡献的人。但是叔叔给你们有个要求:千万千万要呵护、爱护底层的低端人口。”
他把两个“千万”咬得很重很重。
“天下哪会有这么好的事呢?”
工友之家在皮村西门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往右,是志愿者们的办公室和打工博物馆,对面则是一些工友们住的地方。从创始人孙恒和王德志2005来到北京开始,就维持着基本面貌。平日里,工友们会聚集在这儿跳广场舞、打乒乓球、看电影、唱歌、看书,而当天,原本只有两三个人呆着的志愿者办公室成为了整个院子最热闹的地方。办公室右边墙上皮村的地图和左边墙上的“两岸三地打工艺术交流营”几乎成了所有人进门时,相机第一时间对准的焦点。
室内几乎被各路媒体塞满,呼出的二氧化碳和摆在房间中央的电暖炉让这个不到十平米的屋子暂且和室外零下的温度隔绝开来。而志愿者涂俊南仍然穿着整齐,甚至连围巾都没有摘,他这身衣服已经穿了三天,并且还将穿第四天。和很多人一样,上午才听到消息的他匆匆赶来帮忙,没有料到会在这里度过他的周一晚上。而另一位志愿者武豪,作为救助信息传单上的联系人,他的电话从我们一进门开始就没有断过。
人流涌入皮村,为这个小村庄注入了不属于它的活力。就我们所见,来皮村的人身份复杂,多家媒体、志愿者、学生……志愿者因为多是线上自发而来,缺乏组织性。我们碰到一个独行的志愿者,她小心翼翼地问我们:“你们是XX来的吗?”在我们否定后,她有点焦虑,“我也不认识他们,天这么黑,走散了。”
而工友之家的志愿者遇到了不同的困难。事实上,工友之家在皮村南部的影响力不如报道得那么大。我们在皮村的小巷子里迷路时向村民询问:“请问工友之家怎么走?”换个问法,“打工博物馆呢?”得到的大多是茫然的摇头。“如果你说工友之家、打工博物馆,他们可能不知道,但如果你说我们是那个常常搞活动,跳舞放电影的,大家就‘噢~’”涂俊南半是骄傲半是无奈地笑了笑。工友之家和工友的关系并不是领导和从属的关系,而是更像一个NGO(非政府组织)。
更多的阻碍还是来自于不信任。“他们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天下哪会有这么好的事呢?’我们反复解释,说自己真是纯公益的、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和政府没有关系,他们才会收下我们的传单。”我们之前遇到的三姐弟的父亲,像见了鬼般连连摆手,拒绝了涂俊南的传单。
而从这位父亲住的金宏公寓上二楼,左转,墙上贴着不知什么时候的“新北京,新地铁”地铁图,像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从海淀区到皮村,要转三趟公交,共计三十余站,而如果转乘地铁则更加麻烦,需要换乘四次。事实上,皮村大部分的工友都只是在夜晚暂住于此,在皮村本地的小厂工作的只有极少数,大都需要白天早早地赶往上班的地方。拿在银行做保洁的徐阿姨来说,因为只有公交一种方式可供选择,六点半上班的她四点半就得起床,赶往皮村村口搭乘五点半始发的公交车。
同样早起工作了一天的武豪和涂俊南早已掩饰不住自己的疲惫,随着一波又一波媒体的到来,两个一开始正襟危坐的年轻人已顾不上体面,寻找了一个更适合长时间坐的姿势:翘起了倾斜成同一角度的二郎腿。因为27号的突发情况,他们本计划在当日完成的以皮村工人为主题的剧本已经延期了,涂俊南从城里带来写剧本的电脑甚至都没有机会打开过。
皮村的迁徙开始得比通知早得多,网上可见的报道中,去年10月就已开始有此类通知。这场迁徙没有具体时间节点,武豪作为皮村工会长期以来的志愿者,几乎目睹了全过程。“开会以前,就说环保整顿,开完会继续环保整顿。”但事实上,皮村北部的工厂都是一些组装类的小厂,没有烟尘,也排不出什么东西。
大会期间工友们高高兴兴回家了,有的家里要忙着秋收,而有的不需要帮忙,“就当是放了个假”,假期结束后继续来上班。但开完会回来,厂子仍然迟迟不能开工,再找工作,很难。皮村北部的工友们没了工作,只能陆陆续续开始搬离,皮村北部和这次贴公示的南部不同,早已没什么人了。
皮村只是一个因为得到太多关注而争取到96小时额外撤退时间的特例,但搬迁不是。更多北京周边的村子没有发声的机会,就被抹去存在的痕迹。
早早和皮村北部一起迁徙的还有位于皮村西部的东坝,那里也是小马居住过的村子。并没有引起任何关注的它,早就悄无声息地进行了一场大兴式运动。之所以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武豪坦言:“我觉得是这一次的规模太大了,是全市范围的,之前拆东坝的时候,人权什么的也是没有的,说拆就拆,而且是拆不是赶呀。”同在金盏乡的楼梓庄也是如此,尽管现在坐公交车,还能看到和楼梓庄有关的站名,但无法找到这个村子的行政单位——楼梓庄已经沦为了一片废墟。
相比之下,27日的皮村相当温和平静,除了停水停电外,目前为止没有出现暴力拆迁的情况。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房客前几个月刚从车各庄搬过来,落脚没多久,他在皮村的新住处也开始停电停水。经验丰富的他知道这是让他们搬家的前奏,立刻动身找房子,准备过几天又搬走。下手快的他找到的新房子一个月只要八百,虽离皮村还有两公里左右,但已经是我们走访的住户中租到的最经济实惠的房子了。
为了能继续工作,搬、搬、搬,这个村子不能住了,就找下一个能住的村子;为了有个落脚的地方,搬、搬、搬,房价从五百涨到八百再到一千八;为了节约生活成本,搬、搬、搬,直到离北京市区越来越远,最后彻底地消失于行政区划。
皮村离飞机场近,所以房子不能修高,只能一点点向外扩张,无数的两层小楼见缝插针,这让它看起来更加密集与扁平,成为北京“城中村”的典型标本。人们普遍认为,皮村离机场近,修不起高楼,房子不会被拆,安全。现实却唱了一曲反调。
如今,飞机照常从头顶上划过,载着不同的人奔向世界各地,却无法载着皮村人民落地生根的文学梦、航天梦、北京梦,去往一个确定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