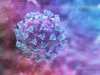我知道,揪着时代来纪念某些人物,就如进行一场心灵的撕裂。这样的伤口有多大、痛感的尺寸能多深,自己也不甚了了。就这庚子年,从故旧的联繫到现实的想像,在一条很悠长的轨道上,不断地响动着你不想看或不想回头的往事。而且,清明节说来就来,感觉就是一种鬼魅的节奏。这一回,可以预料“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凄惨情景;而九州大地上,人们只要登上坟头,那定会仰望一阵清明的天空,让思绪飘荡,最终联想起庚子的病毒之灾。
本以为,疫情的阴霾依然笼罩,大概许多人扫墓也难,过程的麻烦会大于一切。果然,从家乡传来的消息,说为了防疫安全,县里封山了!也就意味着所有人的家庭,都无法在清明这个时节去扫墓拜祭,成为空前的清明现象。我不能说这种决定是否又是一种极端,但或许在这非常时期可以勉强着凑合。对于依然面临瘟疫的威胁,暂时破了老规矩的怀念故旧、寄託哀思,这样被阻断的不爽,大概只是冷春里的“毛毛雨”。
我是回不去了,虽闽东那老家,感觉有着最浓郁的清明气氛。而家乡民风淳朴、人们多为善良厚道,对传统优良习惯的沿袭似乎也毫不含煳。纪念起祖宗先辈来,那几分情感流露是摸得着的虔诚。每年清明,我都要努力回去一趟,尤其双亲故去之后。故乡怀念的意义大多维繫在祈福之上,如同万物的存在都是围绕着人的目的。失去了亲人,家乡便成了故土;倘若没了对故人的怀念,对活人自由快乐生存的指望,那所谓家乡、故土也是形同虚设。
此刻,我在想像着自家从祖父手上起立的墓地。其实,祖上的那些关係亲缘以及他们的过去我无一知晓。从祖母口述中,大概知道那是一拨靠耕种生活的农民,从祖父起才漂泊到这个山外之域,稍稍改变了家族的命运。对我的祖母,她做人的明理、通透,良善、大方,慈爱、关怀,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最深刻而美好的家庭记忆。在县城西北角的山坡上,有我近30年前为祖母撰写的碑文。如今,故土的亲人变得越发遥远,而我的死期自然也是越来越近。
人类可以坦然地面对的生老病死。现代社会,也没太多人会去在意一个寿终正寝者的死,除非他们有什么丰功伟绩,或又是什么名人之类,但也多出于某种的尊敬、礼貌乃至应付。至于真的悲痛,我以为也是绝少的。所谓“重于泰山”者,在今天的世界实在稀少,因为什么时代与环境,便相应出产什么样的人类或人物,这很正常。像司马迁那样看重生命价值,而从容承受极端苦难的官员或学者、文人,彷佛一时还找不到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回不去的清明节,我就自然该写一篇文字。来纪念一下逝者。眼下,遭遇国殇的清明,当然会将目光转向灾难中消殒的人群,特别是为无辜所施加了死神法力的人们。他们的确是不该死的,但为道义、为尽职,在一种複杂的事件推动下,让死亡有了一层非同寻常的意义。若从社会学家的视角看,这样的不幸,却可以观察出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品质优劣来。但我不仅仅属于好奇,也要加入自己的某种判断:生命依然可以常新,可历史没有完全成为历史。
近日因重读鲁迅,难免多有受先生文章及思想的几重感染。这当然也属于重新“中毒”,只是它更像是接种了“历史疫苗”,具有以毒攻毒的效果。许多上了一定年纪的读者,应该都还记鲁迅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那是为纪念五位“左联”作家烈士而写的。他们是一群先生认可的朋友,为追求真理、实现一个自由平等光明的社会,而试图以手中的笔来抗争的年轻人。在那“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时代,鲁迅知道怎样当一个长者与挚友。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鲁迅以如此沉重的笔墨,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失望与苦闷。一个对生存清醒与自觉的人,会诞生出无穷的思绪与思想,也会生发出纯粹的情绪与情感。而时代与作家,如果彼此的关係是正常的,那么敏感与紧张便会如影随形。或许这也是宿命。
时代的确还是有些不同了,人们也看不到旧时期两个敌对阵营前方拼杀、后方宣传的阵势。一切的空间,也都是胜利者的现场。若还有所谓的“敌人”,除了对外部的假想、社会矛盾的价值观念,馀下便是内部利益分配或佔有的噼叉。但如此这般,我等一些人,依然还是会有像鲁迅先生所感慨的“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的坚持、无奈与疑问。
但有一点却是惊人地相似,那就是道真相与说真话的困境。一个偌大的足以发出雷霆之声的世界,怎么就一直是一个只能供养呼吸的“小孔”呢?武汉的冠状病毒所以无限蔓延,造成另外陡增的“百分之九十五”感染者,正是缺失更多有力的“吹哨人”。如果可以立竿见影的公权力,不是时时为处在维护公民利益,守护在可能发生危险的边缘,那么,“为人民服务”的题中之意,就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党员李文亮,美好的一丝愿望也难成现实。
在灾难中去世的李文亮医生,当然不是什么特别伟大的人物。人们给他赋予一个“吹哨人”的称号,实际上也非名副其实。他只是一个平凡但却很正常的人,有良知,关键时刻能说真话。据从媒体上获得的消息,他是被派上战场的。当然,我坚信,即便不是被派遣,他这个有现代常识、热爱生活的医生,哪怕擅长的是眼科,依然不会贪生怕死而走向前线。我非常厌恶这场该死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我还是要深深致敬与哀悼那些包括医务的战士。
4月2日有则新闻,说李文亮等14人被追授为此次抗疫中的首批“烈士”。是的,他们死了,在对抗瘟疫的第一线。他们原本也没有想要当什么英雄或烈士的,谁都会珍惜自己的生命,尤其处在和平的年代,就没有找死的充足说法,或更无慷慨赴死的理由。特别是李文亮,处在一切正常的职业与人生的路上,竟为一场莫名的病毒来袭,一次对身边人的忠告,被莫名“训诫”,在背负冤屈中前往一线去救死扶伤,然后再于染病中含冤离世!
对于烈士们的评价,人们自然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再关注,而最痛心的莫过于他们的至爱亲朋。虽然他们都是瘟疫的受害者,但这其中的李文亮,在这清明节里,却是最值得单独而特别的追悼或思考的。人们当然不会忘记2020年2月7日那天晚上,几乎是整个武汉城都在为他点起了蜡烛。这是一种情绪,或是一种精神。它是民间的,也是纯洁的。直到今天,他的死、他的悲,依然还笼罩着一层无法捅破的神秘。也并非“烈士”就能够盖棺定论。
李文亮终于也成了“烈士”,这是我所完全没有料到的。他是从“小丑”变更为英雄、从屈辱逆转为荣光的。这也是当代人类少有的奇迹现象。在14人的烈士名单中,人们读到一段外加的特殊说明。这如同对突然爆发的疫情採取紧急举措一样,也属于一种亡羊补牢。显然,已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那道如天崩地裂的痕迹,不是简单地留在昼夜的大地,而是刻在人们心灵的世界。历史也将会不断疑问:怎么会有像李文亮这样的烈士呢?
但这样的疑问,似乎也不能一桩了之。近日在武汉,居然又有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战疫“庆祝活动”。我之前就曾发出过告诫:对于瘟疫的发生,人们只能努力减灾。那失去的一切都已无法挽回!面对灾难,我们没有胜利,只有结束!那么,为什么又会有庆祝呢?其实这是常识。江城的庆祝我以为是不能被接受的。庆祝也难免要鼓励喜悦的。而我们,面对那些无辜的上千,不,也许是更多更多不幸的死难者,何以喜悦,褪去晨露一般的满园悲伤?
终于,国家的公祭来了!今天,4月4日,全国哀悼。我听到窗外的一阵汽笛声。我不知道远在武汉主场的人们,会以怎样的心情融入这场纪念中。我上网极力搜索相关的资讯,但是却看不到太多私人悼念的场面。只是几张排队等领骨灰的殡仪馆的长龙。还有一段对话文字:“阿姨这是哪里?我们来这里干什么?”王阿姨忍住眼泪:“这里是殡仪馆,我们来接爸爸妈妈回家。”孩子雀跃着,“太好了,爸爸妈妈可以回家了!他们好了吗?”
埋怨,愤怒;忧伤,绝望,抑或是更强烈的希望?我不知道这里面的具体成分、比例。在我的脑海里,此刻有太多以往不同灾难的历史汇合。尤其是那些之前死于政治斗争运动、之后亡于类似矿难这样人为事故的无辜生灵。一个国家在默哀之后,是否从此凝聚起一股与国民血乳交融的状态,共同拒绝人为的悲剧;是否一道理解所有平凡生命同样珍贵,让一次次相似的、黯然神伤的眼泪不再掉落?假如不能刻骨铭心,公祭的汽笛又是为何而鸣?
在今天微信中,遇见了这样对这个意外纪念日的表达:“和所有的公祭日不同,这次,我不仅悼念死者,同时也悼念我们自己······悼念所有书本里描述的世界和未来;我们悼念越来越远去的真理,悼念我们这一代人、几代人付出过的打拼;我们悼念每一条小溪、每一朵浪花,悼念我们栖身其间的这片土地;我们悼念激励过我们的召唤、悼念我们欢乐时刻的每一滴泪水······”这样富有色彩的悼念描述,让人们更能体验某种无法填补的纪念的空洞。
人类发生的数次大瘟疫,也许我们只能回顾那些死亡的冰冷数据,却无从体验史上所经历的惨痛程度。但是,对刚发生在自家门前的庚子年瘟灾,则是能真实面对、触摸其间伤痛的点点碎片。武汉作家方方所提供的,只是其中的构成,也许并非最不堪最悲惨的那部分,毕竟更多的现场无从想像。可从她的视角,再加之各种流露出来的具体伤害过程,或还有理性冷静地分析推断,这场天灾加人祸,足以让人们思考:人类为什么会如此无辜与脆弱?
如果说一场瘟疫会造成天怒人怨,这背后原因自然值得深思。客观说,我们所经历了让病毒肆虐并伤害无穷的事件发生,证明了某种冷酷的存在,这等冷酷直接来自人性与常识的重大缺陷。它还以蔓延全球的姿态,来表明这种灾难依然在考验着这个最新的世界。八十年前,作家加缪就将瘟疫比作与战争一样的人类灾难。在他的《鼠疫》中这样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瘟疫;没有一个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免除得了的。能够对抗瘟疫的,就是正直。”
我们显然没能看到事件发生时,加缪所指的“正直”的强大。甚至在不断地忽略,不断地漫不经心,以一种谬误掩盖着另一种谬误。就如事后许多人都意识到的:如果提前三个星期,或再提前一两个月,人们就无须承担今天这样的惊天大灾,无须劳动巨大的人力物力、时间金钱,去应对一场无谓的、伤筋动骨的病毒战争!不是吗?就为一条数人间传递的真相与疑虑资讯,便有了从“训诫”到“全国警示”的大动干戈。随后接着隐瞒,接着扩散!
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知识界人士开始回过神来。不少学者也开始认真检讨,从社会学或文化学乃至经济学的角度,来重审这场瘟疫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也有人忘不了那在严冬的灾难中挣扎的场面,感慨武汉城中流动的酸楚、艰难与绝望。同时也感歎于那么多的以外的人,对重灾区投注了真实滚烫的热情、以勇敢的生命拯救危险的生命。灾难如同一剂激素,注入人们的精神肌体,使人类真相的呈现也判若两面:善良与邪恶。
有篇新文章,作者是香港大学SPACE学院刘宁荣教授。他对眼前发生灾难后的社会反应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在同一个时刻、为同一个人、为同一件事发出我们谦卑的声音,吹起我们的口哨声?而这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希望类似的悲剧可以再少些;希望我们无需生活在不必要的恐惧之中;希望这个民族无论何时都是被人敬重的。”这种觉悟,当然不止局限在对瘟疫的防范,而更是人类对自身责任当担的期待。
冠状病毒的氾滥成灾,已令近日的世界浑身哆嗦!因为它,百万人的身体已受到感染侵害,甚至又导致了中外不同程度的人道主义灾难。对此,是否能够瘟疫及时发现、消息及时发佈和手段及时实施,人们正重新从文化与制度层面,进行优劣不同的追踪和思索。问题甚至深入到民主与威权的体制比较。儘管我并不赞同所谓“多难兴邦”的简单说法,但是,对已发生的灾难,果真痛定思痛、刨根究底,断除孽缘、革故鼎新,方可真正民福邦兴!
灾祸的蔓延引发了所有思想者们的高度关注。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撰文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目前本世纪最大的全球危机,其造成了广泛深刻的巨大影响。”他还进一步认为,“迄今为止的国际合作严重不足。如果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不能搁置谁应该为这场危机负责的口水战并转而更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那么这两个国家的信誉可能都会受到严重损害。”这种警告,足以让人为之警醒。
如果一场巨大的灾难与死亡,都无法唤起一切必要的思考和改变,那么这样的民族真就没了指望!可以肯定的是,眼下对灾难问题的思考远未形成规模与深度。尤其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来看,即便是这样“就事论事”的探索反思,未来也同时会伴随更为複杂的是非,甚至是悖论。其原因在于:我们有一个并不太清新的思想界。对于常识,对于逻辑,对于人性,对于文明,似乎都缺乏进入社会体验层面上的共识。
相信今日之公祭,能安抚那些罹难者的在天之灵。末了,作为卑微的个人,我也依然要跟随着,给以他们深切的哀悼。而对说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的李文亮医生,我还是自己的那句话“有一种悲壮,是他自己给的;有一种无辜与屈辱,却是社会的无情馈赠。”我期盼着,因为他和其他人的死或牺牲,使所有的社会信仰与主义走向真实,开始学会向每一个生命的尊严低头。而不是依然那样高高在上,云里雾中。
2020.4.4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