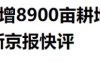1958年在公社化进程中大办公共食堂,被视为进入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办不办食堂、吃不吃食堂被看作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批判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条重要的罪状就是反对办食堂。《人民日报》报道过一条消息,说云南有个“右倾分子”反对群众办食堂。群众说我们的食堂是“雷打不散”,那位“右倾分子”说“我就是雷公,就是要把你们的食堂打散”。这是作为反面典型来示众的。在这种形势下,农村几乎是社社有食堂,队队有食堂(当时的生产队相当于1961年以后的生产大队)。
北京虽没有普遍搞食堂,但在“大跃进”高潮期间,饭馆吃饭自行付费,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爱给多少给多少。每天我在菜市口的“南来顺”吃早点。一天早上,一进饭馆就大吃一惊,屋子中间是十多张方桌拼成的一个台子,放着油饼、烧饼、麻花等食物,旁边有大桶,里面是豆浆、杏仁茶等。这些都是任君自取,四周的方桌上有小笸箩,中有零碎钱币,由君自行付款。饭馆里的人比平常多了好几倍。油饼等一端出来都是一抢而光,“南来顺”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又改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南来顺”的一位老职工说:“赔不起啊!”那时,人们仿佛到了君子国,如此随意地对待经济,经济难道不会报复吗?
1959年秋天报复就来了,先是商店的东西越来越少,购物票证越来越多。什么时候进入困难时期?在我看来有个标志性的事件,那是在1959年“十一”以后,有个秋风萧瑟的早晨,人们起来买早点时发现北京人习惯吃的烧饼、果子(炸果子,一种类似油条的食品)、油饼、豆浆、杏仁茶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菜粥”。这件事给北京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因为大多数北京人早上没有吃菜粥的习惯,当时所有的饮食摊点都是国营的,要变一律都变。困难的缓解也可用早点铺的变化作标志,1961年冬天一个早上,所有的早点铺都支起锅炸油饼了。而且很奇怪,油饼炸出来都是白的。我曾问过,是不是没炸熟?回答说,这是大油(猪油)炸的,怎么炸也不挂色。
1961年春末夏初,通知我们下乡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由于经济困难,本来大学生停止了下乡劳动等活动,这次是个例外。当时食品奇缺,农村饿饭现象很普遍,而干部则利用权力多吃多占。有民谣说“书记拿,队长偷,社员缝个大衣兜”。“十二条”基本原则是局部改变1958、1959年的激进做法。如确定农村所有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办公社时强调“一大二公”,许多县就一两个公社,这次退到一个乡一个公社;又如制止“一平二调”,平调老百姓的财物尽量退回,退不了的作价赔偿。我去的是北京郊区的一个生产队,那真是凋敝不堪,触目惊心。我住在队部,因为常停电,天黑就睡,早上起来,仰望天花板,很奇怪,怎么是黑的呢?天大亮了,我站在床上穿衣服,空气一震动,轰的一声,天花板好像裂开了,原来夜里天花板上聚满了苍蝇。生产队很穷,惟一的大牲口是一条瘦驴。负责饲养瘦驴的是个“富裕中农”,所谓“富裕”只是个成分了,他饿得瘦骨伶仃,眼睛都有些发蓝了。就这样,有个社员还到队部告发他,说他偷吃驴饲料——糠,而且拿着他的粪便作为证据。
下乡的第一件事是劝导老百姓种“十边地”(指沟边、路边、屋边、河边、池塘边、田边等),并说“谁开垦谁种,谁种谁收,谁收谁有,二十年不变”。社员不相信,当面就驳斥我,什么二十年不变,搞“‘初级社’你们说二十年不变,不到两年变了”;“‘高级社’也说二十年不变,结果不到一年变了”。我只是个19岁的学生,根本解释不了。问一同下乡的教务长,他含混地说,不要管它。
第二件事是解散食堂。“十二条”中还说“公共食堂制度,必须坚持”。还有“办好食堂”的指示,我下食堂帮厨,名义叫食堂,真辜负这个好名字。“食堂”只蒸“豆面窝头”,开饭就是社员来打窝头,端回家去吃。所谓“豆面”不是用豆子磨的,有人说是用榨过油的豆饼磨的。面粗而轻,有些像锯末,蒸好的窝头一拿就碎。像我这样一顿可吃一斤馒头的小伙子竟吃不下一个窝头,然而社员还常常为给他的窝头掉下一块而争吵。还好下乡不到一个月,传达了中央给农村干部和社员的一封信,其意在于解散食堂。不过话说得比较婉转,说“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食堂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吃食堂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前面留了“吃食堂”两句恐怕是为了显示与以前的宣传的承继关系。这封信一宣读,社员大乐,食堂马上散伙,连一天也不等。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看到农民发自内心的乐。食堂把粮食按定量分给个人,还好,北京农民还有锅,不至于粮食拿回家后没法做熟。
下乡不到两个月就返校了,解散食堂很成功,宣传种“十边地”则被顶了回来。后来曾碰到当地社员,问起“十边地”,回答说老百姓还是种了,又说能种一季就种一季,收的粮食吃到肚子里谁也拿不走。
这次下乡还有两事可记,一是有位同学胆子真大,竟敢搞“包产到户”,把他所在生产队的田分了,当时就受到校方的制止和批评,可是这曾使农民兴奋。二是我所在的生产队中有位菜园子的“把式”(当地以种菜为主,从外面聘请有种菜技术的师傅)姓李,他教给我许多种菜的知识。我曾说“李师傅,我一定请您吃顿炸酱面”。他笑了,说“等五月节小货(指园子里速生的小白菜、小菠菜、青蒜之类)下来罢,让你们吃点真正的鲜菜”。我存了些面票,准备让他吃个够。可惜的是不到五月节(端午)就被召回学校,那个邀请成了一句空话。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每想起此事都有些遗憾,眼前还会浮起李师傅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