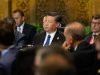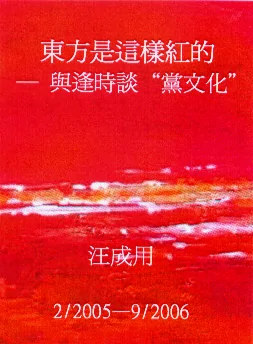
(五) 血色黃昏——“黨文化”的衰敗
“主義”真空的“改革開放”與“盛世”(上)
成用﹕有學者把我們目前所處的時期稱為“後文革”時期﹐對此我十分贊同。文革並未結束﹐文革思維正在以另一種形式繼續。
逢時﹕“後文革”時期的大部份時間我們生活在美國﹐對於中國大陸在這個時期的文化﹐也許難有身臨其境的觀察與深入的分析。能否僅作粗線條的概括以供討論﹖
成用﹕首先的問題是﹐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到“三突出”﹐在此之後﹐中共還有沒有新的文化 “理論”﹖
逢時﹕從本質上說﹐中共在文化領域內向來是有政策﹐無理論。
成用﹕是否可以說﹐“後文革”時期雖然並不缺文藝政策﹐但中共似乎越來越沒能力把這些政策“理論化”。政策也是朝秦暮楚﹐“機會主義”和 “實用主義”的特性更為突出。
逢時﹕不僅文藝領域﹐總體上也是如此。鄧小平的“貓論”與“摸論”難道可算是“理論”﹖實在是連政策也算不上。
成用﹕江的“三個代表”故弄玄虛﹐倒使我想起了文革時“著名”的歌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逢時﹕你是說其中“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語言暴力﹖
成用﹕按照當時社會上的說法﹐這叫“重複就是力量﹐羅嗦就是重點”。當你說不出什麼道理的時候﹐就使用文革式的“就是好”為自己壯膽。“三個代表”可以說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變奏曲﹐共產黨“就是先進﹗就是先進﹗就是先進﹗”。
逢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還堅守“四個堅持”﹐到了“三個代表”的“盛世”﹐中共給國際的假象似乎只是一心“和平崛起”﹐對“主義”不再感興趣﹐什麼都可談。
成用﹕就連當年的頭號敵人﹐國民黨“連爺爺”都回來了﹐還有什麼不可談﹖一時間﹐“共產黨變了”的論調很是流行。
逢時﹕其實﹐共產黨從來都在“變”。當年毛澤東曾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幾年後不是把“蔣匪”趕出了大陸嗎﹖忘記了這一“變”才會對“連爺爺回來”之“變”受寵若驚。一切為了利益﹐不顧原則的“變色龍”是共產黨的特性。“共產黨變了”的論調﹐正好道出了它從未改變的本性。
成用﹕不管再如何變﹐共產黨仍姓“共”。一黨專政沒有變﹐謊言加暴力沒有變﹐為坐穩江山不惜一切的底線沒有變。
逢時﹕還是那句話﹐只要天安門上的“毛像”還在﹐中共就沒有變。
***********************
成用﹕有人認為﹐在“後文革”時期類似當年對毛澤東這樣狂熱的歌頌已基本絕跡﹐並出現了不少揭露社會問題的作品。對此你如何看﹖
逢時﹕歌頌作品並未絕跡﹐只不過形式有所改變。這並不是歌頌文化的改弦易轍﹐而是歌頌的對象起了變化。“後文革”時期共產黨內不再有像毛這樣的強權人物。事實上﹐鄧小平時代有歌頌鄧的“春天的故事”﹐江澤民時代有歌頌江的“走進新時代”。到了所謂的“第四代”﹐只因溫家寶到地方視察時為拿不到工資的民工說了句話﹐就出了個歌唱溫的“百姓的事比天大”。
成用﹕聽說目前中國已出現了歌唱“八榮八恥”的歌曲。如此“緊跟形勢”﹐作曲家們累不累﹖既然毛語錄的“再版前言”都能通篇譜曲﹐我看“八榮八恥”說不定能寫個“交響大合唱”。
逢時﹕只要文革的思維依舊﹐這並非不可能。
成用﹕你是否注意到﹐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變革前後﹐往往會出現“現實主義”的回潮。
逢時﹕有道理。遠的不說﹐就說七十年代後期鄧小平在否定華國鋒建立“鄧時代”的過程中﹐“傷痕文學”的出現就是這一反映。
成用﹕初期的“傷痕文學”具有“批判現實主義”的傾向。以反思 “反右”與文革為主要題材﹐不少“傷痕文學”作品開始試圖走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框架。應該說﹐初期的“傷痕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當局的默認﹐因為鄧小平在其絕對權威建立與鞏固的過程中需要現實主義的批判性。
逢時﹕可是別忘了﹐鄧小平對文革有限的否定以不觸動共產黨的統治為底線。因此他無法容忍“傷痕文學”中隱約表現出的對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的懷疑。
成用﹕1981年開始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运动首先拿走得最远的白樺的《苦戀》開刀。由於當時胡耀邦盡力主張避免再次出現類似文革的整人运动第一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才沒有造成太大的災難。直至劉賓雁等人的“報告文學”出現﹐鄧小平終於忍無可忍了。1986年底開始的又一輪“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不但把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等人一棍子打死﹐胡耀邦本人也遭受了滅頂之災。至此﹐“現實主義”的精神啟蒙經歷了十年的沉浮﹐正式宣告夭折。
逢時﹕我們今天回頭來看“傷痕文學”的起落﹐可以說這是一個 “批判現實主義”在中共“黨文化”的笼罩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实例。
成用﹕“傷痕文學”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是其痛定思痛對文革和 “反右”進行反思的感召力。可惜﹐還未正式進入主題﹐這一潮流就令人瞠目地轉向了向“黨媽媽”的撒嬌而變了味。
逢時﹕一個具有獨創性的說法是﹐把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殘酷整肅比喻成“媽打孩子”。這一“三綱五常”式的“孝子情懷”﹐可說是“奴性”加 “痴情”的“結晶”。 
成用﹕以當時紅極一時的《牧馬人》﹑《天雲山傳奇》等電影小說為例﹐儘管主人翁無一不被黨整得死去活來﹐但最終卻導向把黨“母化”的“宏大抒情”。作品反復宣傳的邏輯是﹐儘管你打了我﹐你還是媽﹐我仍然愛你。
逢時﹕在西方﹐打孩子可能會以“虐待孩子”罪被告上法庭﹐因為孩子也是有獨立人格的人。
成用﹕而在中國向來對“媽打孩子”有各種美言﹐什麼“棒槌下面出孝子”﹐“打是疼罵是愛”等等。
逢時﹕可若是把孩子打死了怎麼解釋﹖難道還是“疼愛”嗎﹖
成用﹕不管怎麼說﹐對“媽”的愛必須是無條件的﹐非此不足以感動自己。在“自我感動”的高潮中﹐“虐待狂”與“被虐待狂”含淚擁抱。“媽” 慷慨又慈祥的“平反”更使“孩子”們感激涕零。
逢時﹕其實﹐對共產黨的“母化”並不始於“傷痕文學”﹐那個在大陸家喻戶曉的歌曲“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就是一個經典。早在文革前﹐“黨”已借一個可憐的士兵之口而實現了自我“母化” ﹐人民便都成了“黨” 的兒子。
成用﹕兒子要孝母﹑戀母﹐就必須轉過身來對“媽”的敵人施暴﹐要“奪過鞭子揍敵人”。這一觀念被反復灌輸﹐日久天長﹐兒子很難不變成只會愚忠於“黨媽媽”而失去普世人性的那個士兵樣的變態人。
逢時﹕白樺的《苦戀》之所以觸怒了“媽”﹐就是因為挨了打的 “孩子”以自己的死向“媽”提了個問題﹕我愛“媽”﹐可“媽”為什麼不愛我﹖據說電影結尾時﹐死者的屍體呈問號狀俯臥在地。這明明是不懷好意地向“媽”挑舋﹐當然無法容忍。可見﹐“傷痕”雖然可寫﹐但必須“好了傷疤忘了疼”﹐舊事不得糾纏﹐要向前看。
成用﹕把“傷痕文學”納入“黨文化”軌道的關鍵﹐是主題重新回歸對黨的歌頌。這樣﹐“傷痕文學”就變成了大家所熟悉的“歌頌文化”在“後文革”時期的變體。今天﹐“傷痕文學”已與真正意義上的文革反思擦肩而過。它留給時代的唯一“遺產”大概就是今天盛行的“青春無悔”。
逢時﹕原來“青春無悔”並非僅僅是豪情壯志﹐還有其“文學”背景。
成用﹕“改革開放”時期十分流行的一個電視系列片《共和國之戀》中有一首歌曲﹐歌詞是這樣的﹐“在愛裡﹐在情裡﹐痛苦幸福我呼喚著你。在歌裡﹐在夢裡﹐生死相依我苦戀著你……”
逢時﹕行了﹐到此為止吧。就這麼幾句﹐挨了打的孩子那種畸形變態的“愛國情懷”已呼之欲出了。
成用﹕這首歌也是“苦戀”中的“傷痕文學”的真實寫照。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及所有無辜人民的整肅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行。受迫害者應義正詞嚴地追究迫害者的法律責任。這本是一個邏輯清晰明瞭的簡單判斷﹐卻被有些人故意 “矯情化”。明明隱藏在思想深層的仍是一個“利益”權衡﹐卻偏要裝“有口難言” 的“深沉”。這種化醜陋為“高尚”的犬儒術﹐實在是偽“ 愛國者”的一大絕技。
逢時﹕可悲的是﹐“傷痕文學”的局限﹐決定了它祇能永遠是毫無作為地“苦戀”。
***********************
成用﹕由胡耀邦的去世引發的“八九民运”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个人的命运。别的不说,要不是“六四”﹐不知我是否還在“黨文化”的紅海中翻滾。可是﹐雖然“八九民运”的历史价值与功绩不可磨灭,但在此期間的文化現象卻是發人深省。
逢時﹕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已說過﹐“文化認同”的改變最為困難。 ““八九民运”提出了“反腐败”、“反专制”、“民主自由”以及“和平、理性、非暴力”等政治诉求与理念。但在文化上却并无反“党文化”的意识,而是不自覺地把幾十年來中共的“文化成品”拿來使用。
成用﹕“六四”時的學生們基本上成長於一個“文化荒漠”時代。幾乎所有的人﹐包括我們在內﹐都嚴重地在文化上“營養不良”。因此在反對中共專制體系的過程中﹐除了拾起中共自己製作的“文化成品”﹐似乎別無選擇。這是一種十分悲哀與尷尬的處境。
逢時﹕學生們唱“國歌”﹑“國際歌”等﹐除了事後能體會到的一種奇特的“反諷”意義外﹐主要的原因是無歌可唱。這實在是“黨文化”的“受毒者”祇得用“黨文化”來反“黨專制”的無奈。
成用﹕“六四”期間﹐廣場集會時有幾首常唱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引起了我的特別注意﹕“血染的風采”。
逢時﹕的確﹐這首歌已成為“六四”学运的一个符号﹐有點像文革中的“樣板戲”。直到最近﹐在海外某些紀念“六四”的活動中﹐這首歌還在唱。
成用﹕“血染的風采”是1979年中越戰爭中出現的歌曲﹐主題宣揚的是以“鮮血”捍衛“共和國”的“愛國主義”情懷。其中核心的一句歌詞是“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逢時﹕音樂風格則仍保留著當年“晉察冀”音調的痕跡。台灣同胞所敏感的“共匪”味還真有點生命力。
成用﹕其實﹐中越戰爭並非“反擊”戰﹐而是侵略戰。不知是戲弄歷史還是被歷史戲弄﹐六十年代時﹐中共還出錢出槍又出人幫助越共打美國。十幾年後﹐一變臉就要收拾當年的小兄弟﹐“捍衛共和國”從何談起﹖國際上打一張牌下一招棋﹐代價是雙方數十萬人的生命。一句話﹐中越戰爭與“愛國”與“八九民摺睕]有任何關係。進一步說﹐“血染的風采”的出現決非偶然﹐而是“黨文化” 一貫宣揚讚美的血腥的暴力文化的產物。
逢時﹕這不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背道而馳嗎﹖ 
成用﹕這正是前面所說的尷尬﹑無奈與悲哀。我們從小受到的就是這種暴力文化的教育﹐用現在的話說﹐叫做“喝狼奶”長大的。什麼“又紅又專”﹑ “紅心向黨”﹑“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紅旗是用烈士的鮮血染成的”。文革中更是滿目皆紅﹐“紅衛兵”“紅小兵”“紅海洋”“紅色江山”“紅色政權” “全國上下一片紅”﹐“紅色的帽徽紅領章”“紅色的戰士紅思想”﹐以至“紅色恐怖”“刺刀見紅”“甘洒熱血寫春秋”﹐一直到今天的“紅色經典”。
逢時﹕我聽得頭都暈了。這種瘋狂的“紅色圖騰”﹐說到底﹐背後是一個“血”字。在西方國家﹐如果電影中有流血場面﹐兒童就不宜觀看﹐以保護兒童心理。而我們從小就受到了要“為黨為祖國為毛主席”“流盡最後一滴鮮血” 的說教。
成用﹕文革中甚至發生過強迫老師帶著孩子們觀看處決“犯人”的事件。耳邊則一天到晚聽的是暴力仇恨語言﹐什麼“千刀萬剮”“死有餘辜”“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血債要用血來還”等。在這種環境中長大﹐可以說﹐我們這代人幾乎百分之百心理上有創傷﹐有問題。這種病態心理﹐使我們習慣於從欣賞暴力中尋找刺激。而對暴力的崇拜又反過來加重了病情﹐人人都像是在“紅色”挑逗下的西班牙“斗牛場”上的牛一樣。1966年的“紅八月”中﹐曾出現過北京紅衛兵把中學老師活活打死﹐再用老師的血寫出“紅色恐怖萬歲”的駭人聽聞的事件。一時間﹐寫“血書”成風﹐動不動就“咬破手指”寫“誓死保衛毛主席”。我的同代人中為表示堅決“上山下鄉”﹐寫血書的大有人在﹐似乎不見血就不足以表現革命。這些現象﹐實在都是我們“病得不輕”的表現。
逢時﹕現在想來﹐這簡直是一種“恐怖主義”的教育﹐卻偏偏冠之以“愛國主義”。這種對人性的嚴重扭曲只有在極權制度下才會發生。我以為﹐崇尚每一個個體生命﹐是人類普世價值觀的基點。從這一理念出發﹐“人”高於“國”﹐更高於“黨”。而中國歷代統治者﹐包括所有的極權專制政權向人民灌輸的是“國” 高於“人”的觀念。中共更是“黨”“國”不分﹐鼓吹為了“黨”“國”的利益要犧牲個人的生命。“血染的風采”就是這一沒有人性的文化發展到高峰的代表作。 “風采”﹐本是一個人內在修養和高尚品行的外在顯露。硬把“風采”與“流血” 這兩件毫不相干的事情捆綁在一起﹐實在是文化的“野化”﹐是用野蠻摧毀文明。
成用﹕必須指出的是﹐“六四”這一悲劇發生的文化背景是中共已經營了多年的成熟的“黨文化”。正因如此﹐“六四”最終沒有﹐也不可能突破這一層文化包圍。這是值得我們每一個歷史的見證人所反思的。
***********************
[1] “黨媽媽”頌
[2] 血染的“風采”
(五) 血色黃昏——“黨文化”的衰敗
“主義”真空的“改革開放”與“盛世”(下)
逢時﹕“六四”之後﹐中國進入了長達十五年的“江澤民時代”。中共雖然想盡辦法讓人們忘卻“六四”﹐但它自己卻無法擺脫“六四”的陰影而始終存在著一種危機感。所謂“穩定壓倒一切”﹐說穿了就是“坐穩江山”壓倒一切。這一心態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變本加厲地愚民﹐甚至打開“潘多拉”盒子﹐公開鼓勵縱欲。
成用﹕當今的中國﹐社會行為“本能化”已日趨普遍。
逢時﹕有些中國大陸的有識之士為此發出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的警言。
成用﹕電影演員趙丹在1980年臨終前曾留下這樣的遺言﹐“黨把文藝管死了”﹐“黨最好少點干預”。在全國上下一心陶醉於“經濟神話”的“盛世”﹐趙丹的遺言似乎已接近實現。一方面﹐宣傳部﹑文化部總得上班﹐因此“文藝為政治服務”指導下的歌頌文化仍強打著精神。在類似“春節晚會”等重大國家級活動中﹐對黨的歌頌仍必須佔一定的比例。另一方面﹐黨已退到了不能再退的底線﹕ “一禁百赦”﹐只要不挑戰“黨”的權威﹐色情﹑凶殺﹑打鬥﹑搞笑﹑妖魔鬼怪﹑低級趣味﹑瘋狂怪誕……﹐似乎寫什麼都行。從“泛政治化”到“非政治化”﹐這回黨算是把文藝“管活了”。
逢時﹕“為藝術而藝術”並非是迴避文藝表現政治。在一個自由創作的世界裡﹐作家難道就不能寫有關政治的題材了嗎﹖文藝是否能完全脫離“為政治服務”﹐並不在於其作品是否寫政治﹐而是在於作者的創作是否能完全建立在個人自由意識的基礎之上﹐不受官方及任何意識形態的控制。當初﹐黨強行規定“政治掛帥”﹐藝術家就必須為黨的“政治”服務﹐大寫“偉大光榮正確”。如今黨號召大家別管“政治”﹐自顧自“奔小康”﹐非政治化的純娛樂作品就氾濫成災。很明顯﹐主導當今文化方向的仍然是“黨的意圖”。
成用﹕“十億人民九億賭﹐還有一億在跳舞”。這種所謂的“非政治化”﹐實際上是一種精心營造的“政治環境”﹐因為這最符合中共當前的利益。由此可見﹐“非政治化”本身即為政治。
逢時﹕說來有趣﹐現在有些海外華人團體在成立宣言或章程裡總要特別聲明一下﹐“本團體是‘非政治’團體”。此言一出﹐實際上該團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已清清楚楚了。比如﹐與“六四”有點關聯的活動絕對屬於“政治”。而慶祝中共國慶﹐歡迎中共領導人則不算“政治”。
成用﹕一句話﹐“反共”就是政治﹐“親共”則不是。小時候我的 “操行評語”的最後一句總歸是“希望你今後多關心政治﹐積極爭取進步”。而如今卻常聽到這樣的規勸﹕“寫你的音樂﹐少問政治”。難道這兩個“政治”是一回事嗎﹖顯然﹐“政治”在我們大陸人的觀念中根據官方意識不斷改變著含義。
逢時﹕中共長期來成功地讓國人們染上了根深蒂固的“恐懼症”﹐即使是人已在西方自由世界多年也不見好轉。可見“非政治化”有多麼強烈的政治暗示性。
成用﹕我認為﹐“六四”之後中共在文化上的工作重點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環境。中共在動手修理文化之前先做了兩個動作。首先﹐用“鄧時代” 的“發展是硬道理”﹐與“江時代”的“奔小康”等庸俗功利主義取代“為共產主義奮鬥”的“革命理想主義”。同時把敢於挑戰專制的極少數人處以重刑﹐讓“莫談國事”“少問政治”的信條深入人心。其次﹐號召“發財致富”及允許“資本家入黨”﹐引誘慫恿人們不擇手段地積累原始資本﹐淘“第一桶金”。“拜金主義” 的氾濫不僅使人民不再感興趣於“政治”﹐同時為共產黨自己瘋狂掠奪瓜分公共資產找到了“根據”﹐真不愧為一箭雙雕的好主意。
逢時﹕遠離“政治”與道德淪喪﹐有了這兩點﹐“黨”便放心地把文化交給了市場。
成用﹕可是﹐左右“文化商品”的﹐並非完全是以供求關係為杠杆的市場調控﹐而是結合了政府的行政干預﹑作者的“風險評估”與市場“利潤導向” 的混合物。一個朋友告訴我﹐他認識的一個在上海專作“盜版書”生意的成功者說﹐什麼都可“盜”﹐多“黃”都敢“盜”﹐但有關“政治”的書一律不碰﹐因為風險太高﹐一出事就什麼都完了。
逢時﹕這是一個遠離“政治”加道德淪喪的範本。“江澤民時代” 是“黨文化”的“收穫期”。其顯著的標誌不僅是其對文化的破壞開始全面顯露﹐而且範圍從文學藝術領域擴張到社會行為準則。了解了這一點﹐對當今中國社會上令人吃驚的道德淪喪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釋。
***********************
成用﹕為期十五年的“江澤民時代”以江於2004年戀戀不捨地下臺而告終結。而同年在雅典奧邥?]幕式上﹐中國作為下一屆主辦國的表演則是“戲子” 江澤民向世界謝幕的深鞠一躬﹐同時把他執政十五年在文化上的“成果”鄭重地作了一個總結。
逢時﹕在萬眾矚目的世界舞台上﹐张艺谋施展绝技﹐把中國文化的現狀濃縮進了八分鐘的眼花繚亂﹐向世界展銷了一個與“經濟神話”門當戶對的 “藝術神話”。 
成用﹕以此作為對“江澤民時代”的文化總結可以說是恰到好處。 “八分鐘”把當前中國的“文化雜碎”表演得淋離盡致。張藝谋不仅把“中國概念” 像擺地攤樣地一一叫賣﹐二胡﹑琵琶﹑旗袍﹑武術﹑京劇﹑燈笼“茉莉花”﹐而且還煽情表現了中國當代最具“市場效應”的“炎黃百老匯”﹕美女與大腿。
逢時﹕二胡和琵琶在這兒其實已不是樂器﹐而是道具。這種對中國文化的“雜耍”究竟是崇尚傳統﹐還是以譁眾取寵誤導世界﹖說穿了﹐““奥运八分钟”是以进口西方通俗的艺术形式为躯壳﹐裝入一堆毫無人文精神的“中國概念”﹐以兜售一個國際化的“盛世”中國。
成用﹕其實也不必過多地指責张艺谋,把林林總總的“江澤民時代” 的文化總結進八分鐘﹐能湊成這樣實屬不易。當代的中國文化既已如此﹐怎能一昧怪罪灶前當炊的“巧婦”﹖张艺谋所作的,不過是代表中國在全世界的目光下展示了當代中國文化的陋俗。在某種程度上這對西方的“中國熱”是一帖“清醒劑”。從幾分鐘前端莊渾厚的希臘文化之旅為起點﹐人們開始思考﹐把“中國概念”作為商業化的“賣點”是否最終會毀了又一個遠古文明﹖ 
逢時﹕無論國人如何振臂高呼“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擺在世界面前的這個“盛世”文化﹐是一個沒有靈魂﹐沒有內涵﹐沒有根基的文化﹐就像踩在高蹺上的臉譜。
成用﹕近來中國常有由官方參與的祭孔典皇﹐大小廟宇香火不斷。一時間﹐“復古”成為時尚﹐年輕人結婚也要穿上古裝拱手作揖﹐擺個姿勢照個像。
逢時﹕這不過是“中國概念”的出口轉內銷﹐“傳統”在此早成了毫無精神內涵的標籤。從文革的“批林批孔”到今天的尊孔祭孔﹐“實用主義”已成了中共唯一的信條﹐底線就是“穩定壓倒一切”﹐以苟延其一黨專制。
***********************
成用﹕我們這一代從小生活在一個“東方紅”時代﹐一個“黨文化” 最成熟﹑最猖獗的時代。一代大“儒”郭沫若的“兩個太陽”之說﹐使愚昧與卑鄙冠冕堂皇地成了“文化”。從小唱著“東方紅”被“紅太陽”燒烤﹐“黨文化”已深深地滲入了我們的血液。且不說大多數仍留在中國大陸的我的同代人﹐僅就目前生活在西方的大陸華人而言﹐我們仍苦苦掙扎在西方文化﹐東方文化和“黨文化” 的衝突之中。究竟能否“自拔”﹐目前尚無定論。
逢時﹕想想幾代人幾乎成了“文化災民”﹐這對一個民族而言是多麼可悲和可怕的事情。
成用﹕知道小說《血色黃昏》嗎﹖
逢時﹕不是描寫文革中的知青在內蒙插隊的作品嗎﹖
成用﹕一代“知青”已成了“血色”的殉葬品﹐而“六四”這代人仍在“血色”中艱難拔步。血腥的暴力文化染紅了東方。雖然“六四”的槍聲把共產主義逼近了黃昏﹐但其血色依然不退。
逢時﹕“六四”標誌了血色黃昏的來臨﹐同時也標誌了一代人覺醒的開端。唱了幾十年的“東方紅”﹐當人們開始明白東方是怎麼紅了的時候﹐我相信“東方紅”便會成為愚昧﹑恐怖與殘忍的象征。
成用﹕自從“十月革命一聲砲響”﹐至今已將近一個世紀。中共仍在堅守著“十月革命”的“最後堡壘”﹐而“十月革命”在其發源地已被送進了墳墓。最近我們游訪了前東德的幾個名城﹐給我的感觸至深。從萊比錫引發的對前東德共產政權的抗議導致了柏林牆的最後倒塌﹐而在這一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的人物之一﹐竟是一位德國的交響樂團的指揮家。
逢時﹕萊比錫是巴哈與門德爾松的故鄉。那天﹐當我站在巴哈的銅像前﹐欣賞街頭藝術家純熟地演奏著的古典音樂時﹐瀰漫全城的那種不必刻意渲染  的古典文化遺風深深地感染著我。是否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是紮根於民間的滲透著人文主義的文化精神使得專制政權的暴力也無能為力。
的古典文化遺風深深地感染著我。是否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是紮根於民間的滲透著人文主義的文化精神使得專制政權的暴力也無能為力。
成用﹕以無數生命為代價的柏林牆終於在“六四”槍聲的五個月後倒塌。在這一輪較量中﹐民主與專制﹐究竟誰是勝利者已不言而喻。然而﹐難道我們帶回芝加哥的昔日柏林牆上的殘石僅僅是這一歷史的記憶嗎﹖
逢時﹕不﹐它不僅僅是紀念﹐更是提醒著我們﹐這個毀壞了整體民族文化與普世精神文明的“東方紅”時代還沒有被埋葬﹐我們的國人仍被禁錮在一堵無形的“黨文化”大牆之後。我期待著這一精神上的“柏林牆”能早日土崩瓦解﹐一個獲得了文化新生的民主自由的中國才是中華民族回歸文明的希望。
***********************
[1]“炎黃百老匯”
[2] 踩在高蹺上的臉譜
[3] 期待精神上的“柏林牆”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