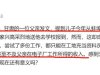九年前的那个五月,我刚被国务院机构分流的风暴,卷到一家报社。心里难免郁闷,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因为和新单位的人还不熟悉,于是时不时回那栋位于朝阳门以南的大楼找原来的同事玩。
那两天,我恰好碰到了一场大戏。一驻外使馆被美帝的炸弹“误炸”,两位记者殉职。那家使馆在大楼的东面,只有一箭之遥。我和几位哥们站在九楼,目睹了那场热闹。旗帜飘扬、喊声震天,我们也似乎感觉到曾有的青春激荡。
下激荡而已,我和朋友更多的是冷眼观潮的心态。工作了五、六年,小吏的生涯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所谓的“爱国”、所谓的“义愤”在当下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东西。
要说对牺牲的两位记者不同情,那就冷血了,要说对美国的“误炸”不义愤,也是假的。可是,我决不会参入那场表示愤怒的游、、、\行。因为这种自由表达是上峰的恩赐,这种选择性的自\由,我谢绝。如果对美国抗\议的游\行和自己政府抗议的游\行,都能自由地举行,那么我会参加这场抗\议美国的\游\行。而当自己这样的义愤,仅仅被当成某种砝码,我宁愿旁观。
看到那些在队伍面前呼喊口号,指挥抗议的年轻人,我知道很多是学生干部,他们的心思难道和队伍里大多数的爱国青年一样么?大学时当过学生干部的我很不以为然,我知道身边的学生干部,比起一般同学太成熟了,他们许多人早修炼成心底波澜不惊,外表演技超群。他们争着接受记者采访,争着上镜,或许目的十分明确,博得学校的喜欢,作为就业的一种凭藉。
最后爱国者的热情也没有把政府的“血性”激发起来,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一切太平无事,大佬仍然以去大洋那一头某家私人牧场里吃烤肉为荣。
再后来,这样的戏又在抗议日本时演了一次,只是群众演员换了新一茬,编剧、导演和剧情没什么变化,这次更是令爱国青年们失望,还没过瘾就被压下去了。“一次性夜壶”的说法不胫而走。本来就是“夜壶”么,夜壶当然有夜壶的价值,认清这点,心甘情愿充当夜壶,博取一点利益完全可以理解,如果硬要把夜壶当成茶壶那就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强烈的失落感必然接踵而至。
九年好像一瞬,这世道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九年前那些爱国青年今何在?也许,一些人去了大洋彼岸,一些人成为科级、副处级干部,一些人成为白领,多数人成为房奴。不知道看到新一代爱国青年,他们今天会作何感想?也许说一句:“谁没年轻过!”
爱国,在今日中国,太容易也太难。说爱国容易,只要把“爱国”的标签往头上一贴,似乎就如练了极高的武功,遇神杀神,遇佛杀佛,手里揣着几顶“汉奸”、“叛徒”、“洋奴”的帽子,就像当年给地富反坏右的红卫兵前辈一样,看谁不顺眼便奉送一顶。我觉得爱国青年们对历史应该全面地了解才行。当年“扶清灭洋”的义和拳兄弟当然有质朴的爱国情怀,可是一旦西狩的太后等和各国签订条约后,回銮第一件事就是剿灭那些曾忠心拥戴她的拳民,爱国的师兄弟一夜之间成为官府镇压的暴徒。四十年前,革命小将对红太阳忠心耿耿。等到最大的走资派被消灭,红太阳的光辉无人敢挡时,一句话:“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一挥手就把这些小将发配到广阔天地中去锻炼,直到曾被他们打倒的二号走资派复出,小将们才得以大批回城。这类爱国青年,从来就是朝廷的一次性“夜壶”,可广土众民的中国,这样的“夜壶”从来是前赴后继,不担心后备力量匮乏。为什么?
说爱国太难,是在这样一个比拼“爱国”pose的国度,一些真正的爱国者反而难以立足,而被视为异类。而爱国和爱政府爱执政党牢牢捆绑在一起,不允许质疑,就如古代的忠君和爱国捆绑在一起那样,君王再混蛋臣民也必须无条件忠诚,君王可以毁江山,却要求臣民殉江山。大学时读过高尔泰的文章《雪落黄河静无声》,他质疑丛维熙小说中一位主人公的“忠贞”,这位先生知道自己相爱的人在60年代初曾有北逃他国的计划时,认为她对祖国不够忠贞而忍痛分手。难道当年逃出去的马思聪先生不爱这个国家?难道现在还在异邦的高尔泰不爱这个国家?只有死在此处的傅雷、老舍,才算是爱国?丛维熙这样的爱国观至今还被许多人提倡,一些人自己把子女、把金钱送到国外,而要求别人无条件“爱国”。臣民没有资格也没有义务爱国,因为他的目的仅仅是活着,只有公民才有资格有义务爱国。如果连起码的公民权不能维护,不能自由地表达,不能以一个现代公民的姿态去监督批评政府,他的爱国情怀只能是有些人的“一次性夜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