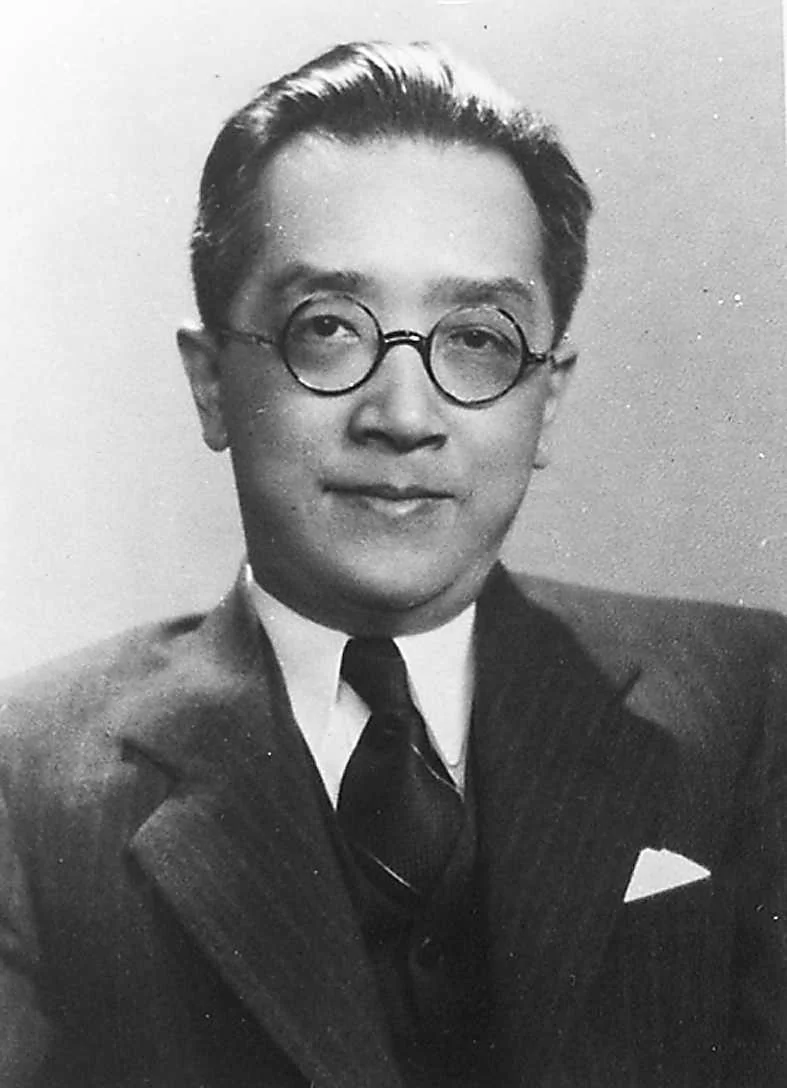“七君子”的大结局
——救国会对《日苏中立条约》表态始末
章立凡
近年在报刊和网络上,不断出现有关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的论争。辩论的焦点之一,是当时救国会领导层对该条约的表态,其中也涉及先父章乃器因此事退出救国会的问题。辩论的双方多是我的老朋友,其中一方与我在电话中论及此事时,我的意见是:当事人亲属须知避嫌,最好是述而不争,心平气和地把史实讲清楚就可以了 。见仁见智,悉听历史公论。本文的撰写也将遵循这一原则。
光荣出狱,各奔前程
1936年11月震惊全国的“七君子”案,使救国会领袖们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风范永垂史册。在狱中他们“六个人是一个人”(史良在"西安事变"结束后投案,另押在女监),对外爱国立场一致;但在具体的政治见解上,则见仁见智,有各自的特色。例如王造时曾经回忆说:
在救国会运动中,我反对蒋介石“不抗日”(!)的情绪是比较激烈的,认为只有联合和发动一切抗日力量,逼迫他非抗不可,不抗就要垮台,才有使他改变不抵抗政策的可能。当我们七个人被关在苏州的时候,有人在李公朴主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好像是《中国的党派》,说救国会有两派意见:一派是正确的,主张拥蒋抗日,以章乃器为代表;一派是不正确的,主张反蒋抗日,以我为代表。我看到这个小册子很不高兴,我是主张逼蒋抗日的,现在我们都被关在牢里,却把我说成是反蒋抗日的,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认为该小册子所说的与事实不符;公朴表示事前毫不知情,决定马上通知该社停止发行。
虽然大家共同否决了这本书的观点,但也从另一角度表明,王造时的政治态度是比较激进的。
“七君子”在抗战爆发后出狱,这时,救国会已发生微妙的变化。当时救亡协会的负责人是钱俊瑞,“七君子”由救国会领导人变成了该会的设计委员,仅剩下提建议的权利。张友渔晚年曾对我说,这种做法,当时也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
父亲一直是持超党派立场投身于救亡运动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局面,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立场。第三党的蒋中光先生曾对我说起一段往事:“上海沦陷前夕,我与几名青年去找令尊,问他蒋介石会不会投降,章先生说不会。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中国地广人多,回旋余地很大;二是蒋先生要维护自己民族领袖的历史地位,不会轻易投降。”
当时父亲认为救国会团结抗日的主张已经实现,从超党派的立场出发,主张统一战线内部各党派要“宽大、容忍”,不必再算旧账,不要再有党派和领导权之争。他认为钱俊瑞与国民党唱对台戏,是一种党派之见和内耗。为此双方发生争论,父亲发表了后来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少号召多建议》一文。
父亲当时做了一副对联:“无此闲情算旧帐,有腔热血效前驱”。不久便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李宗仁之邀,到抗日前线担任安徽省财政厅长。在武汉失守前这段时期,章乃器在安徽前线,李公朴去了山西前线,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王造时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沙千里秘密加入了中共,七人虽然聚会或联系没有中断,但轨迹已显示出不同。
1939年6月,父亲应蒋介石的电召“赴渝述职”。既是应召前往“述职”,孰料蒋竟然不出见,紧接着又下令“章乃器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其实这是蒋介石使出的“调虎离山”计,原因是父亲在安徽与国民党桂系、中共新四军都合作得很好,不但使濒临破产的省财政扭亏为盈,还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银元,于是该省的国民党CC派和地方势力,纷纷向蒋造谣告密,说他“勾结奸党奸军”,令蒋委员长很不放心。后来经戴笠查明是诬告,蒋介石派贺耀祖来劝说父亲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拟委任他为金融方面的官员,最后又征求他出任陕西或甘肃省的财政厅长,均被父亲拒绝。从此他再也没有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
父亲在重庆同救国会的同事们重聚,由于暌违已久,不免产生隔阂。父亲曾回忆说:
我回到重庆的时候,正值‘五·三’大轰炸过去不久,街道上和人的脸上都是一片萧条景象。救国会上层除了韬奋曾经邀我在生活书店作了一次关于安徽青年动员的报告以外,再没有人愿意了解我在安徽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史良甚至当面指责我不该当财政厅长,胡子婴认为我不就工合总干事职,对工合对自己损失都很大,钱俊瑞则散播流言说我要进中央训练团受训。我所得到的最大安慰,是建国初期毛主席说我在安徽为党培养了一批财经干部,做了好事。(《抗战初期在安徽》)
父亲在入狱前是救国会的灵魂人物,负责宣传和财务,该会的经费,主要出自他的毁家纾难。经过战乱离合,当时救国会已无实体,只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存在。“七君子”各自有自己的事业,沈衡老年高德劭,仍被大家尊为“家长”。但老先生在内部能够倚重的,主要是史良。
救国会这时已发生张申府与沈老之间的人事纠纷,父亲感到目前的活动方式,已不可能像往日那样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因而产生了消极情绪。1941年春,救国会上层因对《日苏中立条约》的表态问题产生分歧,促使他脱离了救国会。
对苏表态,最后晚餐
中国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曾得到苏联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南进”战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极力谋求与苏联达成妥协,以便抽出兵力巩固中国战场,进兵东南亚,从英、美、荷等国手中争夺殖民地和战略资源。而斯大林为避免在东西两条战线作战,也不愿同日本发生战争,希望把日本的进攻矛头引向南洋。苏联继签订《苏德友好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又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这一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条约中还包含一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根据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俄在北京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四条:“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後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定。”该协定第五条还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抗日战争爆发后,两国于1937年8月20日在南京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时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除法西斯国家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斯大林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作出这一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抉择,除在国际法法理上违约外,也背弃了“胜利了的民族应该解放被压迫民族作出更大牺牲”这一列宁主义原则,使中国成为这一条约的最大受害者。
条约签订后,中外舆论哗然,也给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困扰。在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毛泽东是强调既团结又斗争的;但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特别是对以“老子党”自居的苏共,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共不能不发表声明,维护苏联的威信,同时又重申:“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实际上表明了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立场。
救国会的领导人当时曾联名写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认为苏联的这一做法"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并从法理上对条约的内容提出质疑,要求作出解释。
据王造时回忆:“在重庆救国会的重要负责同志开会讨论这件事情的结果,认为救国运动是由于日本侵略东北而起的,中国抗战也是为着这个问题。苏联虽然是我们最好的友邦,但是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当场推举我起草,张申府审查。我随即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认为是很大的遗憾。张申府看过之后,旋经开会修正通过。当时我们七个人(指救国会“七君子”),除邹韬奋因生活书店被迫已潜往香港外,我们六个人都在重庆参加会议(记得王炳南、张友渔同志等也参加会议)。开会决定由沙千里誊清两份,于次日在史良家里签字。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我九人。记得陶行知声明对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是赞成的,但不赞成公开发表,故未签字。”
签字的信件共有两份,一份由沙千里派人送苏联大使潘友新转交斯大林,另一份则由王造时送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交中央社发表。王世杰在日记中说:“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友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质问。”后来救国会恐该信被利用作为反苏的口实,于是又安排收回了这一信件。关于此信的收回始末,有两种记载。
一是钱俊瑞说:“当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政府出于应付形势的必要,曾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中立协定。中国有些人起来反对,衡老(沈钧儒)由于了解情况不够,也附和签了名。后来,恩来同志找他谈,把当时国内外形势详细地讲清楚,对他的参加签名提出了批评。衡老立即表示,‘我一时糊涂,错了。’并说:‘我立即撤销我的签名,当众认错,还可以做一番宣传。’”
二是萨空了说:《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一天我得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有个内部通知,说救国会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等人发表声明反对这个条约的签订,此文国内不要发表,可在海外发表。我立即去找李公朴,告诉他这个消息。公朴一听立刻领悟到这个声明有不妥之处。我们一同去找沈老、沙千里,把我们的看法告诉了他们。我们认为在当时,发表这样的声明对团结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德意日侵略者不利。沈老听后,认为我们的意见是对的,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一次政治上的失误。后来大家想了个主意,以补充内容为理由,又把这份声明从国民党宣传部要了回来。后来沈衡老多次就此事躬身自责。”
王造时后来回忆:1957年3月,他与萨谈及此事,萨空了说,你们知道国民党伪中央宣传部为什么没有把信交中央社发表,而侧面拿到香港去发表?我说我至今不明白。他说有人把你们亲笔签名的信从伪中宣部拿走了,伪中宣部没有根据,恐怕(别)人提出质问,不敢交伪中央社发表,只好拿到香港去发表了。我追问他,是怎样从伪中宣部把原信拿出来的,萨空了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了。
如此看来,似乎是萨、李向沈钧儒进言并收回信件于前,周恩来批评在后。但萨空了没有说明收回的具体经过。
父亲当时是不同意收回的,而且后来也一直不肯认错。他认为救国会作为一个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政治团体,如果在这一关键时刻不对苏联的做法公开表态,就无法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及其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丧失存在的依据。据胡子婴回忆:在受了周恩来的批评后,“沈衡老表示救国会要作自我检讨。章乃器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救国会发表宣言是救国会的事,共产党无权干涉,救国会也不应该检讨。他争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国会”。
上述十几个当事人中,王炳南、张友渔、钱俊瑞、萨空了、沙千里皆为中共秘密党员,不过前三位的身份很早就公开了。他们应该是知情人,不知为何,王、张、沙的回忆录中,均未见到公开信起草过程的记载。
误会澄清,两人划"右"
知识分子应该是“直立的思考者”。父亲是一位学者和专业人士,参与政治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国民党和一些在野党派中“结党营私”的风气是深恶痛绝的,因此他一直提倡“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在他自己所参与创立的政团内,也一向公私分明,从不搞小宗派。在内心深处,他没有党派利益的门户之见,一直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
当时被推举起草公开信的王造时,在将信件交给王世杰的次日就离渝赴赣。后来他接到沈钧儒来信,说:“自你离渝后,此间谣言纷纷,盼速来渝面谈一切。”据他回忆,过了些时候在重庆与沈老晤面时,“谈到这个问题,颇为痛心。他并且说外面有谣言,说我们拿了国民党的钱。我愤然问:你拿了没有?你相信我拿了没有?他说我不相信,但事是做错了。”后来救国会的许多成员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但王造时没有加入。
1945年冬,救国会更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此前邹韬奋于1944年7月24日病逝于上海,根据遗愿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成为民主先烈。“七君子”只剩下五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新政治协商会议十四个党派单位之一的救国会,于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初抵莫斯科访问的第三天)宣布解散,同时“以本会名义庆祝斯大林七十大寿并送纪念册”,用自己的结束作为“一边倒”的寿礼。
据我所知,在退出救国会之后,父亲与当年的同事们一直保持着私人情谊。他不但参加了这次茶话会,且以来宾和会员的双重身份致辞。家里有一块长着许多大颗粒金砂的白色奇石,是父亲在北戴河疗养时捡的,剖开后送了一半给爱石成癖的沈衡老。
1949年以后,“七君子”中的沈钧儒担任了最高法院院长,史良、章乃器、沙千里也先后出任部长职务。而“公开信”的起草者王造时,则长时期受到误解和不公正的待遇。他在七人中学历最高,学问和口才最好,却没有被安排行政职务,一直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老朋友潘大逵为他感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据史良对他说,“党对你有些误会,将来慢慢可以说清楚”,后来他又听张孟闻说:“中央某负责同志说因为一个什么条约的事情党对我有误会”。这位“负责同志”是谁,至今没有人说清楚。
1957年3月,王造时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3月21日上午,他特地去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澄清此事。张告诉他:“我们当初听到谣言说,这封信是你事先起草好的,强迫大家签字,如果不签,救国会就有分裂的危险,并且有谣言说国民党拿出了一笔钱来发动这个运动。”
当晚,王造时与史良、胡愈之、千家驹等原救国会的朋友们在沈钧儒家聚餐时,曾情绪激动地要求大家为他作证。史良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衡老听到此事就痛心。这件事情当初是我们大家做的,由我们大家负责任,不能由你单独负责任。这是政治上的一个错误。”
周恩来于3月27日召见王造时,王又就此事向周作了简单交代,因王造时的遗稿残缺,周对此事的表态内容至今不得而知。但王谈到了周问他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的问题:“周总理说,当初解散救国会是一个错误。毛主席看见了民主党派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没有救国会的名字,认为是一种损失。周总理说我当初反对解散是对的。”
救国会在历史上是与中共配合得最紧密的民主党派。周恩来重提恢复救国会,或许与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变化有关,但目前没有公开的文献档案可为佐证。王造时曾为此走访了一些救国会的老朋友,除顾执中积极支持外,响应者寥寥。原救国会重量级人物沈钧儒、史良已在民盟掌权,均不赞成恢复,并劝他加入民盟。章伯钧说,如果王愿意参加民主党派,“除民建会以外,都会欢迎你的”,特别是和章有关的民盟和农工会欢迎。罗隆基认为沈、史不赞成,恢复救国会有困难,欢迎他参加民盟,“但不如史良那样热情”。潘大逵则主张王造时当无党派民主人士。
此外,王还记述了他的安福小同乡罗隆基对公开信问题的看法:“这个误会,史良同志等应负责任。他们是随时可以向党中央负责同志替我解释清楚的。这就是所谓‘共患难易,共利害难’了”。
王造时也曾为这两个问题,到粮食部去见过章乃器。当他谈及在公开信问题上,自己和沈、史等“都承认在政治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时,父亲的态度却迥然不同。王造时是这样记述的:“他说他不认为是犯了错误,当初没有错,今天看来更没有错。他并且说应该追究是什么人把这件事情的责任完全推在我身上。”
至于恢复救国会的提议,父亲也一口回绝。
3月29日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和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到前门饭店与王造时长谈。关于恢复救国会问题,张副部长说:“不能由我们决定恢复不恢复。如果是我们来决定,那等于是你们奉命恢复,这个问题还是你和救国会的朋友们多去商量商量好,如果大家都主张恢复,那我们是欢迎的。”谈及对“日苏中立条约”的表态时,“他们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大家都觉得畅快。你承认是政治上的一个错误,那是政治家的态度,章乃器是顽固。我说这个历史包袱解除了,我特别感到愉快和兴奋”。
由于没什么人响应,救国会始终没能恢复起来。不过出于重获信任的喜悦,王造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很快投身于“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
这种"皆大欢喜"的氛围,也只维持了两个多月。无论是刚卸下包袱的王造时,还是“顽固”坚持己见的章乃器,都同时被打成“右派”,当年的两位“难兄难弟”再度落难。王造时恢复救国会的活动,也成为他“阴谋组织资产阶级政党”的罪状。
“七君子”中除邹韬奋、李公朴于40年代为民主献身外,其余五人结局如下:民盟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沈钧儒老人于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逝世。逝世前曾申请入党,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造时于1966年“七君子事件”30周年前夕被捕入狱,1971年8月5日冤死狱中,离开人世时被诬为“反革命”。
章乃器熬过"文革"的漫漫长夜,于1977年5月13日在北京医院地下室病逝,辞世时为“摘帽右派”,史良、沙千里出席追悼会。
1982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沙千里在北京逝世,史良出席了追悼会。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家属直到逝世后才知晓。
“七君子”中最后辞世的一位是史良。她“文革”中曾受冲击,1979年10月当选民盟中央主席。1985年9月6日与世长辞,逝世时是人大副委员长。章乃器、王造时的“右派”错案在1980年改正,并分别举行过纪念活动。除王造时的骨灰安葬于上海烈士陵园外,其余四人的骨灰均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至于是什么人把起草“公开信”的责任推卸到王造时头上,至今虽然仍是个谜,但当事人的范围也比较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