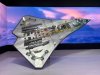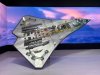抄袭者汪晖的前世今生
汪晖的抄袭,仔细读完王彬彬的批评文章,加上对于王彬彬提到的若干文献的仔细阅读比对,可以看出抄袭一事立论有据,完全成立。许多人以此为依据,像王彬彬一样指责汪晖的学风不正,固然是巴老所提倡的“说真话”,这当然是无可厚非。但是以此来透视汪晖进入学术界这若干年的思想脉络、学术道路,或许更为有趣。笔者不才,喜好钩沉索引,不妨就数年来所阅读之关于汪晖之文献,对其在学术道路上“渐入颓唐”,乃至最后“东窗事发”,作一番粗线条的勾勒,以待方家指正。
一、扬州师院生涯与汪晖的早年
一九七七年,正是改革开放呼之欲出的年代,这一年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停止了毛选第五卷的印刷,改印高考试卷,由此开始了恢复高考的历程。邓小平这一举措,无疑石破天惊,而他所力倡的恢复高考开始时期的那七七七八两届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社会的风云人物,汪晖亦厕身其中,只是其面貌后来越发可疑。
汪晖考入扬州师院时正是一九七七年,其母亲是扬州师院的教师,那一年汪晖十八岁。扬州师院现名扬州大学,其前身乃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张謇创立的南通高等师范学院。著名学者王国维、姜亮夫都曾在这所学校任教过。校内有诸多在学界赫赫有名的学者,但是在文革时期,扬州师院如同诸多高校一样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但是扬州师院依然群星璀璨,诸如古典文学大师任中敏、李坦、孙龙父、谭佛雏。现代文学有著名学者曾华鹏、吴周文、李关元。汪晖在这样的条件下入学读书,理应做出一番成绩。
有人曾评价汪晖这一代学者乃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虽有道理,但是过分强调了时代潮流之于人物的影响。扬州虽然交通便利,但那是古代的事情,凭借和运河相依而已。近代以来,扬州城日益闭塞,要说本科期间汪晖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无疑是牵强之论。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在于,汪晖当时所倾心的,更多是鲁迅研究和古典文学,他在扬州师院读硕士研究生时期的导师,就是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章石承先生。章先生虽然在词学方面造诣精湛,但是在鲁迅研究方面也有许多成果。汪晖受到章先生的影响,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但是没想到若干年之后,汪晖居然因为研究鲁迅的论文被指责抄袭,真是贻笑大方。
此处我要对汪晖在扬州师院的几位导师做一番简要的介绍,诸如章石承先生、曾华鹏先生。章先生的老师是著名词学大师龙榆生先生,章先生秉承了乃师治学严谨的作风,而且为人极其古道热肠,对龙榆生先生一直恪守师生礼数,不管世道艰难若何。曾华鹏先生是五十年代复旦大学毕业,他和他的同辈学长章培恒先生、范伯群先生,都是贾植芳先生的高足。其在鲁迅研究和王鲁彦研究上的造诣,引人瞩目。其为人治学之朴实严谨,自不必言。贾植芳先生曾因胡风案入狱,一生坎坷,其晚年学生张业松先生如此评价贾先生:他(贾植芳)活在鲁迅的脉络上。汪晖后来从事鲁迅研究,和章石承先生、曾华鹏先生的影响,密不可分。但是最后上演了抄袭这一出,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而李关元先生和章石承先生曾华鹏先生一样,都是淡漠的学者,虽然声名不显,但是其治学在学界已经留下了影响。他们曾经联合培养了诸多如今在现代文学研究界颇有名气的学者,诸如徐德明、葛红兵等。汪晖有如此诸多学风严谨的老师,到最后却因为学风不正被人钉在抄袭的耻辱柱上,端的是有辱师门。
汪晖在九十年代的《读书》上发表有《明暗之间》一文,记载了他与章石承先生的一段过往。一九八三年汪晖北上访学,章先生在他临行前声称有事情要交代。汪晖应约来到章先生的家里。章先生告知汪晖先去找在镇江的蒋逸雪先生,请他写信给时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王士菁。蒋先生是王先生的私塾老师,而且资助过王先生读书,汪晖可以通过王先生的关系查阅存放于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藏书。于此之外,章先生还私下里叮嘱汪晖,有一事相托,但是千万不要对人说起。章先生说请他去龙榆生先生的墓上祭拜,代他鞠躬致敬。后来汪晖回忆:这私事说来简单,后来我才觉得不寻常。
龙榆生,一个多么对于当代人来说非常陌生的名字,然而对于如今的老一辈人来说,再为熟悉不过。他是二十年代最富盛名的词学大师,其词学成就可与唐圭璋、夏承焘并称。龙榆生是章石承在暨南大学读书时的老师,私交极为密切。抗战时期,龙榆生先生不幸落水,章先生痛心疾首,却也无可奈何。或许正是这一政治上的歧途,导致龙榆生在学术史上几乎被遗忘。汪晖遵嘱找到了龙榆生的女公子龙顺宜,龙顺宜与汪晖一起去龙先生的坟上祭拜。两人来到北京万安公墓,找到了龙先生的墓碑。龙顺宜忽然问汪晖:你们这一代人,如何看待周作人先生?周作人先生名动天下,但是抗战时期选择了与龙榆生先生一样舍身伺虎,终致身败名裂。汪晖那时二十三岁,按照当时流行的至今尚未翻案的“汉奸说”回答龙顺宜,龙顺宜长叹一声:老一辈的人死完了,年轻一代就更不能理解了。后来汪晖忆及此事,只是觉得伤了老人的心,是不该的,但是没有苛责前人的内疚。同样的道理,汪晖评价龙榆生先生,也是同样苛刻:他虽然拒绝出卖文物,但是这点个人的清白,掩不住大节有污。在那样的历史语境下,不可能成为获得理解的理由。
这样一段过往,对于透视汪晖的学术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汪晖师从诸多名师,但是在对于文学以及文学历史人物的理解上,显得极为陌生。不管是周作人,亦或是龙榆生,他们的历史抉择,都有那个动荡年代的逼不得已,而汪晖对于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具体到内心的真切理解。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汪晖的《反抗绝望》之于鲁迅的内心洞察,几乎是寥寥无几。这样的著作被冠之以鲁迅研究的里程碑,真令人感到遗憾。更何况还有抄袭的内容,让人始料不及。或许正是从此开始,汪晖与他的师承辈在学术选择上渐行渐远,最终走火入魔。
二、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从文学史研究到思想史研究
一九八四年汪晖考入中国社科院,追随唐弢先生攻读文学史。当时社科院只有二十多个研究生,编在一个班上,汪晖担任学习委员。当时的社科院教师群星璀璨:于光远、李泽厚、苏绍智、马洪、贺麟、任继愈、彭泽益。而这个班上的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学界的风云人物:郭树清、樊纲、左大培、王逸舟、黄速建、韩水法,汪晖于其中,显得极为另类。
这一另类的原因在于,这个班上的许多学生选择了经济学,选择文学哲学的为少。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类似于“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经济、政治改革是当时他们每天讨论的话题。后来汪晖在九十年代以文学史研究者介入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有其在社科院的从学经历有关。同时也可以看出八十年代学风在汪晖身上的直观反映。八十年代的学术氛围,虽然激情高涨,但是学风比较粗疏,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汪晖抄袭的理由。九十年代中期,汪晖在《天涯》杂志上发表《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表明了他已经彻底告别文学批评,转向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但是这一转型,让汪晖成为了众人眼中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尤其是他主管《读书》杂志之后刊登美国学者高默波美化文革的文章,更让人对其新左派的立场深信不疑。而他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徐友渔、朱学勤、雷颐等人的攻击,更加显示出他立场的左倾。
汪晖的学术转向,原因诸多,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其学风的浮躁所致,在汪晖的师辈中,无论是章石承还是唐弢,生前都是严谨治学从不逾矩的本份学者,章石承著有《李清照年谱》、《陆游诗选》,功底扎实。而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早已成为学术界的经典之作。但汪晖的学术道路虽然在初期尚能在师傅辈的指引下循规蹈矩,尚能沉潜,其写下《反抗绝望》,虽然有抄袭之处,但按照严家炎先生的说法,主体思想还是他自己的。但是他在九十年代以后逐渐写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已经全然让人不知所云。
汪晖从文学史研究转向思想史研究,进而走火入魔,从小处看是学风不正,从大处看乃是八十年代空泛的学术风气在九十年代的恶性循环。李泽厚曾言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相比乃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此言概括虽然粗疏,却也八九不离十。八十年代许多名噪一时的新理论新方法,如今看起来都是非常可笑,立论不稳。诸如社会上流行的“三论”,金观涛夫妇提出的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性结构等等,虽然看似有理,却缺乏明确的学理支撑。整个八十年代真正扎实的学术研究,极为稀少。这种情况到了经历过历史大变局的九十年代,才有所改观。
汪晖学术转向的另一原因,乃是其主编《读书》和《学人》的重要契机。在汪晖主编读书之前,《读书》整体是偏向人文趣味,汪晖接掌《读书》之后,其办刊思路乃至方针逐渐向社会科学领域转移,但汪晖自己的学术立场,让他开始在选稿中立场偏向极其严重。诸如在他接掌图书三年之后,即二零零零年,读书刊登了美国学者高默波美化文革的文章,引起了知识界的轩然大波。
与汪晖一样从文学史研究转向思想史研究的陈平原,却没有像汪晖那样走火入魔,误入歧途。虽然陈平原和汪晖一起主编《学人》丛刊,在九十年代引起了极大关注。陈平原做学问与汪晖相比,更为扎实和按部就班,丝毫没有汪晖大跃进式的学术转向,刚写完文学史研究的著作,转身写出了四卷本吓死人的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陈平原的另一长处,就是始终坚守学术本位,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学术界的所谓左右之争,远离了诸多俗世纷扰。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汪晖在《学人》十年之后写下的纪念文章中,对于《学人》走来的这“小小十年”,语气不胜感慨。
翻开汪晖号称代表作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杂乱无章。第一部上下卷的标题为“理与物”、“公理与反公理”,第二部上下卷的标题为 “帝国与国家”、“科学话语共同体”,其体系之混乱,思维之跳跃,让人瞠目结舌。我仔细读完这四卷本,仿佛吃了一顿怪异的杂烩汤,说不清楚什么味道。只见到铺天盖地的学术术语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西方学者怪异的名字。这样的所谓思想史,严重混淆了思想史的界限,就笔者所涉猎而言,葛兆光、韦政通两位学人的《中国思想史》,就比汪晖来得高明的多。而且这两位先生的思想史,篇幅虽然不及汪晖,但是却没有汪晖那样吓死人的排场,以及所谓宏观叙事的巨型架构。
汪晖这种思想史的写法,说到底就是唬人。这种拿外国人吓唬中国人的本事,五四以来,源远流长。但是即便是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敢像汪晖这样肆意夸大自己的国际学术影响。即便是胡适这样师出名门,也只是谨慎为人为文,安守本分罢了。汪晖与五四那一代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五四时期诸如胡适这样的西化派,乃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方法,来观照自己所研究的东方文化。而汪晖则是将西方理论生吞活剥,如同贴标签一样将西方的理论与术语贴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上,因此其在《反抗绝望》中以克尔凯郭尔比附鲁迅,尚有他早年阅读鲁迅的心得体会与其阅读西方著作的心有相契,及至他写下《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已经全然演变成一种毫无精神共鸣的学术生产。公理与名教、教育改制与心性之学,这些中西混合的怪胎,成了汪晖走火入魔的绝佳凭证。
三、从长江《读书》奖风波到抄袭事件
二零零零年,由《读书》杂志承办的长江读书奖,由于汪晖的获奖引起了巨大争议。本来汪晖获奖并不能引起太多的关注,顶多是人们在认可程度上有所分歧。事实在于,汪晖获奖的同时还担任着这个奖项的评委,这就让人贻笑大方。而获奖人之一钱理群先生也和汪晖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汪晖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钱理群先生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但是这一次两人同时受到指责。在《读书》奖风波之后,汪晖最终被拿掉了《读书》主编,钱理群先生还发表了一些很不负责任的言论,为汪晖辩护,具体情况可参阅萧夏林文章《两个钱理群》。
时隔十年,汪晖抄袭案事起,钱理群先生又犯了天真的毛病,又一次为汪晖辩护。钱先生本来可以保持沉默的,因为汪晖抄袭的论文答辩委员会各位委员几乎都是钱理群的老师辈,诸如严家炎先生。利害相关,总要避嫌才好,但是钱先生又一次犯了低级错误。王彬彬听闻了钱理群先生的表态后大为失态,破口大骂钱理群先生无耻,并要求记者原文刊登。可能钱先生也不想再趟这趟浑水了,对王彬彬的咒骂表示宽容之后,也闭口不谈。钱先生的胸襟,当然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屡次犯错,则让人遗憾。
从二零零零年的长江《读书》奖风波到二零一零年的抄袭案,汪晖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但最后总是四平八稳。除了民间社会的质疑,以及知识分子的批评,鲜见体制内或是汪晖的单位对于汪晖公正的处理。截止到目前,清华大学网站上依然挂着《严谨治学的学者汪晖》这样的文章,汪晖的教授照当,国务院津贴照拿,没人来管。仿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事实上这些事情,都昭显了汪晖之于公理、常识的冷漠和忽略。长江读书奖风波中,汪晖表示他只是召集人,并没有参加评奖,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抄袭事件中,汪晖又说希望学术界自己去澄清。这两起事件发生的时候,汪晖都声称自己在美国,真是无处不巧合。这些言论归根到底,汪晖在为自己开脱,回避实质问题。
而我们细细来考察这两件事情,前一次汪晖的身份是《读书》主编,他这一明显违反学术规则的行为,让《读书》蒙羞。而后一次抄袭案中,汪晖的主要身份是清华大学教授,同时还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抄袭一事,让清华丢脸,也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这一头衔的公信力引起人们的怀疑。有人以这两起事件为例,将其看做知识界在九十年代末左右之争的延续。坦白而言,这种概括并不确切。长江《读书》奖风波的实质,乃是学术界对于学术腐败学术公正性的讨论,少有涉及到具体的学术观点。而抄袭事件,则牵涉到学术造假等严肃的问题。不能因为在这两次事件中批评汪晖的徐友渔、王彬彬诸君是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就将他们对汪晖的批评看做左右之争,而有人将王彬彬批评汪晖看做南京大学对清华大学的挑战,则更是无稽之谈。
坦白而言,就汪晖的学术能力而言,并不差劲,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女士一再强调这一点,但世道轮回,旦夕不测,当年以《反抗绝望》暴得大名的汪晖,会在多年之后被王彬彬揭开抄袭的老底。本文的意旨,也在于提出自己的质疑,看一看汪晖如何从一介本分的淮扬书生,一步步被塑造成为一个学术神话,以及最终这个神话如今已经破裂。我想通过此文,刮去汪晖身上厚重的油彩,还其一个干净自由身。不管这种工作会不会遭人记恨,我都觉得很有意义。
责任编辑: zhongkang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0/0717/172677.html
相关新闻











 中国美院教师抄袭海外画作曝光 民讽:这不是抄袭 是复印(图)
中国美院教师抄袭海外画作曝光 民讽:这不是抄袭 是复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