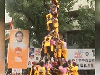一个人,要心怀怎样的绝望,才会在42岁的年龄,选择跳海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天,是1957年11月20日下午,石挥从批判会场回来,妻子童葆苓正要出去。她是著名京剧演员,团里安排她去接待来访的越南文化代表团。石挥一听说妻子有事外出,一下子把童葆苓抱住,拼命地上下吻她,久久不肯松手。童葆苓感觉丈夫有点异常,但因为忙着赶往剧团,也没往深处去想,就匆匆出门去了。
傍晚,石挥从家里出来,往码头走去。上影厂一位同事在路上碰到他,问他去哪里,他答非所问地说:“再也不能演戏了。”暮色中,石挥来到黄埔码头,买了张票,登上了开往宁波的“民主三号”客轮。从此便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有段时间,大家对他的失踪议论纷纷,有传闻说石挥去了香港,到了台湾,远赴美国,投向了西方怀抱。
总之,这位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全才,是永远地离开了。
他的离开,标志着一种无与伦比的表演艺术的终结。
40年后,张国立、李成儒、何冰联袂出演根据老舍原著改编的电视剧《我这一辈子》。最初,导演张国立让葛优饰演男一号福海,葛优推辞说:演不了,演不了。最后实在找不到主演,张国立只好亲自出演男主角。
平常谁都想争演主角,这次却纷纷避让,原因不为别的,就因为40年前,这个角色石挥已经演过了,而且演得无法超越。虽然后来张国立也演得不错,但老舍的儿子舒乙仍然认为,石挥比张国立演得强多了。
大导演谢晋曾说过,如果《芙蓉镇》的男主角换成石挥,那绝对比姜文演得还要出色。
早在1940年代,石挥便为自己赢得了“话剧皇帝”的声誉。
1941年,26岁的石挥凭借《正气歌》中的文天祥一角广为人知;又因《秋海棠》一剧红遍上海滩,这部话剧他平均每场要谢幕12次。如果他不巧生病,无法上场,角色由替补演员出演,观众会闹着要求退票。梅兰芳特地去剧场观看了石挥演出的《秋海棠》,感动得落泪说:“我太投入了,我忘了这是在看戏。”
此后,剧团再写《秋海棠》的海报,广告词就改成了“女士们看本剧请带两条手帕”。
舞台上的石挥犹如天才,其出神入化的演出,就连《雷雨》的编剧曹禺也赞不绝口,由衷地说:他扮演的鲁贵,比我剧本中写的还好。
石挥不是科班出身,他对艺术的感觉,来自他独到的体会。他兼采各家之长,把中国民间的传统特色,和英国哥格兰的“表现派”融为一炉,形成了一套个人的表演风格。他对凡事必须遵循苏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做法不以为然。
在表演上,他坚持走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路子,与当时流行的主流手法保持距离。他塑造的人物亲切自然,与时代要求的高大形象相距甚远。他以观众的好恶为取舍,痛恨概念化公式化,无形中使自己站在了政治标准第一的对立面。他的艺术观与新的文艺方针格格不入,尽管他努力地改造自己,向新时代靠拢,但他拍摄的歌颂解放军的《关连长》,仍受到来自各方的批判。此后,为配合革命文艺的需要,他导演了《鸡毛信》、《天仙配》和《雾海夜航》三部影片,但仍然跟不上新的文艺方针的要求,这让他倍感压抑。
1956年,上面提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在文艺创作上,要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石挥听到有关讲话的传达,极为振奋,撰文发言,诉苦衷、批外行、倡传统,将憋了六七年的胸中块垒,一泻而出。后来风向一变,他便成了极右分子。
突然之间,所有的嘴脸,都从昔日的温和,像川剧中的变脸似的,一个个凶恶起来,疾言厉色地发出声讨的怒吼,让他大惊失色,越来越感到人性的险恶。
从后来的结局看,石挥的失踪是接连两天开会的结果。他的上影厂同事,竟然罔顾事实,断章取义,揭发批判他的所谓右派言行。说他骄傲自大,自以为有点成就,就跟组织讨价还价;说他写文章否定党的领导,嘲笑他根本不懂艺术,只知道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揭发他道德败坏,流氓成性,吃喝玩乐玩女人,在周璇生病期间公然对其强奸……总之,几乎一夜之间,石挥便从观众喜爱的名导名演,变成了人人喊打的恶魔;从卓越的电影艺术家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黄宗江在回忆录里说,40年代,他和石挥一同住在上海的亭子间。有一次,他听见石挥说过一句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天下人都是王八蛋”。在这句极端恶毒的咒骂之中,深藏着对险恶人性的憎恶和轻蔑。当一个世界充满太多邪恶的时候,当他所珍视的艺术已经不复存在,他的人格已然成了众人可以随意践踏的泥土,这个眼前的世界,还有值得留恋的必要吗?
石挥失踪后,对于他的批判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在1958年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上影厂副厂长张骏祥发表了一篇名为《石挥是电影界极端右派分子》的文章。这位清华毕业的留美硕士,以诛心的语言揭露说:“远在上海沦为孤岛的时期,石挥就煽动人脱离当时党领导的剧团上海剧艺社,破坏剧运。解放以来,石挥随时随地,从讲笑话、说相声到写文章、拍电影,不放弃任何机会,千方百计地诬蔑、讽刺和咒骂党,反对党的政策和党的文艺路线。在鸣放期中,他更认为‘翻身’的时机已到,猖狂地发表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文章,喷吐出蕴蓄在他胸中的毒液。”
在紧随其后的《中国电影》1958年第1期上,以导演《一江春水向东流》、和《乌鸦与麻雀》闻名于世的郑君里,也发表文章《谈石挥的反动的艺术观点》,从艺术的角度批判石挥。郑君里说:“石挥从来不放过一个最小的机会在正面人物的鼻子上抹灰”,“他狂热地夸大了正面人物的所谓阴暗面,用欣赏的态度加油加酱,从中制造各种笑料,去迎合小市民观众的低级趣味”。作为导演,“他可以轻轻地一笔勾销了思想对剧本的指导作用”;作为演员,他反对史坦尼表演体系。说什么“英、法的表演大师就不按什么史坦尼,你能不承认他们的艺术?”这些都是石挥典型的反动言论。
郑君里甚至武断地说,石挥根本算不上演员,他只是一个卖弄“恶性海派噱头”的“戏油子”,他的戏包袱里装的全是破烂。总之,“无论在编剧、导演、表演各方面,石挥一刻也没有放松在经济上把它变为个人抓钱的手段,在政治上把它变为向新社会、向人民进攻的武器。……金钱、女人、吃喝是石挥生活中三件大事。”
这一类批判文章,电影出版社在1958年底,把它们汇编成两本反击右派的集子,书名是《捍卫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这本书的续集选登了赵丹和瞿白音合写的文章——《石挥“滚”的哲学和他的才能》。石挥跟青年演员说过这样的话:“跟我滚两年,包你能滚出来,滚成个名演员。”赵、瞿认为,“滚”的中心思想,即“票房价值”,就是千方百计地迎合当时的资产阶级和城市小市民观众的落后趣味,赢得他们的笑声、掌声。两位作者还“根据同志们揭发的情况”,历数石挥的罪恶:出身于破落的大地主家庭,最早是一个“五分钟”演员,后来混进上海剧艺社,演了文天祥,一举成名。他从此骄狂起来,在剧社制造纠纷。与此同时,他买通小报,吹捧自己,把自己加冕为“话剧皇帝”。解放前夕,他做了演出的老板,剥削同行。还做过投机倒把的棉纱交易,穿着美军的军服,任意打骂三轮车工人。解放后,“党耐心的教育他,争取他,给他重要的创作任务……可是他欲壑难填,大声的叫嚣‘党埋没人才’,‘不尊重传统’,‘扼杀创作意志,没有自由’,‘新社会只叫人说假话’……他到处放火,到处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向我们党和人民猖狂进攻”。
在一派批判声中,石挥编剧导演过的电影、话剧,从《关连长》、《我这一辈子》到《雾海夜航》都成了批判者的靶子。
当以上批判甚嚣尘上的时候,1959年春,有人在吴淞口外的海滩上(一说是芦苇荡里)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因浸泡时间太长已无法辨认。从西装口袋里的派克钢笔和腕上的手表推断,警方初步断定是石挥。另外,男尸修补过的牙齿,经上海华东医院对照石挥补牙时的X光片,最终确认死者就是失踪一年多的石挥。
三十年后,电影界重新评价石挥,过去所有的批判,都成了不实之词。所谓强奸的真相,是他与周璇恋爱,正准备结婚时,香港传出周璇的绯闻,他大受打击。后来周璇患精神病回到上海,被上影厂的一个美工强奸。
而当年制造谎言,撰文揭批石挥的积极分子,后来也受到各种迫害。瞿白音因为一篇《关于电影创新的独白》,在1964年被打入另册,文革中又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饱受折磨,“四人帮”倒台不久即撒手人寰。张骏祥被关进“牛棚”,郑君里惨死狱中。赵丹1967年12月被捕入狱,被捕前后屡遭毒打。1980年逝世后做尸体解剖,医生告诉黄宗英说:“赵丹身上,没有一块地方没伤,包括两只耳朵。”
当一场浩劫结束之后,受迫害的人们都在大声控诉,可很少有人反思,他们的厄运与反右时的紧跟、表态、落井下石有什么关系;他们当初不顾事实,违背情理,上纲上线地揭批石挥,最终害死的不但是石挥,也绑上了自己的命运。
几十年后,有人在回忆中增加了一些石挥失踪的细节。石挥那天登上的民主三号轮船,是他拍摄《雾海迷航》时体验生活和拍摄外景的地方,因此船员们都认识他,以为他又是来体验生活的。
当天夜里,有好几个人看到石挥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甲板上,望着大海出神。
之后,他就失踪了,消失在了波涛滚滚的大海上。
资料来源:
1、《石挥与童葆苓的爱情生活:三年夫妻缘,远胜百年情》
2、《永远的石挥,被誉为我国最好的演员,42岁消失在大海之上》
3、《石挥之死:带着对人性的失望,他纵身跳进大海,那一年,他42岁》
4、百度百科《石挥》
2022-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