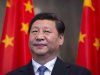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重刑。
汉文帝的时候,有一任廷尉(相当于大法官兼司法部长)叫张释之,有一次有个盗墓贼偷窃了汉高祖庙里的玉环,被卫士抓获。汉文帝十分恼怒,于是就责令张释之严惩此人。
张释之审了半天,依照当时的相关法律,奏请文帝判处他弃市。
文帝一看这个结果就大怒,说我把这个人交到你手上,为的就是让你判他个夷灭三族,你居然只把这个人砍头了事,你这也太糊弄领导了吧!
汉文帝的意思就是,这事儿我很气愤,所以你必须搞株连。
张释之一看到天威震怒,就免冠叩首说:“皇上啊,依照法律,弃市已是最高处罚了。如果您觉得盗窃个宗庙器物就要诛灭全族,如果以后有人偷挖长陵上的一抔土,又该如何处罚呢?”
汉文帝很聪明,一听这话,就有点醒悟,回家跟老妈薄太后商议了一下,就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决。

我觉得,相比那些动不动就要“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的“大有为之君”们,汉文帝这个人,好歹算是个有点人味儿、会说几句人话的君主。他有的时候真的能俯下身子,站在平民百姓的视角去审视问题。
你看他想修个露台,一听说要花费十个中产之家的财产,立马就不干了。
这在中国古代的王侯将相中,是一种大熊猫一般的稀有性格,后世帝王,大概也就宋仁宗又灵光乍现了一回,其他帝王将相想的更多都是“我的计划很大,你们忍一下”“再苦一苦百姓”之类的玩意儿。

而汉文帝的这种平民视角尤其体现在他对司法的量刑主张上。
汉袭秦制,本来法律是相当严苛的。可是有一次,齐地的官员淳于意犯了罪,依律要执行肉刑,他的女儿缇萦就给文帝写信,说:肉刑这个刑罚实在是太残酷了,肢体被砍掉了,就没办法再长出来,以后犯人即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过原来的生活了。身为女儿,她请求文帝不要让父亲接受这种刑罚,而作为代偿,她愿意自己卖给官家做奴婢。
汉文帝接到这封信之后就深为感动,同年就下诏废除了肉刑。不仅如此,他还举一反三,觉得一人有罪,亲属邻里连坐这个刑罚似乎也没有什么道理——淳于意犯罪,为什么要把他的女儿卖为奴隶呢?所以文帝又干了一件后世非常少有的举动,那就是废除了先秦以来一直沿用,已经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连坐法”(首孥连坐)。
如果按照法家那种“老百姓就是欠管,不重刑就会乱”的理论,文帝朝的大汉应该是一个狼烟四起,各地盗贼纷纷扯杆子造反的时代。可是历史的事实证明,文帝时代,恰恰是秦汉帝国、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帝制时期治安、民生都最好、经济恢复最迅速的时代,文景之治的盛世一直到今天都被拿来吹牛。这说明一件事,那就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个正经当了几年皇帝(之前是秦始皇和汉高祖)的人,汉文帝开创的这种(相对而言的)轻刑主义思想,其实是行得通的。
然而,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文帝开创的这种轻刑主义传统,在古代中国终究只是昙花一现,连坐、肉刑等制度在他死后很快就被他的子孙景帝、武帝那里被恢复了。到了司马迁因为说错一句话关键部位挨了一刀的时候,太史公虽然觉得自己这一刀挨得很冤枉,但已经无法像当年的缇萦小姑娘一样,说出砍掉的肢体不能再长出来,所以肉刑不对这种有朴素的法理学认知的话来了。
整个中国古代其后的刑罚发展史,基本上就是沿着用刑越来越重,株连越来越广的方向去演进。株连范围从最开始的“夷灭三族”、发展到后来的“诛九族”、“十族”乃至“瓜蔓抄”。而杀人的方式,从最开始的砍头、弃市发展到了后来的腰斩、凌迟……
我曾经一度非常奇怪,为什么我们古代历史上明明有汉文帝那样有人情味、知道“节刑”的上位者,却依然拉不住法律的缰绳,让法律朝着重刑的一边绝尘而去呢?
直到后来,我又重温了汉文帝与张释之的这个故事,我才看出了一点端倪。你看,在这个故事中,汉文帝本来是个非常注重节制刑罚的皇帝,但听到有人偷了他老爹庙里的玉环,气血上涌的时候,他依然高喊着要夷灭这个人的三族,完全忘了不株连、轻刑罚本来是他自己的主张。这当然可以理解——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呢,谁听说别人辱及自己祖先时能不发怒呢?
在古代帝制的那个系统下,“天子一怒”是容易被纵容,而很难被掣肘的。汉文帝的幸运,在于他碰见了一个敢抬杠的张释之,斗胆把他的冲动顶了回去,让皇帝恢复了冷静。可是,在中国古代史上,真正能像张释之那样直言敢谏的臣子有多少呢?像文帝那样能在盛怒之下听得进不同意见的皇帝又有几个?至少到他孙子武帝那里,就早没有了这样的雅量,张释之若是生在了武帝朝,这样跟皇帝顶牛的结果,多半是和太史公一样,被一刀了断了是非根。
所以重刑主义是所有人在愤怒时共同的冲动,而当一套体制没有机制遏制这种冲动、对法律进行回调时,司法向着重刑滑坡就会成为一种必然。
这种滑坡,让人想起了生物学上的“左墙定律”——一个醉汉,蹒跚的走在一条路上,左面有一堵墙,右面有一道沟,他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早晚会调到右边的沟里,因为这个进化模型中一个方向是被封死的,所以物种在随机进化过程中,早晚会走向相反的那个极端。
中国古代的法律进化史,其实也高度遵循这种“左墙定律”——由于愤怒的皇帝与愤怒的公众总是将张释之那样试图节刑、轻刑的司法官员视为“为犯罪者开脱”,司法者为了趋利避祸,在两千年的演进中倾向于用越来越重的刑罚去惩治犯罪者、若犯罪者这一条命还不够“解恨”,那就只能株连他的家属,于是司法只能向着重刑主义的极端绝尘而去。
而张释之在劝谏汉文帝时警告的另一件事,其实也在千年后应验了:“如果您觉得盗窃个宗庙器物就要诛灭全族,如果以后有人偷挖长陵上的一抔土,又该如何处罚?”
“挖长陵(汉高祖墓)的一抔土”其实是造反的一个委婉说法,所以张释之问的问题其实是:如果因为一些小罪就轻易动用重刑,那么真正遇到大恶时,又拿什么来进行惩罚呢?
这其实是一个重刑主义必然导致的“刑罚金属疲劳”问题,以重刑去吓阻某种轻罪,搞到最后大家都对重刑脱敏了,最后刑罚反而失去了其应有的威慑力。
这样的故事在古代史上也曾一再发生,比如明代曾经是株连、保甲、户籍制度都最严苛的朝代,犯罪者家属一旦被抄没沦入贱籍,基本上就世世代代永世不得翻身了。如果你的邻里、亲戚当中有人犯上作乱,除非你及时出首立大功,想不跟着吃瓜捞甚至砍头基本也不可能。朱元璋曾对他定下的这套“刚猛治国”术非常得意。
可是到了明末我们看到,这种“刚猛”对平定和恢复社会秩序基本没有起到任何正向效果。相反,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至少在起事初期都会采用最酷烈的手段去对待明朝的官民,所过州县屠掠无遗。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对于“流寇”们来说,既然从扯杆子造反那一刻起,就注定要被诛灭九族,那何妨把事情做的更绝一点呢?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张献忠
于是杀人在明末沦为一种像吃饭喝水一样大家都司空见惯的东西,最终社会从重刑主义、株连主义中除了让人们习惯了遍及社会的普遍性残忍,没有收获任何治理效果。
而重刑主义在古代中国的千年发展、延续,还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影响,那就是很多平民百姓,在长期的“熟读历史”当中也养成和大多数帝王一般的“帝王心术”,在他们看来,社会不够安定、有人作奸犯科,那就是因为治的还不够狠、杀人还不够多。治理什么什么犯罪“逮住就毙”、甚至抄没家产、让其子孙沦为二等公民,管准就好了。

这样的人应该会非常神往自己能穿越回古代,也能坐在把龙椅上发号施令,没有现代社会诸多常识的掣肘,他们幻想起来一定更爽。只可惜,他们常常忘了,现实中的自己,真的穿越到了那种时代,往往更可能成为被治、被杀的平民。
所以想起来也很感叹——你想想两千年前的汉文帝刘恒,那是一个有帝王命、却经常站在草根角度操一下心的、还算温柔的人;而两千年后的很多网民,却明明有着韭菜的命,操着帝王的心,他们明明没有九五之尊,却比历史上的秦皇汉武们更心如铁石。
这样的转换,我不知是怎样发生的。但我知道,重刑主义思想给他们造成的那种越来越拿人不当人看的影响,一定在这种千年转换中居功至伟。
昨天《“贪二代”们再混蛋,也证明不了罗翔呼吁错了》谈到轻刑主义和重刑主义。本来我在这两种刑罚主张之间是没有个人偏好的。但想起了历史,我总觉得,几千年的重刑主义倾向搞下来了,现在我们需要一点反向的教化,以便让很多认知错位了太久的人,稍微清醒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