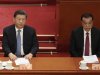我没有女儿。但对拥有女儿那种如饴在口的美好,感同身受。
有一天,春运。因为急着要去西昌采访,我挤上了一趟长途客车。人多极了,那趟车开进新南门客车站时,坝子上的人忽然像被磁铁吸引过去的粉末。司机并不立即停住,点一脚油门踩一脚刹车。粉末们一会东一会西。好歹停住,人们像抛石机一样抛进行李,有的从门里进,有的直接从窗户翻进去。
那是九十年代末的一个普通场面,空气里混杂着汗味,脚臭,蔬菜味,我身边坐着一对父女,准确的说是从窗户外冲进来一对父女,他把女儿递给我,自己又翻进来。
也不怎么谢我,坐定,他就急急地不知从哪儿掏出一只苹果,粗砺的手擦了几下,让女儿吃。女儿约莫四五岁,眼睛很大,眼仁黑黑的透着灵气,是西昌、大凉山女孩子常见的长相。
那地方的小女孩,干净的像未经雕琢的玉。她吃着吃着,就睡着了,阳光晒了进来,照得她的鼻翼也有些透明。
那父亲看着阳光,忽然掏出一张帕子,挡在窗上,其实是挂在窗帘早不知去向的一根铁丝上。车厢晃动,不一会儿,帕子掉下来,他又挂上去,用粗糙手指把帕子仔细卷在铁丝上……再一会儿又掉下来,他就不断挂上去。
最后他用身体挡住阳光,车行路上,阳光的角度不断变化,他调整着身体的姿势。其实徒劳。
但他很幸福。
我有些嘲笑,这粗人刚才为什么不用帕子擦苹果。
快到眉山时,忽然一脚刹车,女孩的头撞到前面座椅,哭了。那父亲破口大骂司机,很脏的川骂。又怕女儿疼,给她揉了揉额头,她哇的就吐了,他一伸手,接住了。
女儿一直吐,他一直用手接住,直到女儿平静下来时,他才有空扯下那张帕子擦自己的手。
我想,这是出门在外打工父亲用的万能帕子吧。
不一会儿,车停休息区,那时还叫加水。父亲抱着女儿冲下去,抢占了水龙头,给女儿洗着吐脏的前襟,手,脸……
天很冷,为了怕张冻疮吧,他又不知从哪儿掏出一盒抹脸的,擦手,擦脸,很仔细,却严重不分顺序。
这样的父亲终会老去,老得抱不动女儿,翻不进窗子,挡不住阳光刺眼。女儿慢慢长大,亭亭玉立,即将迎接自己的爱情、婚姻……
白居易写过一首极美的诗:苏家小女名简简,芙蓉花腮柳叶眼。十一把镜学点妆,十二抽针能绣裳。十三行坐事调品,不肯迷头白地藏。玲珑云髻生菜样,飘摇风袖蔷薇香……
有一天,这女儿走在路上被一棍子打晕,拐了坏人家,用铁链拴住,生了八个孩子,得了精神病……
你却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的不良风俗和贫穷使然,谁都想娶妻生子,跟饿了要吃饭一样,拐跑一个女孩,人性而已。
这太脏了。
为什么要站在施暴者的而不是受害者的立场呢呢?显得视角更广,更宽容吗。
你听得见女孩被强暴时呼唤天地无应破碎的声音吗。
真希望铁链女的父亲是杨佳,或者美国那个父亲。当全村目睹悲剧,二十五年连个报警的人都没有,此时别装逼告诉尚存正义的人:你要遵守法律。
双方不对等时,装公允,就是帮凶。
周云蓬唱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不要做乌鲁木齐的孩子不要做云南的孩子不要做南充的孩子。
白居易那首诗写的极美也极悲伤,后面的结局,我尝试翻译成大白话:
这漂亮的女孩啊,能把头发编出各种花的样子,她走起路来,衣袖间都飘出蔷薇的香气。
她举手投足,都那么婀娜多姿,她转动起来,浑身上下像是发着光一样。
这花儿一样的女孩,却在她即将出嫁的前一年,突然死掉了。
不要悲伤啼哭啊,她也许本不是世间凡物的妻子。她恐怕是天仙贬谪,只合着在人间待到十三岁。
好物易逝,彩云易散,琉璃易碎。
这段短文字,不算文章,手机上匆匆写就,最后:
每一个文字都是一个具灵性的符箓,我手写我心。别乱写,有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