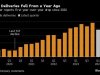我在本论丛之四提出香港人是“中英双重皇民化”的产物,这固然可以理解为“在我们身上包含着世界上两个最重要文明的文化基因”,但因为我们是位于岭南之南一隅、透过千百年中英殖民统治而间接获得那些文化因素的,所以除了好的东西之外,还遗传了不少杂质和渣滓。因此,看待香港文化,我们不能单讲承传,还需明白到有大量而细致的批判和建设功夫要做。那些杂质和渣滓,包括具体一件一个的文化物,更包括我们面对这些文化物时的意识和潜意识。举我们香港人的语言为例,就可说明清楚。首先声明,我说的批判,其实是站在意识形态以外的持平分析,就算是用了例如“皇民化”这类词语,也是只取其客观部分、不带褒贬。
语言的形成有两种因素,一是生理心理内育的,一是家庭社会政治外加的。后者是本文讨论范围,包含了我们对自身语言的好恶、应用范围和认知立场,以及我们生活里各种政治和权力机构对语言的规范。
我首先不谈政治因素,只从语言科学的观点讲什么是香港人的母语,再论述中英殖民政权对这母语的规范,以及这种规范内化到了香港人语言意识的什么程度。
自英港殖民政权在战后逐步普及教育、从小一起要求英语学习那时起,香港人的母语便逐步偏离粤语,大约在七八十年代已明显过渡到一种一般生育妇女都讲的、在每两代人之间紧密承传的自然语言;这个语言包含了英语、华语及港人自创的语元,例如“baby洗petpet啦咪喊”。学术上,这个语言可归类为克里奥尔语(creole)或混合语(mixed language),两者如何区别,语言学家还没有清楚定见;我称这个年轻的语言为“香港话”,其主要构成语–华语和英语–都同时提供大量语词、文法和音韵,混成的比重视年龄、学历、职业和社会阶层等因素因人而异。
这样构成的“香港话”是一种很奇妙的语言,有本身稳定的、不同于华语及英语的动态语法规范,掌握此语的人能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象,本能地调校两者的比重、发音和其他语言特征。一个只谙华语或只谙英语的人,无法与讲地道香港话的人达至“双向沟通”(mutual intelligibility);香港话和华语、香港话和英语这两对语言,因此都各自满足了语言分类学视为区别不同语言的充分条件。这是从语言科学的观点而言。
但很不幸,由于受到英港和中港两个殖民政权长年政治压抑和歧视,讲香港话的人被讥为“两头不通”,连粤语正统派人士也指摘讲此话者“咬字唔正”、“多懒音嗲韵”,香港话于是沦为三等、四等语言,在自己的土地上的地位比粤语更低,无法向高雅方向发展,甚至讲此话者自己也鄙视自己,那便是港人被“中英双重皇民化”的最典型例子。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非常广泛深入–大家看看,我为什么刚刚写的是“最典型例子”而不是华英混合的“最typical嘅example”?
真要讲语言政治,应该这样看:2019年之前,当大多数香港人还相信一国两制、承认中国是香港的最终主权国的时候,说“我们的母语是粤语”,虽然从语言科学的角度看已经是错的,但从语言政治的角度看,还可勉为其难,因为那时要抵抗是北方官话普教中;说到底,坚持一国两制不过是坚持了中国的一种地方主义。但是,2019-2020期间,香港人主体意识已经跃然而起、全面确立,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国族认同。今天,我们的第一政治纲领是光复;假如仍然说“我们的母语是粤语”,难道我们要的是把香港光复到中国的一个省里再搞一次地方主义吗?
当然,我们不是全面反对粤语;在广东发生的粤语运动我们大力支持。在中国内部,分离意识不能浮出水面,提倡地方主义所以是好的,但我们香港人已经超越了那个境界。
今天,在透过多年艰辛付出、建立了自身的身份认同之后,香港人需要提倡的不再是粤语,而是与中国语包括其各种方言都大异其趣的香港话。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在语言环节里日益自觉地把包括粤语在内的中国语看成不同程度的“他者”;舍此不能建立健全稳固的“香港人”这个“我者”观念。不如此合语言科学之力与中国意识划清界线,对着文化实力和政治攻击力比我们强大千百倍的中国,新生的香港人主体性不可能存活,而必然走上像台湾那批49年大陆难民终了要和中国统一的下场。诚然,达至无有他我之分的“一个世界”,乃崇高终极理想,但现阶段绝对化地要求不分他我,却是一种错误;君不见2014年民主阵营里反驱蝗者的荒腔走板,结果和梁氏统治集团对了完美口形?
不错,语言的一个作用是沟通,但它的另一个作用却是区隔,在什么时地应该强调哪一个,要看场景。我举一个以语言作防守性区隔、尽量切断与他者沟通的实例。2009年耶鲁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斯科特(James C. Scott)发表了一本力作《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他的研究对象,是生活在横跨中、印和印支五国、面积比欧洲还大的地域(他称之为 Zomia)之内、海拔一千英尺以上亚热带森林里的“高山族”。
大家都知道,台湾和海南岛都有所谓的“高山族”;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些族人好端端平原河谷海岸那些经济富庶且生活方便的地方不住,却要跑到森山野岭里与禽兽为伍?答案很简单:他们世世代代本是住平原的,却因受到帝国殖民入侵像香港人一样失掉家园,之后节节败退,最后被迫上高山,成为人类学从来没有的“高山族”(有些这样的人被赶到海里,成为蜑家/蛋家,香港人则是被赶到发达国)。斯科特研究的“高山族”,是在大约两千年前开始,给逐步迫上高山的;他们要逃离的,主要是汉族、尤其是明清两朝夹中国政治军事势力南来的汉殖民政权,以及印支半岛上的缅、泰族政权。
根据长年的在地研究,斯科特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高山族”都可谓现代意义下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愿生活在殖民政权底下,不愿交税、做徭役、忍受官僚压迫、被同化到某种形式的国家结构(state)里而宁愿逃到政权不易伸展到的深山野岭,为的是保留个体自身的独立与自由。“他们利用自身的文化、耕种方法、带平等主义的政治组织、神司领导的反抗运动、甚至那没有了文字的语言来分隔开他们的社群和那些想吞没他们的政权。”
“那没有了文字的语言”是怎么回事呢?斯科特指出,这些被压迫的民族本来是有使用文字的,虽然文盲的是绝大多数,而掌握文字的,多半是生活在这些民族和汉、缅族交接线上的一些买办阶级;他们用的书面语是一些含汉、缅字元的pidgin。这些能书写的人相对富裕,在汉缅势力范围里也可以生存得不错,所以多半不会上山;愿意上山的,也会发现在山上的政治环境里,他们的书写能力没有多少价值,久而久之也就消失了。但是,斯科特进一步指出,这些“高山族”至今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字,很可能是一种自觉选择。他们还在平地上生活的时候,文字最根本的功效是让政权把他们纳入控制范围里。
试想,一个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的群体,是很难有效纳入政权的户籍里成为征税和摊派徭役的对象的。同样,一个人如果没有名字,政权就很难通缉他,尤其是在没有摄像技术的时代。语言可以用来沟通,但能沟通就有被政权网罗的危险,那些 Zomia“高山族”于是索性不要文字,上山之前把一切文字记录销毁;只有口语的语言于是产生一种区隔、保护的作用。这不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原来,自由并不是西方文明知识人独有的概念,而且为了捍卫这自由,有些东方人可以去到好尽!
当然,处岭南之南一隅的香港人汉化程度,已经不能像上述那些“高山族”那样摆脱含汉语元素的语言;故上述研究只能说是提示了我们:在滴水难抗汪洋的情况底下,香港话每进一步从华语异化,都有利于我们与中港殖民政权区隔,强化我们的自身认同。因此,所有的“咬字唔正”、“多懒音嗲韵”等语言异化,其实都是有用的、好的。但要大多数香港人接受“反语言大一统”、与自己固有的语言观念背驰不会容易,因为那必须自觉破除很多定见、摒弃那些在我们过去争取进入社会中上层过程里接受了的各种皇民化荼毒,返璞归真,从新认识、珍惜语言最根本的发展规律就是“约定俗成”,而这一点,却正正是政权的大忌!
香港话还在发展,特别在海外。不少人担心自己每天讲的香港话,会包含越来越多的外来语,到我们的下一代更不必说。但我认为,那主要是香港话的进一步与华语异化,在两至三代人之间也不会因此令之完全消失。在思考香港话该选取什么演化方向最有利于延续并强化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时候,我提议多了解日语的发展历史并从中借镜。日语的来源问题很复杂,学术界百年来众说纷纭,有认为是阿尔泰语系与南岛语系碰撞产生的一种远古混合语,后来又加入了大量中古汉语元素,但今天的语言学家依然无法把日语归类,只好认定它自成一家。可以想象,古代日本或有一些“哈唐族”批评其他日本人读汉字“咬音唔正”、“多懒音嗲韵”,事实没错却不但无阻日语成为一种独特的、优秀的语言,更成为了日语和华语之间的一个自然区隔。这也许才是最值得我们香港人羡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