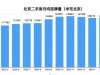网上看到一篇有关北京知青下乡插队部署工作的文章,勾起了我与北京知青一起生活的一段回忆。
1966年文革开始,大学停止招生,工厂停止招工,城市的中学毕业生,除了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别无出路。据北京市劳动局统计,到了1968年7月份,北京市三年累计毕业生已达25.8万人,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
于是中央出台了“上山下乡”的战略部署,在半年时间内,北京市开展了三次上山下乡大动员,目的地分别是东北、内蒙古和山西。这三批都是通过办学习班,忆苦思甜、斗私批修教育,由领导动员、学生自愿报名组织的,但只完成了五万多人,是全部毕业生的一个零头。
可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当年的12月21日发表了著名的重要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最高指示就是命令,自愿不自愿都得服从,从此掀起了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运动。
1968年12月初,我们村迎来了北京来的十多名中学生,他们应属于那批自愿报名来山西的三万两千人之列。那年我十一岁,正在本村上五年级。
知青们是被公社那台唯一的机动车,苏制“小嘎斯”送来的。小卡车就停在我家的打麦场上,大队组织了群众敲锣打鼓来欢迎。知青们除了自己的行装之外,还带来一大捆《毛泽东选集》,是北京市政府送给我们村的革命礼物,每户都分得一套“红宝书”。
我们这个小山村一共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家家都住土窑洞,生产队并没有可用的住宿地方,只能把他们安排到社员家里。实际选择的是我家和我堂伯、堂叔三家,每家各分了四五个。说来有意思,知青是来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可我们家是中农成分,堂伯和堂叔两家还都是富农,属于“阶级敌人”呢,也不知道这干部是怎么想的。
我家分来四个女生,穿着打扮整齐划一,都是那个年代北京女孩的标准形象:头上梳两条齐肩短辫,一身灰布衣服。上衣是北京特有的那种半长棉大衣,那种大衣在改革开放初期曾风靡半个中国,我在北京上大学时,老家不少人都托我给代买过。知青的衣服并不是新的,有些褪色,但很干净得体。
我家向阳的小北窑被腾出来给知青做了宿舍。这窑本来是我与哥哥住的,我们不得不搬回到大东窑,与父母和妹妹共享那两个前后相连的大土炕。北窑里原有一个炕,可睡两人,爸爸又在地面上用木板和条凳搭起一个简易大床,供另外两位用。
知青们自己开伙做饭,刚开始粮菜供应是由上面负责的,标准远远高于村民。普通社员家里的主食都吃粗面馍和咸菜,但知青吃的是白面馍和炒菜,只是村里人发现他们蒸的馒头硬得能打死狗。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是“老三届”的北京知青,刚巧当年也在晋南插队,他证实了我的说法,认为他们当时吃饭上真没受苦。
当地人称知青为“洋学生”,这个称呼没有贬义,只是很形象。因为他们是大城市来的学生而已,我们本地也有中学生,从没人管他们叫“知识青年”。
“洋学生”虽然每天与社员一起下地,但生产队并没拿他们当作重要的劳动力。看待他们就像那些上面派来的“蹲点干部”一样,知道他们过段时间就会走的,不会长久。再说了,队里毕竟就是那么多地,那么多活,在那个生产条件下,多几个知青不会使地里多打粮食。因此对他们的劳动没有严格的要求,像挑担、驾驭牲口等重活、难活也不会安排他们干。所以知青小团体和村民始终是两张皮,并不能像领袖期望的那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或者说像一坨黄泥与一坨红泥揉在一起那么简单。
上级也注意到生产队并不能有效地对知青“再教育”,后来就把他们归属到了大队林场,吃住条件不变,只是干活在林场。大队林场管理着一百多亩苹果园,那时候果树不施肥也不浇水,一年里就是剪枝、喷农药、摘果子这三件事,活路简单而不重,员工不多便于管理。苹果快成熟时,有村民路过看到有“洋学生”在吃苹果,还用小刀削了皮,很是愤愤不平。认为他们能天天随便吃苹果就是莫大的福利了,还要削了皮吃,太娇性了。
我家的四个知青姐姐,性情各异,特点分明。最成熟稳重的是王志贤同学,一看就是班干部的模样。她平时表情矜持,言语不多,没见过她高声说笑。但在开大会时,她总是代表知青发言,慷慨激昂,立场鲜明,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很快就入了党,第一个抽调回城走了。
另外两位徐淑英、张连弟,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形体反差很大,但却又形影不离。俩人属于那种老实本分、默默无闻的类型。她们在村里呆的时间最长,好几年都没有捞到回城的机会,好像真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最终当地政府安排她们进了县里的机械厂,当了工人。我去县城时看过她们,一身蓝色工作服,带着些许油迹,在那个时代也是让人羡慕的工人阶级形象。再后来她们年龄也大了,就在当地结婚生子,一直干到退休。据说孩子享受了政策照顾,去了北京。
四个女知青中,个性最鲜明的是卢平姑娘,身材娇小,圆脸大眼。她性格活泼直率,能说爱笑,每天的话要比其他三位加起来还多。可能是性格上的差异,她与其他三位的关系不怎么融洽,出出进进总是一个人耍单帮。晚上收工在家很无聊,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连电灯也没有,我们村不通电力。卢平总会跑到我们家住的窑洞来,和我们一起聊天。我爸爸提醒她要和同学们处好关系,她振振有词地说,她们三个人不可能长期好,只有两个人才可以长久保持好关系。
我也最喜欢找卢平玩,她给我看她的压箱底的宝贝:一张大大的手帕,上面别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让我大开眼界,她也送了一枚给我。最神奇的是那个夜光像章,用手电筒照一会儿,就会在黑夜里发出灿烂的光芒。
春天来了,我用纸盒养了几只蚕当宠物,她就天天和我一起伺弄:喂桑叶,清理粪便,直到蚕宝宝成熟结茧。蚕茧都是银白色的,但卢平说,北京的蚕结茧是彩色的,有红的、绿的和黄的等等,我将信将疑。后来我确实也养过彩色的蚕种,但只有红色和黄色,并没有绿的,看来她说话有一定的水分。
卢平也跟我爸爸妈妈聊村里的人和事,常常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给人定性,爸爸不同意,她就说:“大叔眼大无神,不分敌友。”
到第二年秋天时,卢平的妹妹也中学毕业了,从北京跑来看姐姐。卢平很高兴,特地领妹妹“二平”见我。二平比姐姐小一岁,长得比姐姐秀气文静,没那么多话。再后来卢平也走了,不是抽调回城,而是随妹妹一起去安徽农村了,据说那儿是她爸爸的老家。
转眼间,半个世纪就过去了,我与四位知青姐姐走过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地点轨迹重合到了一起。回想我们共渡的一段短暂的历史时光,真实体会到了那句名言:在历史长河中,个人只是一粒随波逐流的沙子,大浪把你带到哪里,就在哪里上岸。如今我都成退休老人了,她们也已年过七十了。我真心希望她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2022年2月21日于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