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普通的故事,可能在你身边俯拾皆是,但又弥足珍贵。
仿佛上班途中行色匆匆的路人给你一个真诚的微笑,或者从环贸出来的时候前面的人替你扶了一下即将关上的玻璃门,又或者,高铁上坐在前排的人观察了你的行李后自始至终没有把他的座椅靠背放下来。
这些细节很重要,这个族群成色几何,这些都是必答题,至于我要讲的故事,可以作为加分题。

我是重庆人,1990年大学毕业留在了上海《文汇报》工作,工作了两年,1992年的某一天,政法部的Y老师找我,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我说我有女朋友的,Y老师说报社年轻人都说你追求的上海女同学没看上你。
我说:“他们晓得个锤子。”
老头说别硬撑了,人家说那女孩子都要出国了。
我捶胸顿足:“册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出国。”
老头摸出一张照片说,姑娘跟你一样大,合资企业工作,上海人,家里独女,条件可以的。
我看了看照片说:“这也长得太善良了吧……”
老头有点急了:“哎呀,实话说,我也在求她父亲帮点忙,你要不去见一下,成不成再说,侬就当帮我老头子一个忙。明天中午12点,南京路德大西餐馆。”
1992年我才不到24岁,Y老师我不好得罪的。

中午在德大刚坐下,姑娘就到了,那年头手机微信啥都没有,很不方便,还好提前看过照片,我见她一进大门就拼命招手:“这里……”
柳云龙演的那些电视剧接头的时候估计也这样:“请问,暗号是……”
“Y老师!”
“同志,我姓邱,你叫我邱记者就行,您贵姓?”
“免贵姓钱,缺钱的钱。”
得!罗宋汤和炸猪排估计都我买单了。
然后就开始吃,主要是吃,偶尔搭两句,整个相亲的主要矛盾是,邱记者条件很差,长得又矬,又穷,然后还没看上对方的长相,男人啊,活一万岁都没人真心相信心灵美;女方条件也算不上好,长得纯朴不说了,对我的收入、分房啥的打听得仔仔细细。
当中还问:“你多高啊?”
我说:“一七五。”
钱姑娘说:“瞎七搭八,一六八最多了。”
我默默地喝着罗宋汤惭愧地说:“我有一六八真心天打雷劈。”
一顿饭吃了三刻钟,情况已经很清楚,双方都没瞧上眼,而且双方都承认自己是癞蛤蟆(钱姑娘先提出这个观点的),但是都想吃天鹅肉,急起来唐僧肉都想吃。
钱姑娘说:“我就喜欢童安格那样的,风度翩翩,又有创作才能,钱肯定也不少赚。”
我说:“那是,我跟童安格差距是有点悬殊,不过他唱歌嗲叽叽的。”
钱姑娘说:“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说我就喜欢林青霞那样的,长得又好、身材又好、皮肤又好。
钱姑娘说,口水擦一下。
我说:“你平时有点啥娱乐?”
钱姑娘说:“我不读书,骗你是小狗。我就平时听听电台的流行歌曲,还有短波里的台湾香港流行歌。”
我说总算找到一个他妈的共同爱好,不容易。
我买完单我们就告别了,临走,钱姑娘在纸上写了个座机号码给我,说是她家的电话。
“谢谢你请客。你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打电话。”
我说夏夏侬,咱生意不成仁义在。

上海人发音要叫上海宁。
我在上海生活了三十七年,有人说上海宁排外,觉得还好,准确地说是至少不排素质高的。
说其他地方的人偶有排上海宁的小情绪,倒是略有感知。
上海女人也挺好,怎么个好法,会打扮、讲情调、会过日子,这些都还不算核心价值。
有个叫谷歌的公司,它的口号说:不作恶。上海女人也有个重要特点:有底线。

1992年的时候,小平南巡,发表了重要讲话。
夏天的时候,《文汇报》驻北京站的信息说,邓公可能还要北巡,东北三省,建议总部派记者先去打前站。
我和乐先生被挑选出来,第二天就出发了。
在东北转了两周,跟没头苍蝇似的,没有任何消息。
有一天在沈阳,天气非常热,我从来不知道东北夏天会这么热,旅馆房间里没空调,俩男的光着膀子穿条短裤挤在一个房间里,互相嫌弃。
乐先生也是收音机发烧友,百无聊赖的时候,他在短波里搜到一个台湾的信号,叫做“中广流行网”。
一个台湾的女生DJ说:现在我们向各位听众介绍女歌手孟庭苇的新专辑,主打歌的名字叫《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请欣赏。
那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清凉的歌,直接浇灭了沈阳35度高温。

2016年初的时候,我还在体制内的老单位。
有一天去北京参加一个什么论坛,一上飞机坐下来,就觉得旁边一个中年妇女老打量我。
飞机刚进入平飞,安静了一点点,一个遥远的声音从右耳飘过来:
“还是喜欢林青霞?”
晕晕乎乎中脑子里闪过至少30秒的画面,我才定格在德大西餐馆。
“喔哟,童安格夫人!”
前后两排对这两句对话回应了一点轻微的骚动。
“我姓啥还记得不?”
“你缺钱呀,还能姓啥?我姓啥你记得不?”
“呵呵,我订了东方早报的。”

我们一起出机场的时候,一个男的戴着白手套在出口等他口中的钱总。
钱总说:“侬怎么走?”
我说去叫车。住在国贸。
钱总说我送你吧,介意不?
我说,介意……个屁。
司机明显训练过的,上车帮我挡着头,经介绍后一口一个邱总咱出发了,邱总水和咖啡都有,邱总温度如何?
邱总说:“你就别邱总了,咱听听钱总聊聊她怎么从缺钱变成不缺钱的。”
司机说:“您看哎呀我就是改不了嘴碎的毛病,钱总都批评我好几回了。”
钱总打个哈欠,把飞机上看的一本书放进她的爱马仕包里。
我说高铁上好多假的爱马仕,800块一个那种。
钱总说:“姓邱的,你毛病也是同一个,嘴碎。”

一路无语,两个男的都怕挨钱总骂。
我先到了,钱总跟下来,说去喝杯咖啡吧,都二十四年了我的天哪。
钱总说她有两个二十年,结婚二十年,下海经商二十年,生意做得挺成功,女儿去年上了大学,按说一切都挺好的。
唯一遗憾的是,比她大十岁的老公2006年的时候,查出患有心脏病,还动了二尖瓣手术,但是手术后的效果比较差。
严重点说,感觉整个人都废了。体重从160斤降到了100斤,像一个纸片人,稍微一动就喘得直不起腰。
2006年的时候,老公对她说,你才38岁,还有大把的人生要过,我勿要再拖累侬了。
她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2009年的时候,她老公又进了ICU,所有的人都在想,也许,老公终于解脱了,钱女士,也终于解脱了。
但是,奇迹一直发生,老公又一次挺了过来。
只是,仍然在一种极端虚弱的状态。
她说:唉,哪有完美的人生,完美的都是假的。
我喝了两杯咖啡,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说:1992年的时候,我们看重的东西,现在看来,不值钱啊,但是,不经历这些,24岁的年轻人又怎么可能悟得到呢?
钱总走的时候,把包里的书拿出来,说很好看,她看完了,送给我,说她四十岁后改读书了。

这本书叫《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是普利策奖的得奖作品。
什么样的好故事才能配得上这么好的一个书名呢?
叫玛丽洛尔的法国盲少女和叫维尔纳的德国少年有一个共同的秘密,通过短波收听一个法国教授讲述科学知识,讲述“一切美好和真实的东西”,在希特勒纳粹时期,私下收听秘密电台是死罪。
玛丽洛尔在二战后期接手了教授的电台,用于向盟军传递法国海岸线的情报。德国少年维尔纳作为技术天才被纳粹征召入伍,负责搜寻这部电台。
最后的结局,当然是维尔纳为了保护“美好和真实的东西”而倒戈,击毙了他的上级并向盟军投降。
但是战争的疯狂完全摧垮了尚未成年的维尔纳的身体和灵魂,他已经弱得像个纸片人,并在一次漫无目标的奔跑中踩中地雷变为尘土喷涌而去。

我加了钱总的微信后聊了一回天。
她说:“很多人都认为这本书的结局很不合理。最好的结尾应该是维尔纳爱上了盲女玛丽洛尔,在战争结束后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她说:“我可能心理有了问题,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是最好的结局。或者说,这是唯一的结局。”

2018年的一天,她发了一个朋友圈,大约是毫不避讳说自己已经50岁了,人生跑过了半场。
庆祝的方式是陪着她老公到小区里转了半个小时,阳光很好,老公的身体有非常明显的恢复。
“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接下来,把工作交给年轻人,带着老公到处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2023年,美国流媒体巨头Netflix将《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制作成4集网剧。
这是我在这一年看到的年度最佳,震撼程度超过了其他所有影视作品。
看完之后我突然想起来给钱总发一个微信:
“嗨,奈飞拍了那本书,你知道吗?他们没有让维尔纳死,还让他和玛丽洛尔深情拥吻。真是顺应民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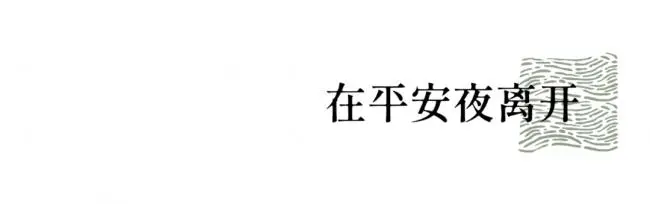
中午的时候,钱总打了个语音电话给我。
她说:“去年底,那一拨,我老公也未能幸免,本来就有基础病,在家里捱了两天,最后还是决定送医院,在医院只待了一天就走了。”
她说,在家里那两天,老公一直发烧,他在手机上看到很多东西,然后,他似乎已经确信自己过不了这一关了。
那两天,就两个人在家,孩子在国外读研,家里阿姨也请假处理自己家里的事了。
两个人聊了很多很多话,觉得,想把这一生要说的话一字不落的说完。
其中有一个细节,她说,很私密,但也很释怀。
老公对她说:记不记得2007年的时候,他和她开玩笑,说你个公司董事长天天也不出去应酬,生意能做好吗?
她说:记得。
老公说:我的意思就是,我已经从心理到生理上都是一个废人了,我已经耽误你太多了,其实,你自己要改变任何生活的方式,我都毫无怨言,甚至,那么真诚地祝福和感动。
她说:我第一次就听懂了。所以,除了必须的出差,一年两三天吧,其他时间,我是朝九晚五,永远回家吃饭,你知道为什么吗?除了我对你必须尽到的责任,付出的爱,我还有一个很自私的想法,我要让那些阴阳怪气的人、那些见不得别人好的人、“钱董事长也有今天”的人,都得知道,陪着你,我就是幸福的。
当然,最后的最后,我发现,这个想法不自私也不怪异,或者说,这就是人的生活,最简单的生活,正常人的生活,当然,也是宁静和幸福的生活……
她跟老公说,我这半辈子要说有个啥成就的话,四个字:没有放弃。
老公在平安夜离开,一脸微笑,最后时刻说:
“侬一定要活得幸福,活得快乐,否则,对不起我们受的那么多的苦。”

“秋天的小提琴,
那长长的呜咽,
用单调的忧郁,
刺伤我心。”
玛丽洛尔在向盟军发送情报的时候,收听到了BBC广播的重要信息,就是这首魏尔伦的《秋歌》,它告诉所有的抵抗组织,盟军将在D-day于诺曼底登陆。
很多年前,我第一次读《秋歌》的时候,还是在东方早报的初创时期,所有的一切都生机勃勃,我还把它用于东方早报的征订广告。
很多年以后,再次听到魏尔伦美好的诗句,关注的是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当然,无论如何,还有光,以及,善良和爱,也许它已经不那么耀眼、光芒万丈,但是,它还在,平淡无奇、抚慰人心。

冬天的时候,我们约在上海延平路的小咖啡馆喝咖啡。
钱女士说:“忙活了一年,企业的销售倒有增长,很感谢你曾经发给我看的那段扎克伯格接受采访的视频,其中一句很有共鸣:乐观者容易成功,悲观者往往是对的。”
我说:“意思差不多就是正确地失败,盲目地胜利,也不是没道理。”
钱女士说:“女儿张罗着给我介绍老伴,让我重新开始,对方条件还不错,比我还小两岁,人也高高大大的。就是我这岁数再弄这么一出,也不知道妥不妥?”
邱总说:“卧槽又相上亲了!”
钱女士说:“人家对方还没给回音呢。我这条件也实在一般,55岁的丑老太婆,该不会是看上我的钱吧?”
邱总说:“网上说的,自信点,把‘该不会’仨字儿拿掉。”
啪!咖啡杯毫无意外地敲在桌上。
“姓邱的,你是一嘴的烤瓷牙也吐不出颗象牙哈!服务员,买单,让这个又穷又酸的戆男人买单。”
愤怒的高跟鞋在延平路的寒风中叮叮咚咚敲了十几米,想了想又折回来:
“侬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不容易,需要帮忙就开口哈……”
邱兵重庆巴南人,李植芳老师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