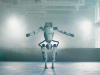去年夏天,耶鲁大学(Yale)研究者发表了一项研究:对于具有同等资历的年轻男性和女性科学家,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学者都更倾向于选择男性科学家。面对着成就相同的假想申请者的简历材料,六大研究机构的教授明显更愿意为男性申请者提供工作。即便他们愿意招收那名女性,提供给她的年薪也平均比提供给男性的低4000美元。更有意思的是,女性学者与其男性同僚偏见一致。
这项新研究为女性在科学界长久以来一直受到的偏见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美国,仅仅五分之一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授予女性,而其中只有一半是美国人。全美所有的物理教授中,女性仅占14%。黑人与拉丁裔就更少了。基本上一年里,只有13名非裔和20名拉丁裔美国人——男女都包括——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这其实一点不难理解:很多少数人种上高中时就在科学类学科上远远落后,并且,他们在接受教育的每个阶段所受到的偏见也早有广泛记录。但是,在就业前景、个人声誉、智力刺激和收入等方面形势一片大好的STEM领域里(STEM即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到底是什么让女性从业者如此之少呢?
1978年,我毕业于耶鲁大学物理学专业。作为耶鲁头两个取得物理学学士学位的女生之一,这个问题深深困扰着我。我在一所乡下的公立学校上中学,在那里,一些物理和微积分的尖子课是不允许我上的。因为校长这么说:“女孩永远都不会去搞科学和数学的。”既愤懑又无聊,我开始阅读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学习资料,还拿起书本自学微积分。刚进耶鲁时,我远没有准备好。和我一起上物理学绪论的男生在高中都接受过严格得多的数学和科学的训练。教授快速地讲述课程资料,男生们打着哈欠,而我却越来越焦虑自己懂的如此至少。我是整个教室里唯一的女生,我一直在斗争到底要不要举手问问题、让自己遭到嘲笑——结果就是我更加听不懂老师讲的东西,远远落在其他人后面。
而最后,我以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会会员的最高荣誉毕业,在系里连续三个学期的量子力学考试及引力物理学这门研究生课程中出类拔萃,同时我还自学了耶鲁大学大型计算机程序。但是我没有选择物理作为我的职业。四年结束时,我早已疲惫于为了赶上其他同学而长时间孤独地埋头苦学、隐藏内心的不安、在男生们合作解决作业题时独自奋斗;早已厌倦了为了让自己被看作是科学家而穿成一种样子、为了展示女性风采又穿成另一种样子;尽管也有我想交往的男生没被我的专业吓跑,但大多数确实被吓跑了。
不过,我没有投身于物理学的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不曾有一位教授,连指导我毕业设计的导师都没有,鼓励我读研究生。显然这是认为我天资不够,无法在物理学领域取得成功。我把毕业论文的初稿放在导师办公室门口,羞涩地偷偷跑掉。没能实现梦想的伤痛让我把教科书、实验报告和作业题统统锁在了我父亲的军用提箱里,永远与物理和数学分道扬镳。
直到2005年,当哈佛(Harvard)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场午餐时间的演讲里问到“为什么很多女性都不在自然科学领域争取终身教授职位”时,我才觉得必须要打开那个箱子了。我自青少年时期就认识萨默斯,他曾是我高中辩论队的裁判,给我留下了“尊重聪慧女性”的印象。除了其他相关理由,他还提出了一种解释:男性与女性在科学与数学的最高端领域有天赋差异。我本以为他提这个问题是真心想知道答案,结果听到他推测“女性教授少可能是因为男女生物学上的差距”,我心中一惊。然而,当我读到针对他这个观点的激烈评论时,我意识到,即便是我自己,也不能确定为什么那么多女性在获得物理和数学高等学位之前就放弃了。我决定联系我以前的同学和教授,重审女性在STEM领域的表现,回到耶鲁,看看我毕业后事情是否有任何改变。我想知道我为什么背离了自己的梦想,为什么如此多的女性仍在背离她们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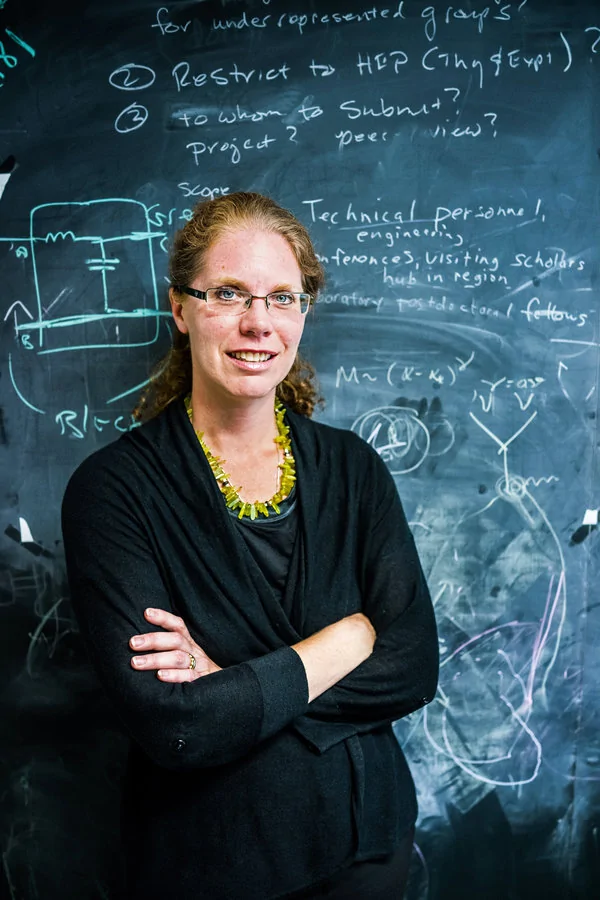
邦妮·弗莱明是耶稣大学物理系第二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教授。 Joseph Ow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当然,从很多方面来看,大环境对想学习科学和数学的女性已变得越来越友好。当年我在纽约州北部上的高中现已无需女生自学微积分,物理学也由一位有魅力的年轻女教师讲授。2010年的秋天,我第一次回到耶鲁,每个人都在夸耀物理学和物理相关专业的本科生中有30%到40%都是女生。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女孩子所在系的系主任由杰出的女天体物理学家梅格·厄里(Meg Urry)担任。她在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空间研究中心读了博士后,还曾为哈勃空间望远镜工作过,2001年被耶鲁大学聘请为终身教授。(那时,整个系一个女教授都没有。)
近几年,厄里一直致力于用实实在在的数据和自己的个人经历改变同事中“为什么从事科学的女性那么少”的观念。她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发表文章回击萨默斯的观点,她表示自己逐渐意识到女性相继离开专业岗位并非她们天赋不够,而是被长期的“不受重视、心情不爽、通往成功的道路遍布路障”给打击的。
尽管厄里在她的专栏里坦率写到,年轻时她曾把自己在获聘与升职上屡遭失败看作是自己不够优秀的证据,但现在任何一个见过她的人都难以想象她也会不自信。她总挂着一种揶揄般的微笑、眼睛闪闪发亮、有着不留情面的幽默感。不止一个——足足有五个人曾向我描述,厄里是校园里最忙的女性。
我们见面之前,厄里认为她系里的女生也会感受到厄里和我过去经过的挣扎,但系里的保障系统足以保护她们不产生我们那种自我怀疑。比如,在物理系第二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教授邦妮·弗莱明(Bonnie Fleming)的指导下,学生们为耶鲁物理学本科女生办起了不定期会议。除此之外,厄里觉得,既然有这么多女生在耶鲁学习物理,而且又有这么多名列前茅,教授不可能没发觉她们的能力不输男性。我提到下午有个茶会,届时我将采访一些对科学与性别感兴趣的女生,厄里说她会尽量参加。
主持茶会的是朱迪思·克劳斯(Judith Krauss)教授(她是护理学院的前院长,现在是西利曼学院[Silliman College]院长,我本科时就住在西利曼),她提醒我说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学生感兴趣参加的。而当80位年轻女性(和3位好奇的男性)挤进屋里时,克劳斯和我都震惊了。厄里急匆匆赶到,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座位。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分享自己的故事。一位女生在高中修大学物理时,惊慌失措地发现班里一共就3个女孩子;更糟的是,另外两位后来退课了。另一个女生说她从一开始就是唯一一个修大学物理的女生。同学无情地嘲笑她:“你是女孩子,女孩子学不了物理。”她希望老师能终止这种嘲弄,可他没有。
另一名女生插进来说,她的老师才是嘲笑者中最过分的。一次物理课上,老师宣布:男生的成绩按“男生正态分布”给,女生按“女生正态分布”给。当问及理由,老师解释说他无法合理地期望一个女生能在物理上与男生按统一标准竞争。
听众中,对大家讨论的事情不明就里的要么是高中在女校读的,要么是生长在国外的。(与我在茶会及其他场合交谈过的女同性恋科学家对于课堂上和实验室的性别观念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其中许多困扰都与普通女性一样。)有一名学生——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说她一到校就注册了很多高级课程,选最难的数学课时一点都没犹豫。可当她发现自己是班里唯一的女生,第一堂课就跟不上时,她动摇了。她问教授:“我该留下么?”“如果你没有信心留下”——她学着他讽刺的腔调——“那你就别修这课了”。
茶会结束后,十几名女生留下来继续讨论。“我们组的男生从不认真对待我说的话,”一个天体物理专业的女生抱怨说,“我不想表现得争强好胜,必须这样么?我生来不是这种人。读研究生就一定要好斗吗?以后一辈子都要这样?”另一个说她不喜欢和姐姐一起去俱乐部时被介绍说是天体物理专业的。“我在桌下踢她。我讨厌酒吧或派对里的人知道我读物理专业。他们知道的那一瞬间,男孩子都扭头走了。”还有一名女生提起,就算是耶鲁的男生也不愿意跟学物理的女生约会,她很担心自己在4年里将一次约会都没有。
学生离开后,我问厄里她是否也跟我一样吃惊。“比你更吃惊,”她说——毕竟,她是这些女生中大多数人的系主任。
此后两年里,我又从密歇根、纽约州北部和康涅狄格州的年轻女性口中听到类似的故事。我真失望,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的文化和心理上的影响因素不仅延续至当今社会——一个告诉女性什么都不能阻止她们在一切领域成功的社会——似乎还更甚于过去。细究的话,“做传统温柔女性”的压力倒是比我年轻时更大了。
要想找到美国人对科学、特别是对从事科学的女性的刻板印象,你只需看一集广受欢迎的电视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就行了。剧中角色包括一伙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笨拙又可爱的男性物理学家和他们的邻居佩妮(Penny),一个有魅力的金发女郎,来洛杉矶实现她的演员梦。尽管剧里出现了两位女科学家,可是其中一个,伯纳黛特(Bernadette),说话声音尖锐刺耳,足以震碎试管。在她努力取得微生物学博士学位时,并不是在实验室工作——像任何一个真正的博士研究生一样,而是与佩妮一起当服务员。而另一位,由马伊姆·拜力克(Mayim Bialik)出演的艾米(Amy)是名神经生物学家,她与孩子气但聪明绝顶的物理学家谢尔顿(Sheldon)发展出暧昧关系。拜力克本人确实拥有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在生活中也绝不像剧中所饰的人物那般矮胖邋遢。诚然,《生活大爆炸》是个情景喜剧,每个角色都是夸张的。但是,有哪个正常的年轻人愿意踏进充斥着谢尔顿、霍华德(Howard)和拉杰(Raj)这种怪胎的屋子?又有哪个正常的年轻姑娘愿意把自己想象成寒酸、社交低能的艾米,而非时髦、愉快、数学盲加科学盲的佩妮?
虽然美国人想当然地把科学家和土包子划等号,但在其他文化中,拥有数学天赋通常被看做是一个人反应快、有创意的证明。2008年,美国数学学会(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调查了一系列旨在发掘优秀人才的国际著名数学大赛参赛情况。数据显示:美国选手几乎全是移民来的孩子,且很少有女选手。例如,1959年到2008年,保加利亚送出21名女生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而美国自1974年第一次参加该竞赛起至2008年,一共才送出3名女生;1998年以前居然一个女性都没有。这项调查的作者称,美国本土学生无论男女坚决不参加数学俱乐部和数学竞赛,因为“只有亚洲人和书呆子”才会自愿去搞数学。“换句话说,美国初中和高中的普遍观点是,喜欢学数学是很土的;这样做会被其他人排挤。”结果,有天赋的——甚至天赋胜于男生的女生,通常都会为了合群而掩盖数学才能。
上述调查结果同样适用于科学类学科。厄里告诉我,在她过去工作过的空间望远镜局里,意大利和法国女性“穿得特别漂亮,是美国人会说露得太多的那种。你能见到法国女人穿着短裙和网袜;这对她们而言太正常了。那些国家的男人似乎能够把人的性别身份与学术身份分开对待。美国男人好像无法把女性既做女人又做科学家来欣赏;只能二选一。”
毋庸置疑的是,在科学和数学领域中,男女地位差别并非基因导致,而是文化驱使。80年代初,一大批美国初中生参加了美国高考(SAT)中的数学考试。那些分数超过700的学生中,男女比例13:1。不过就算在初中就能取得700甚至更高的分数,也并不代表该生在更高的数学领域上拥有真正的创造性和能力。而且这些全都是美国学生。数学界曾对国际比赛中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进行研究,通过分析身处其他文化中的年轻女性表现来分析其天赋。这项研究的结论?在科学领域阶梯最高层鲜有女性,“主要归因于时代、国家和种族群体的可变因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些赏识并培育拥有极高数学天赋女性的国家,其女性科学家的比例要远高于别国。”此外,现在在SAT数学考试中分数超过700的学生里,男女比例仅为3:1了。如果女生如此受制于生理局限,那她们又怎能在短期内稳步提高成绩呢?
小学里,男孩和女孩在数学和科学上的表现旗鼓相当。上高中前,当无论对于男女这些学科都开始变难的时候,差异显现了。尽管从1987年到1997年间,在高中修物理课的女生比例从39%上升到47%,可直到2000年也再没有增加。而且如果你观察大学物理课、而不是高中物理的选课情况;以及大学物理课的成绩、而非出勤率,你会发现形势更加严峻。大学微积分选课情况稍好,计算机学科简直惨不忍睹。可能男生比女生更喜欢物理和计算机。但另一个同样可能的解释是:男生总是被鼓励要在困难的、不受欢迎的学科上坚持下去;而女生,不管她多聪明,退掉门物理课或不认真对待大学物理考试都不会受到太多来自家长、老师和辅导员的批评。
人们早就了解,文化信号能够影响一个学生在考试中的表现。在那份多次被引用的1999年的研究中,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一些数学背景和能力都差不多的学生被分为两组。第一组学生被告知男性比女性在数学测试中表现更出色;而第二组被担保说不管他们之前听到过什么,男女其实没有差别。两组学生都参加了同一项数学测验,第一组男生比女生高出20多分,而第二组男生只比女生高2分。
甚至有可能,数学和科学的天赋无法用考试成绩鉴别。遍布高等工程、计算机、数学和物理学领域的美国白人男性,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在SAT数学考试中取得650分以上的成绩,而大于三分之一的人低于550分。在中等层次领域中,努力、决心与鼓励似乎和单纯的天赋同样重要。甚至在最高层次领域里,考试成绩也貌似没什么关系。大家都知道,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的智商才125,并不很出挑。
女性是否走上科学的征途,最强有力的影响因素也许是其他人是否鼓励她。我在耶鲁的第一年,物理期中考试得了32分,父母直催我换专业。他们所希望的就是我能养活自己直到结婚,然后让丈夫养活。学物理,不像是能达到这个目标。
我走上Science Hill去找授课教授迈克尔·泽勒(Michael Zeller)签退课表。我乘电梯来到泽勒教授那层,穿过墙壁上排列着清一色男教授照片、贴着我根本看不懂题目的讲座通知的走廊。我敲开教授的门,费了好大劲才结结巴巴地告诉他我期中考了32分,需要他帮我签退课表。
“为什么?”他问。他自己两门物理课都得了D,还不是期中考,而是整个课程。这故事听着很像一个和蔼的教授为了让他最笨的学生感觉自己不那么傻而编出来的。他的情况是,那两个D显然是发挥失常。而我的情况是,32分就意味着我根本学不了物理。
“就在你自己那道游,”他说。他看出了我的困惑,告诉我说他曾是斯坦福(Stanford)游泳队一员。他的动作和别人一样棒,可总是游不过别人。“泽勒,”教练说,“你的问题是老看其他人游得怎么样。就看你自己那条泳道,游出你最快速度,你就能赢。”
我估摸着他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不会给我签退课表。
“你能行的,”他说,“坚持下去。”
我继续上那门课。一周一周过去,我努力解决作业题,直到它们看起来不是那么高深莫测。现在,我越仔细重温我4英寸厚的大一物理教程,就会发现越多的用彗星一样的感叹号标注的公式和用爆炸新星一样的粉红色星号划出的理论精髓。书中的注释将我带回曾经的年代:我坐在拥挤的宿舍里,忽然明白了某些支配物体相互作用的原理——不管是地球上或是几光年以外,我惊讶于如此广大复杂的体系竟能浓缩成我在书中划出的公式。还有什么能比掌握了一种全新看世界的方法、掌握了比现实还真的现实更加激动人心的呢?
学期结束我得了B;第二个学期我得了A。在大四开始前,我已跻身班级前列,还拥有最多的科研经验。然而,没有一个教授问我想不想上研究生。当我羞涩地向泽勒教授提起我的梦想是进普林斯顿(Princeton)做研究最后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时,他摇摇头说,你想去普林斯顿,那就把你的自负装进兜里。因为那里的男生特别聪明、特别有竞争力,你的自负会被碾碎的。他的话让我觉得自己不够聪明、竞争力不足,没资格申请。
指导我做毕业设计的数学教授也没有敦促我去读博士学位。我9个月来没有参加过派对、经常晚饭不吃、睡眠不足,就为弄明白为什么波——声音、光还有其他的波——在一切奇数维空间里是以球面形式传播,就像气球的球皮;而在一切偶数维空间中就像一个实心的保龄球那样传播。当我最终找到答案时,我满怀胜利之情敲开了导师的门。可我记得他一句也没夸我。我迫切地想问问,是不是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证明我的能力足够强,以后能成为理论物理学家。但我知道如果我有必要问这个问题的话,我就不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