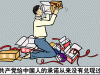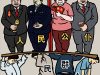民国时的土地自由买卖,就是自由资本主义了。善于耕种与经营的农民,转变为地主。同城市善于工商者转变为老板同类。而对于民国继承皇权不下县的乡村自治,地主士绅既是义务的社会秩序维护者,且是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传承者。他们家门与庭院内常挂的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他们乃农耕社会的先进代表。乡村由痞子取代士绅,阿Q掌了权力,颠倒了良莠、是非与善恶。这些痞子流氓夺权后到公社化时,不仅党政财文大权独揽,土地收益分配权也独占,他们就转化为土地的主人。再经这些年土地市场买卖,他们又是土地的经管者,“代表农民集体”再成土地僭主,而且成为土地红利的垄断者。今天,上层,叫红二代,下层,是阿Q二代,他们最喜欢也最习惯老毛无法无天耍任性,当然也厌恶老毛厌恶的温良恭俭让。新生的土地占有主,乃拥有各级权力者,在房地产土地买卖中,他们按权力大小分享土地红利。他们卖土地70年所有权,70年后,收回重新出卖,把土地当摇钱树,摇出吃土地财政各级新地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地主。他们灭了文明的地主,自已摇身为不挂地主名的大地主。赤色土地革命的荒谬,打着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口号,却把当权者变为富豪与土豪。
洛克早有名言告诫:“公权,不可私有,私产,不可公有。”这是政治经济学的铁律,他们不正是违反此铁律造成历史及今日之荒诞吗?
当这公有实是官有党有,制度性贪腐哪能除灭。他们最初由枪杆子劫夺,掌权后以政权劫夺。而且钻入世界市场,发现了知识产权的劫夺致富最快,人家说打贸易战,其实,是打的防贼战哩。不禁想到资中筠先生为教育弊病,曾哀叹中国人种要退化。难道农村的痞子运动,城市的红卫兵运动再加复起的义和团运动,不更早就在促使中国人种的邪化、痞化与退化吗?
留美农学博士董时进上书劝阻土改遭拒
1949年12月,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曾上书毛泽东,劝阻土地改革。董的观点简单明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当时的一些文件和讲话,认为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董认为是不正确的。他指出,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5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5至10亩,13%农户拥有10至15亩,1000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数据,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了董的观点。董对土地由擅长耕种土地的地主富农转到不擅耕种者,而且细粹化经营,必然減产。亊实证明:中国粮食产量经土改加公社化折腾,直到攺革开放再分田到户,1984年才恢复到抗日前1937年的产量。从前有天灾,还有地主士绅搭粥棚施粥饥饿者,可逃荒活命。共产专制不准逃荒,河南信阳地区便饿死上百万。今日青年不理解能饿死人,杨继绳的《墓碑》便是证词。
翻开历史,触目惊心,哪是一句“不准说历史错误”可制止,不说,便永在重复与固化历史错误。
这种农学家从经济与社会学早分析出土攺特别是暴力土改的弊病。从占有土地的农村结构看,不是什么贫富悬殊的尖锐阶级矛盾,而今天凭权力成为暴发户。清朝也只暴露一个和珅,而共产集权制造的和珅,秦城监獄关的只是总数的零头。多少和珅式的赃款,不在外国银行,也已变外资回来投资了呢。
地主污名化的几个标签
前靣举出真正代表地主的人物是曾国藩、谭嗣同等,即说明不能用黄世仁、周扒皮等几个虚构人物来污蔑地主。甚至格丘山先生著文嘲讽此新时代不如黄世仁等那旧时代,他说:“这是个武松给西门庆看家护院的时代,这是个关羽过五关贿六将的时代,这是个包拯把秦香莲送进精神病院的时代,这是个喜儿赖着要嫁黄世仁的时代……”,“数卑鄙人物还看今朝”。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用戏剧与小说虚构丑恶化地主,笔者读到作家丁抒写他亲见高玉宝不同意那么写地主的一段话,应立此存照。
丁抒说当年他进人民大学时,高玉宝也在补习文化,分在该校预科班。署他名字的小说《半夜鸡叫》正由《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荒草〔实名郭永江,四川资阳人〕创作完成。稿子交高玉宝看后,他说:“这么写,叫我怎么做人?”也就是这么违背真实过度汚蔑地主,使他无面目返乡见乡亲。而当地人说周扒皮的原型地主,只是很抠,有些节约,却并不苛待长工,也不可能半夜弄长工下地。漆黑的夜,锄断了禾苗,得不偿失哟!丁抒用他亲见讲真实的高玉宝,去反对弄假的代笔者。
给刘文彩泥塑收租院的故亊,也是虚构。对于关水牢的著名人物冷月英,笔者当年采访过住她家相邻小学去体验生活的作曲家美术家,还有西南人艺院长栗荗章。他们去刘文采庄园见到的所谓水牢,乃四面透风藏鸦片的儲藏室。今天,那里只剩刘文彩捐几百亩良田办的中学,还是川西名校。
地主中,有没有坏人?当然也有。不过巴金写的《家》里的冯乐山那种坏,也并非普遍。在那做官也讲道德文章的社会,地主要是不讲仁义与信用,也难处世。我听地主家子弟说他偷吃了一点腊肉,挨了打,说那是栽秧打谷留来待长工的。彭县友人廖鴻昌为退休地质工程师,他说他家劳力充足,租地50亩耕种,他随父去向地主拜年,他不仅首次吃到海參席,而且租佃是主客关系,父亲请坐上位。走时,主人还给他一块大洋的红包,这钱,足够他上中学一学期伙食费。中共将农民与地主说成你死我活的关系,只不过为其阶级斗争理论服务。
关于地主的沉冤,今年九月有宋永毅教授与夏明教授在纽约城巿大学开了一次世界性的学术讨论。受此启发,这是我第三次为冤沉海底的地主鸣冤。第一次鸣在陈奎德先生主持的《纵览中国》上,再次是为作家方方对川东地主在土改中尽是软埋鳴冤受攻击去作证。看来,地主的奇冤,还需从人权建设与人性恢复的高度,理清这笔历史旧账。前苏聨政治死难者纪念碑的揭幕,不是为中国历史上的沉冤招雪树了榜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