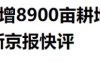在轰轰烈烈大跃进的1958年夏季,我们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在中学校长“农村具有广阔天地、农业大有发展前途”的号召下,高高兴兴的考入了××农学院。那时在职业选择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是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就行了。在报考志愿的选择上全由学校领导安排,如果过于看重选择志愿,惧怕学校领导给扣上思想落后的政治帽子,到那时什么大学也考不上了。当时同学们也认为挑剔志愿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只能是盲目服从,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一生交给党安排。九月一日,我们这些大部分来自农村不足二十岁的小青年,背上极简单的行囊,踏入了大学校门。
一、1958学年
在最高领袖“高等农林院校办在城里活见鬼”一言九鼎的鬼使神差下,将建校已50余年,结构完整的高等农业教学体系打破,学校从济南城里迁到泰安乡下。人还是那些人,天还是那块天,但“鬼”却是不见了。前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望一时头脑发热的最高领袖,不要轻易否定我们先辈的作为。
将泰安的山东省部队转业干部速成中学、泰安农校、泰安牧校、泰安二中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迁移,实行了至上而下全面的瞎折腾。我们踏进学校大门的第二天,即投入了迁校搬家工作。将学校课桌课椅、实验设备、图书期刊、生活用具等,肩扛人抬,运至济南火车站,火车运到泰安后,我们再搬运到学校。全校学生、教职员工、老幼家属全面投入战斗,形成了庞大的运输团队。白天黑夜历时一个半月,精疲力竭。上述几个泰安的学校当然也不会例外。最糟糕的是遇到连雨天,搬迁物资在风吹雨淋下,与老天爷一样在那里哭泣落泪,叹息它们的命运!这正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了。在“史无前例”中的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学院等就更加悲惨。
迁校后还没来得及作任何安顿,我们即马不停蹄的又投入到“全民动手”完成全国1070万吨大炼钢铁的战斗行列。学校整个操场竖起了一座座土高炉,砌起了一排排炼焦窑,狼烟四起,遮天盖地,马达昼夜轰鸣。我们班的40位同学一半去运铁矿石(实际上是两人抬一筐回来。是不是铁矿石,含铁量多少,谁也说不清),一半炼焦炭。运铁矿石的同学2~3天才能返回,正如有的同学私下说,走在路上就睡着了。炼焦炭的同学12小时两班倒。同学们倒班后灰头土脸的钻进宿舍就睡觉,既不洗脸,也不洗手,更谈不上洗澡了。有的同学连饭也不吃,只顾睡大觉。
一日,夜间12点钟,全宿舍区沸腾起来,大呼小叫,震耳欲聋,睡梦中的全体同学被惊醒,说我们学校炼出了第一炉铁水,全校教职员工,全体家属去给市委报喜。月光下全校红旗招展,高音喇叭歌声嘹亮,全体拥向市委。到了市委大门口,还得排队等候,因为那时放各种“卫星”的单位太多了,市委也应接不暇。一直激动到天亮,我们才返回学校。吃过早饭,同学们摩拳擦掌,又继续“大炼”了,但昏昏欲睡的同学们从内心深处却不愿再炼出第二炉铁水了。然而却没有一位同学讲怪话,发牢骚,最大的本事只能是默不作声,黯然无语。因为同学们在中学亲历了1957年的整团,目睹了如火如荼反右派的战斗洗礼,一旦有点“风吹草动”,轻者被拔白旗(实际上就是批斗),重者被扣上“资产阶级小右派”的帽子,列为专政对象,那就更惨了。我们一直干到12月上旬,已是天寒地冻,屋里屋外同样结冰,冻得难忍。最后的结果是炼了一堆连炼钢厂都不要的废铁渣,消耗了大量煤炭,投入的人力、财力无法计算,实在是得不偿失,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偃旗息鼓。前无古人的全民大炼钢铁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却成了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接踵而来学校厉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不懂,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略知一二,就是天天拼体力劳动呗!这正是领导怕我们刚刚踏进学校大门的青年学生会变成“知识越多越反动”,“书读得越多越愚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刚刚踏进大学校门,连一天课还未上,便戴上了“知识分子”这顶大帽子,真是一大幸事。于是我们背着小铺盖卷,步行下放到距学校30公里之外的山区劳动锻炼。任务是在大山里栽苹果树。每天均进行每人完成劳动量统计、质量检查、思想总结、开展红旗竞赛……热火朝天。那时我们是小孩子,年幼无知,思想十分天真无邪,用一种极幼稚的心态,热爱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我们每天只管拼命劳动。我一天曾挖过1米见方的7个苹果穴,折合一天要挖刨1万6千公斤土石方,每天还要借着月光夜战到晚上10点钟,将白天挖好的树穴栽上苹果树,浇足底水。过着披星戴月的生活,这话一点也不过分。
在这样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我们每天吃的又是什么呢?一天三顿蹲在地上吃煮地瓜,喝的是面粉汤水,菜是腥臊难咽的萝卜咸菜。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睡的是铺着一张薄席的土地。我们是在乘大跃进的浩荡东风前进!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其中有来自城市的女同学,她们从来未吃过这样的苦,干过这种强体力劳动活。一天下午在山上刨树穴时,一位来自城市的女同学对她的同伴说肚子疼,医生给她吃了点药,队长让她回宿舍休息。我们收工回来后,她疼痛得更加剧烈,队长请示大队部后,让我们几个男同学用小木板抬她去距城30公里的医院,我们连夜兼程,连一分钟也不忍心怠慢。初冬季节,到达县城医院后,我们的衣服被汗水全部湿透。刚到医院她就停止了呼吸。
1959年春天,我们在山上植树时,山上的巨石滚落下来,将下面植树的同学砸死。它给人们留下太多的思考,他(她)们的死谁之过,连苍天也难以回答。由于说不明的原因,这两位同学变成了人间无形的冤鬼,溘然长逝,成了“活见鬼”的殉葬品。他们的家人没有得到1分钱的抚恤金。来世一生,仅带走了一口薄板小棺材。回想起来,实在使人无限的悲痛、伤感、惋惜、崇敬。有的同学在背后发牢骚说,我们拿着钱是来上学的,怎么让我们天天劳动啊!我们常想,无论国家怎么发展都不能放弃读书,任何时代都需要有知识的人。靠知识改变命运,在那个年代,虽然是幻想说梦,但有梦总比绝望强。在反右倾,鼓干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上山劳动没有几点钟之说,天天是天一亮我们就上山刨树穴,刚吃完早饭就盼望着中午饭。中午饭送到山上,我们用沾满黄泥的双手,接过4两重的地瓜面窝窝头和一碗菜汤,狼吞虎咽,几分钟就吃完了,然后躺在山坡上闭目养神,连闲聊的力气也没有了。傍晚,夕阳西下后,我们才摸黑下山。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荣辱观。我们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知识分子”,不但要改造思想,而且要在外表上也应像贫下中农。我们来自农村的这些穷孩子,家长靠人民公社那块土地,连肚子也很难填饱。初冬已到,每天早晨穿着破旧小棉袄,腰中扎着小麻绳,头上裹着围巾,上山劳动,从内容到形式完全像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那时谁最像贫下中农的穷样,谁走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谁就最光荣。
1959年新年到了,除夕下午放假半天,我们几个同学到十余里的公社驻地理发,我顺便从公社百货门市部买了半斤山东白干酒,其他同学也有买酒的,也有买萝卜咸菜的带回驻地。夜幕降临后,我们同住在一屋的八位同学围坐在透风撒气的农村草房中的土地上,用酒瓶你一口我一口推杯换盏,就着萝卜咸菜,有说有笑,大喊大闹,十分惬意,似乎今天已进入共产主义,当酒喝到兴头时,一位同学以颓废绝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我至今未能忘怀,他说:“今晚有酒今晚醉,莫管明早喝凉水。”这大概就是同学们节日最快乐的心声吧!我这是平生第一次喝酒。
一天,传下令来,上级领导明天要来检查指导。大队部指令中队部六点钟起床集合迎接领导,中队部恐怕落后,指令小队部五点半起床集合,小队部更怕落后,指令我们学生五点钟起床集合。结果我们在清晨的寒风凛冽中,饿着肚子干等了一个多小时,纯粹是糟蹋人,这就是图虚名招实祸的“大跃进”在青年学生中的一个缩影。我们刚刚踏进大学校门的第一年,就享受到了劳动改造的“待遇”。今天的人们是无法理解1958年代刮起的共产主义狂风!
好不容易熬到“五一”节,学校领导让我们陆续返校。每个同学进行了全面、深刻、不实事求是的思想总结:改造了思想,学到了知识,开阔了眼界,锻炼了身体,做到了“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从“五一”节以后到七月中旬放暑假,我们上了两个月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终于盼来了“网”开一面,有了读书的一席之地。胜利的完成了大学新的一学年。
二、1959学年
暑假开学前夕,同学们都抱着希望,新学年开始了,我们总该按部就班的上课了。开学的第二天,仍然是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常抓不懈。我们成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例外。我们常想,难道这一辈子我们就这样生活下去吗?真可谓长路漫漫,征程无限。对我国的科学事业忧心忡忡,心有余悸,完全失掉了信心。全班去支援农业第一线,抗旱保苗,抗旱保丰收。在农村看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社员干农活的很少,间或有一俩人干活,也是出工不出力。社员每天三次去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的公共食堂领取窝窝头,领回来后,就坐在树荫下或门厅乘凉,闲聊,妇女们乘凉纳鞋底。在村庄的残垣断壁上还隐约可见那些蛊惑人心战天斗地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和“超英赶美”等假大空的标语。而田地里的野草足有半人高,这正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我们这些学生只能是一块田地,一块田地的拔草保苗、挑水抗旱。整个生产队的农活我们班全包了。晚上我们也只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聊天,但绝不谈政治,生怕逾越“雷池”半步。在那红色恐怖年代,政治是高压线,一触即亡。“平时开玩笑,运动当材料”,这句政治格言名不虚传。当秋收秋种完成以后,又是一个半月,我们总算返校了。
返校后,一周六天,一天政治学习,一天建校劳动,其余四天,还有些课余劳动,稀稀拉拉松松垮垮的上课。这时正是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学习的最好时机,然而最高领袖于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上他提到麻雀问题时,不无情绪的说:“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因此,围歼麻雀就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在这一旨意下,每天下午全校停课,围歼小麻雀。学校房顶上、庭院里、空地上……布满无数岗哨和花花绿绿的假人,我们同学拿着洗脸盆、搪瓷碗,手中擎着花色彩旗,同学们准时进入阵地,将校园和宿舍区包围起来。阵地密如网,岗哨密如林。校围歼麻雀总指挥部一声令下,敲盆击碗,摇旗呐喊,杀声震天,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小麻雀坠地身亡。经过三天苦战,战果辉煌。麻雀也是小精灵,一部分麻雀被赶到安静的农村,但农村也绝不是一片静土,也不是真空地带。这时,每班3~5人组成一个战斗小分队,进攻农村。每天下午四时,我们准时奔赴距城十余里的农村,掏堵漏网的每一只麻雀,到晚上10点多钟才返校,我们的决心是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又是一周的折腾。从1955年开始,最高领袖的旨意是让小麻雀断子绝孙。但他这一“英明举措”,却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已受到大自然对农林业生产的严厉惩罚。
这期间也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之后,为了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我校同全国的形势一样,全方位掀起了充分发动群众的热潮,从班级、从全系、从全校,检举揭发大大小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弄得人人自危,胆战心惊。学校党委书记在动员大会上信口雌黄的说:检举不检举,揭发不揭发是立场问题,检举揭发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否属实是认识问题。只能是乱打一通,痛快一时。这一部分人整那一部分人,这一英明举措,在全国已揪出55万多名右派分子的基础上,又整肃出了380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实属战果辉煌。那时的建国方略就是一心一意谋整人,揪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越多,革命成绩就越大,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就会越快。
我们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正是需要营养长身体的时期,何况处于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在我们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时,口粮供应每人每月30市斤,完全不够吃。由于我人高马大,身强力壮,脏活、累活班长总是分配给我,我也有质有量的完成。在劳动期间,我曾说过:“让吃饱晚上干活也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同学举报后,我只好低头弯腰认罪,无限上纲的深刻检讨,“狠挖思想根源”,以屈辱之心说一套假话:“我与彭德怀同流合污,遥相呼应,我反对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国家哪有吃不饱饭的人,我有眼无珠,睁着眼睛说瞎话,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否则过不了关。大会、小会批斗一周,将完整的检查材料交给支书。又加上我是贫下中农出身,又加上我是现役军官子弟,根正苗红。几天之后,在全班大全上,支书还表扬了我:检查深刻,认识透彻,有悔改表现,今后要继续努力……我总算被解放了。那时右派分子、坏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高悬在每个同学头上的三把利剑,不知何时就会有一把利剑射在倒霉同学的头上,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更哪有“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班有一同学丢失了银行存折,校保卫处也来人卧底探查。一周以后,拿出匪夷所思的英明决策。破案当然要走群众路线,让每个同学写一张字条检举揭发偷存折的人。这一荒诞无稽,不可思议的“英明决策”宣布后,全班同学鸦雀无声,人人如坐针毡,毛骨悚然,无精打采的低下头沉默思考,惶惶不可终日,人人心事重重。但是谁也不敢提相反意见,不说顺话就很好了,只好低下头默不作声,明哲保身,严缄其口,但求无过,否则,那把利剑就会落到自己头上。经过一番瞎折腾,我班王××同学得票最多,“当选”。因为这一同学平时好多管闲事,从哪个侧面看,他都像“偷斧子的”,百口难辩。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选之后,利剑落在他头上,小会斗,大会批,白天在保安人员的监视下,在宿舍里写检查,写交待,不准去上课。写认罪材料,坦白交待是他每天的“必修课”。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同学们也跟着倒了霉。晚自习不能上,开大批判会。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这位“当选”的同学每晚都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接受批斗,寒冬腊月天吓得满头大汗淋漓,一直折腾了大半个学期,学年期末考试时,他四门功课不及格,只好勒令退学,这把利剑终于见了血,他成了时代的又一牺牲品。(后来存折找到了,确实不是他偷的)。
1959年下学期,我们仍然盼望着按部就班的上课,系统的学知识,系统的学本领。因为学校刚刚搬迁,教学楼还未建起来,只能在大饭厅里上课,冬天冻的非常难受,没有棉衣的同学更是冻得瑟瑟发抖,特别是来自南方的同学,他(她)们没有穿棉衣的习惯,手、脚被严重冻伤,难受,也得受;难忍,也得忍;难耐,也得耐。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女同学,平时上课、上晚自习时怀中揣着热水袋取暖。
学校又布置进行教育改革,将资产阶级的办学模式催垮,由“资产阶级草包教授们”编写的教材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不实用的。停下课来全校同学进行教学改革大讨论,由学生自己编写教材自己学才是实用的。其中讨论到《气象学》,“资产阶级草包教授们”讲的是“空气流动就形成了风”,这谁不知道,这门课程砍掉。东砍、西砍,最后剩不下几门课程。更可笑的是,我们班分得《森林树木学》教材的编写,任课老师只好带领全班同学分赴距学校较近的泰山、徂徕山进行野外树木调查,时间一个月,回校后又将“资产阶级草包教授们”编写的教材转抄过来,最后给这本伪书披红挂彩,锣鼓喧天的给校党委报了喜。天翻地覆,倒行逆施,学生教老师,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三、1960学年
新学年又开始了,但这一学年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开学的第二天就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总可以上课了。但上课不足一周,新的政治任务又来了,继续反右倾,鼓干劲。为了大树特树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威,每人每周必须学习一篇毛主席著作,硬性规定每人必须写一篇不少于1000字的心得体会,同时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上挂下联,向党交心。同学们更作难了,但绝不敢草率从事,因为这是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红色法宝。我们是农学院,又不是政治学院,为什么把学习毛著当成主课?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得不偿失。我们是小孩子,是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心得体会,每天急于找报纸,抄报纸,也不管对号不对号,凑满篇幅为准则。到图书馆借出政治杂志转抄下来,或者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每个星期六下午,各学习小组评议每人写的好坏,其中包括是认真对待还是敷衍了事,字写得工整与否等。每星期一下午将各小组评出的较好的一篇,再在全班同学大会上宣读,再评出全班最好的一篇交到系党总支。它挤掉了学习专业课的大部分时间,每周是这样倒噜,雷打不动。同学们敢怒不敢言,有的同学在上晚自习时,在看专业书的同时也将一本毛主席著作放在课桌上,有人来时,迅速将专业书盖上,惧怕别人给扣上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态度是政治立场问题,哪敢松懈,每天人人提心吊胆,本来就提着的心弦绷得更紧了。
由于我经历了1957年“引蛇出洞”的反右派,看到了许多优秀教师、教学能手被打成右派;又看到1958年拨白旗的事实;又看到1959年痛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血腥战斗,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我处处小心翼翼,不敢说真心话,在小组会上发言谨小慎微,每句话沉思再三,因此小组会上同学们多次批评我不关心政治,思想消沉……
9月底,我们又奔赴农村,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帮助农民秋收秋种。这时我们的口粮供应由每月30市斤降为24市斤。人人皆知的吃不饱,人人也不敢说吃不饱。又来了新的政治口号:“低标准,瓜菜代”,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只有天知道,瓜菜在哪里?生产队每天给我们蒸一锅用洋槐树叶做的菜团子,里面放很少的玉米面。由于天气已进入初冬,菜团子冰凉,吃后我的胃受不了,不吃,又饿得受不了,干脆,要后面的受不了吧,这样也节省下菜团子,自己也免得受罪。有的同学对洋槐树叶过敏,吃后脸肿、手肿,也就不吃了。时间到了中国人大团圆的仲秋节,同学们却高兴不起来,无米之炊。仲秋节下午,生产队长给我们送来一只瘦鸭子,全班同学立刻沸腾了,但怎么做法,怎么吃法,又犯难了。因为我们是一群小孩子,一直在外上学,在家从未帮过炊。我小时受母亲的指教、熏陶,平时同学们聊天时,我又聊些做菜、做饭的方法。全班同学一致推选我为厨师总长。我将鸭毛退掉,洗净,将整个鸭子剁成肉沫,放上两把盐,煮了一大锅鸭子汤。因为过节同学们提前半小时收工回来后,每人美滋滋的喝了一碗热鸭子汤,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终生难忘的仲秋节。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如在昨日,记忆犹新。
回校后,还是饿字当头,由于缺乏营养,有一大半同学得了肝炎病、浮肿病,有的同学用酱油冲水来充饥。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我到郊外捡拾农民田地里丢弃的地瓜叶、地瓜蔓。回校后洗净,切碎,放在洗脸盆里,倒入开水,浸烫15分钟,沥净水后,再重复一遍,如同在课堂上做化学试验一般。再买2分钱的酱油倒进去,调拌后,分给全班同学吃,同学们饥不择食的雀跃疯抢,一直在吵:这是谁的发明?是否还需要申请专利?这一填满肚子的“科学方法”很快在全班普开,也算挽救了一些人。后来,在捡拾地瓜叶的同时,同学们也做一些农民不要了的地瓜复收。复收回来的地瓜总不能生着吃,煮地瓜的木柴又成了难题。因为我从小在城市长大,知道搞建筑用的那些油毛毡,可以点燃烧火。我便从我校建楼工地上,一小块,一小块地捡拾那些丢弃不要的油毛毡。同学们每天早晨,将地瓜装入水桶煮起来,宿舍区炊烟四起,烟雾缭绕,好一派繁忙的早炊景象。当时,有的同学惊奇的直接问我,你怎么知道油毛毡能烧火呢?在四年大学期间,我“研制”了两项发明,但均未申请专利。这真是人生中一段不可忘怀的黑色幽默。
那时,每个同学每天吃几两饭非常有计划,甚至连一粒米也不敢多吃,也绝不敢寅粮卯吃。可是发现我们班有一同学几乎是顿顿敞开肚皮吃,同学们产生了怀疑,给支书、班长反映情况后,支书、班长决定在他去上课时,翻他一下,结果从他床头翻出二百多斤饭票。据他交待,某日夜间,他从食堂里偷的。我们捡拾地瓜叶、蔓与这位同学走的路径不同,但目的完全相同。这位同学被开除学籍了。与此同时,更大的恶性事件发生了。在我们学校大门口出现了“反饥饿”的标语,又在学生食堂饭票上出现了“忍饥挨饿的伙伴们,起来吧!起来要求地瓜、黑馍(地瓜面窝窝头)和能充饥的东西。”这两条“反动”标语一出现,却给广大同学带来了麻烦,停课,对笔迹,排查,检举,破案……弄得人心惶惶,惊魂四起,折腾一周也无结果。到寒假放假前,每人又写了两份与上面同样话的字条交上,才告一段落。寒假后,我们在火车站劳动时,这位同学逮捕入狱,判刑7年。
寒假后,我们班一位十分老实而又内向的同学背后对我心神不宁的说:“我不想上学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打成右派的都是知识分子,上学越多,打成右派的可能性越大,工人、农民,哪有打成右派的?”我说以后可能会好点。处于那个时代我也不敢多说,我的政治觉悟水平也不高。一周以后那位同学装病退学了。1957年反右中,最高领袖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作了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组成部分的“科学论断”,他的这一科学观点,1958年5月5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又得到全体中央委员的确认,成为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永世的“神圣法典”,可与3800年前的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相提并论。我们这些几年后将成为知识分子的青年人,不言而喻也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使人不寒而栗。同学们愈来愈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凶险。
建校劳动日正好与月末碰在同一天,一个月的饭票将用尽。我同一学习小组的一同学也身材魁梧,人高马大。早晨喝了一碗稀粥,中午吃了两块炸咸带鱼,晚上无饭可吃,抬了一天的大筐,现在回想起来真不是滋味。那时就连父子也顾不上啦,那还有什么父子情,同学爱!完全导致了人性的丧失。这些忧伤的细节和悲怆的情感将口口相传永远载入史册。
四月初,春暖花开之际,我们班又去距学校30公里的山区修水库,我们班的具体任务是运土、运石料,一干又是一个月。经过这样的千锤百炼,谁敢说我们不是无产阶级的红色知识分子!
四、1961学年
这一年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并实行的“调正、巩固、充实、提高”发展国民经济方针的指引下,我们的学习完全走向正规。认认真真、实实在在的学了一些专业知识。寒假后,我们又分赴外地进行毕业实习。我的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均获得满分,得到了指导老师的好评。
八月初,我们愉快的分别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是那些乘风破浪前进的场景,那些刻骨铭心的教训,还不时在脑海里荡漾,成为全然不可忘却的记忆。以史为鉴,希望那些类似的悲剧不要再以不同的方式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