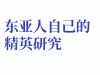1993年,29岁的中国政法大学在读研究生薛波,在和同学查阅资料时,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本的《英美法词典》。而我们的邻邦日本,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有了一部《英米法词典》。敏感的薛波意识到,我们和日本在法学领域为何存在巨大差距了,而我们和英美法系的国家谈判时,又为何有时会发生鸡和鸭说的情况了。
中国已经和外界处在日益频繁交流的时代,不能总是自话自说,编辑一部《英美法词典》,与世界接轨,就成了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一
有人会问:词典为什么重要?潘汉典教授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长期以来被翻译成了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就是30年。从1954年、1975年、1978年到1982年,三次修改宪法,都没有发现错译。直到1985年才得以改正。
前些年,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法律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100亿美金。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高宗泽律师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
过去,我们闭关锁国,与西方隔绝,自己玩独龙游戏是可以的。但改革开放要融入世界,要解决贸易纠纷和国际纠纷,就必须懂得英美法。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是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是依照英美法。一直以来,因为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
故而,组织精通英美法的学者编写一本高质量的词典,便刻不容缓地摆在了国内法学界的面前。
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经验,只能一边摸索一边编写。一群人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宿舍内,从早上8点忙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终于辛苦地做出了一些初步成果。但拿给具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这不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英美法教育传统被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民国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他们,是一群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学精英。他们最具才华的年代,被轻忽法律的环境所压制、所摧残,甚至扼杀。但词典的编撰,非他们的加入不能完成。
他们中的有些人,早在1949年以前就已经是法学界的著名权威。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这所大学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惟一系统讲授英美法律的学院,是1949年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由于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程序,国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政府很是焦急。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这才组建起一支赴远东军事法庭的队伍,其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东吴大学。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场
可是1949后,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最优秀的人物,只要选择了留在大陆的,都几乎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情。
二
那几年,薛波在上海、南京、杭州,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1900~1997),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后来的代校长兼法学院院长,前后任职20余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法学人才。他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法律教育家,他在东吴法学院任职期间,始终维护学院独立超然的行政地位,他招聘的教授,世界著名,他们的著述当时领先,从学院出去的学生享誉国内外。
1946年东京审判,中国出席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法官、检察官、顾问,几乎全部出自东吴法学院,这些法官们都是盛振为院长亲手选派的,他们或者是盛振为聘请的教授,或者是盛振为的学生。
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国一共出了6位国际法院的法官。这6位国际法官清一色全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而这些教授和毕业生不是盛振为的同事就是盛振为的学生。
就是这样一位法学界泰斗级的人物,在1950年被撤职,不久又打成"反革命",判处10年徒刑,押送甘肃劳改,后因宋庆龄出面说情,6年后才被释放,1980年代获官方平反。
高文彬,1921年出生于上海,1945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1946年应聘前往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加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工作,先后担任国际检察处翻译官和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健在的全程参与过1946-1948东京审判的亲历者。当年,是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证据,才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了绞架。
高文彬被聘为翻译时月薪250美元,几个月后由于工作出色,在结束翻译工作后,被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留下担任秘书,月薪涨到300美元,当时每顿饭花费0.4美元,生活非常富裕。
东京大审判结束之后,法庭上结识的美国朋友邀请他赴美深造。高文彬考虑到一大家子人都在上海,自己身为长子,肩负着养家的责任,所以婉谢了对方的好意。

年轻时的高文彬
1952年,高文彬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敲锣声都听不见。但他凭着不屈的精神、顽强的毅力和坚韧的信念,在监狱和农场期间,从未放弃过阅读学习,每天坚持写英文笔记。1980年后高文彬终于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高文彬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
周枏(1908~2004),被中国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像王国维、胡适、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名家,而周枏位列其一。
像这样一位法学大家,直到薛波拜访他时,才发现他竟然生活在极其简陋的环境里: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位于上海南昌路282号。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
周枏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枏最值钱的家当。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枏,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此后,在距离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枏度过了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落实政策,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了10年。退休后,因为没有房子,他只得选择回到上海。
再后来,因健康问题,年迈的周枏无法照料自己,又搬回安徽女儿家居住。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在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俞伟奕(1922~2004),1944年东吴大学法学士,后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牵连,反复遭受批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受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品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调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1916~1999),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抗战后任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竭尽心力。他去世后,大家才知道——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卢峻(1909~2000),东吴大学1930届学生,毕业时同时获得复旦大学文学士硕士学位。经业师吴经熊老师推荐,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就读,1933年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国际私法之理论与实际》等。卢先生在上海的旧居属于极个别的未加任何装饰的民国旧居,质朴得让人震撼!他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钱买的。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身体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哈佛法学评论》每期都要给他寄送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蔡晋,1933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先后担任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并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1980年应聘为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主编《国外法学知识译丛·刑事侦查与司法鉴定》,编译《各国宪政制度和民商法要览·欧洲分册(下)》。在上海法学研究所受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委托审查部分香港原有法律的任务中,他写出了《最高法院条例》和《刑事罪条例》的审查报告,作出了重要贡献。
晚年的蔡晋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的奶粉罐,装着蔡晋全部的"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就连这样条件的医院也是难以入住的。即便如此,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上。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是照顾他的护工的休息处。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一同轻轻地放置于他的灵柩内。
三
很多年过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拜望卢峻的情景。
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了出来,欣慰地说:"我答应你。"
在华东一带,薛波共找到14位老者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1930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1949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1979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1980年代后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
这些审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84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奉献。
老人们以极其严谨而忘我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仅只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w(美国法),卢绳祖先生(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就写下了2000多字、长达6页纸的注释。结果,近90高龄的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
周枏先生的手高度颤抖,已无法正常书写,字迹不好辨认,他便委托80多岁的夫人——1930年代的经济学学士,将书写的稿件一一誊抄。
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论起来。
王毓骅先生目力衰减,必须借助自然光阅看稿子,但他家中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前往几公里外的女儿家。
潘汉典先生(1921—2019),27岁时毕业于东吴大学比较法研究所,获法学硕士学位。精通英、法、日、德、俄等多种语言。他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1949后仍能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这让他很幸运地躲过了那场灾难。在手术前的48小时,潘先生仍还挂着尿袋审稿。是什么动力,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编写词典的事业中?"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潘先生母亲在抗战中家破人亡,去世时,留给他两句话:"你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仗义执言,无愧于你父母的中国人。"潘先生以促进我国法学和法制建设现代化为己任,致力于介绍当代外国法学,投身英美法词典的工作即其一端。他说:"其他,我没什么好说的。"
四
薛波多次向记者提起老人们在上海第一次开会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几个东吴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个小会议室里,5月的上海已经很热了,会议室没空调,房间闷得要命,老人们却讨论得很热烈。会后,薛波要找一家好点的饭馆吃饭,老人们死活不答应,"很好了,很好了",每个人都这么说。最后进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饭,10块钱,老人们都吃得很香。
词典出版时,几乎没有人要求署名,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定会是一项青史留名的事业。"千万不要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潘汉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卢峻先生时,卢先生拉着两人的手多次叮嘱,不仅如此,就连600元的审稿费卢先生都捐给了编辑部。
他们铭记着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几乎每位老人的心灵都受到过深深的伤害。除了宝贵的时光,被剥夺的,还有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学者以学和思为业,然而他们却被迫停止学习和思考近30年。
薛波曾多次到过每位老人的家,几乎每个老人家里都看不到书,那时是不敢有,现在则是没钱买。审稿时,有时为一个词甚至要去开架书店查阅。
老人们的奉献,是他们唱响的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荣誉、尊严和承认。""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努力地工作,是在响应他们内心深处的召唤。"
卢峻先生去世后,在他的葬礼上,他女儿再三向薛波致谢:"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晋先生,蔡先生每次看到他,都非常高兴,脸上会浮现出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说话,他的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薛波: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学,奉献于社会,这也是他人生的价值。
可是,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薛波看过老人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面目清秀,一个昔日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晚景竟如此凄凉。
不是所有的东吴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请。一位耶鲁大学的法学硕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绝:"我一只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这么多年不搞法律。"回信简短,但文字背后的沉痛难以言说。
更令人痛心的悲情来自一位东吴老人,她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遭受的苦难,全都忘得干干净净。薛波说:"她越平静,越不反省,我越觉得我们的可怜。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个人彻底转向,把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抹得一点也不剩下?"
五

1997年7月29日在上海的部分《元照英美法词典》审订学者合影,左起分别为潘汉典、周枏、卢绳祖、许之森、蔡晋、徐开墅、高文彬、浦增元、郭念祖诸先生。
一部词典引出了一群老人。
这部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
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历经九载寒暑,呕心沥血,在默默无闻中不计名利地编写,终于做成了一件功垂千秋的大事业。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这是谁的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