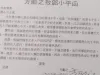方励之学长(一九三六--二○一二)过世将及半年,作文以纪念之。即使作为“文革”后鹊起于国际学界的中国科学家,方励之亦不啻凤毛麟角,中国有几人?就此,我们也不应忘记他。一九五六年从北大毕业的方励之夫妇是“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青年学子,作为学生干部更是处处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听党的话,又红又专。方励之生前的办公桌上还放着下半年要来随他作研究的中国学生的资料,至死不忘服务中国。方励之那一代人是最虔诚最热烈的爱国者!但是国爱他们吗?作为“六四”精神领袖,方励之夫妇在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无奈去国后,可怜再也没有踏上故土,有国难投他们被剥夺了回来的权利,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方励之已仙去,让他魂兮归来吧!
同为学生干部
方励之长我半岁(六个月零三天)却高我二个年级,十六岁时他已读大学,如果小学、中学是一步步读上来的,那方励之四岁时就上学了。一九五四年我入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时,方励之和李淑娴已经升到物理系三年级。一进校我即为团支书,方李二位早已是团干部了,北大团委书记胡启立召集学生干部开会时,得以认识方励之。一九五五年胡启立任全国学联主席,然后离开北大去了团中央,他在一九八九年和赵紫阳一起被踢出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据说原定胡启立将接班任总书记。一九四五年起胡启立曾在北大物理系求学四年,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毕业于北大机械系。
此处所说“物理系”实指北大物理系中的物理专业。“院系调整”后系里除物理专业外,还有气象专业,不过教师和学生的多数、尤其是众多名师在物理专业。一九五八年秋,北大物理系分解成了三个系: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和地球物理系,后者包含了气象专业。此外,一九五五年北大新设了培养掌握核裂变人才的物理研究室,它虽冠有北大名头,可是通了天的。铀或鈈核裂变的连锁反应过程就是原子弹爆炸。物理研究室在一九五八年也撩开了点神秘面纱,唤作为原子能系,并开始招收一年级新生。这个系经费足,受重视程度远高于前三个系,且不位于北大校园内,后来它改名为技术物理系。
功课好且已入党的方励之,又专又红,四年级时转入了新成立的物理研究室。一九五六年方励之从北大物理研究室毕业时,被挑选去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学院的政治氛围比北大宽松,更强调搞好科研业务,反右时方励之被保了下来,说若戴帽就可惜了。不过“原子弹”工作是不能让他碰了,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被近代物理所下放农村劳动九个月后贬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九五九年初方励之在科大被处理成“内控右派”,只开除党籍没划为右派份子,后来他也被叫作“漏网右派”。
同样是又专又红的李淑娴,一九五六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时留校当了助教,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九五七年她被戴了右派帽子。
一九六一年十月六日方李二人结婚,互相搀扶着携手走过五十年又半年整,方励之竟驾鹤西去了,呜呼!
方励之的同学
一九五二年和方励之、李淑娴同时考入北大物理系的有周海婴、谭天荣、倪皖荪等多人。当时物理系的课业很重,鲁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婴没有能坚持到底,就业当了物理系的实验员,不久改行了。天马行空不务正业的谭天荣也留级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起北大校园里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助党整风”大字报,谭天荣终得以甩开课业语不惊人死不休了,于是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唯一的“右派学生首领”,改正后算作是一九五八年毕业。北大物理系代有怪才出,例如我们级有人自学古印度梵文,高一级的有人研究东欧共产党上台执政史,等等,但他们的本业成绩都很好,谭天荣似是例外,四年课程读了六年。
和方、李同为学生干部的倪皖荪功课也很好,那时“政治挂帅”之风尚未炽盛,功课差的同学没什威信,当不了干部。反右前高校学生没有班主任,也未设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的发明权属清华蒋南翔,比笔者晚六、七届的胡锦涛的第一个职业即为清华水利系的政治辅导员),记得连哪个同学住哪个床位也是由我派定的,学生党员极大多数来自工农速成中学,跟班很吃力,还得我搭配成绩好的同学人盯人帮他们学习以“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因此所有的学生工作都落在学生团干部身上。即便如此倪皖荪仍是学习优秀,一九五六年毕业时得以留校当了助教。福兮祸所伏,他没能逃过反右浩劫,一九五八年初被迫离校后没有再回北大。
一九五七年春,反右前夕,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到北大开学生座谈会,他传达了毛主席的号召:发扬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帮助党清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三害”恶行。话已说得如此激越如此恳切,显是昔日的北大校友今天的伟大领袖披肝沥胆之言,且是派文化教育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官员来转告的,热血沸腾毫无机心的毛头小子们怎能不激动万分积极响应。我们轻信了,可谁又能不堕入彀中呢?陷阱早已挖就,虚“席”以待,就等着北大的傻小子们一个一个往下跳了。事后毛泽东说那不叫阴谋叫“阳谋”,为的是以知识份子为假想敌“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一九五七年“五·一九”初起时蛰伏的北大左派很快就清醒过来,挟倾党之重暗运功力泰山压顶般扑向右派,扭转了原说的“助党整风”大方向。课也停下了,校园里一片混乱。倪皖荪、李淑娴和已在科学院工作的方励之三人准备给党中央写信,谈自己的看法,信未写完,反右即开始,这三名同案犯中的二个北大人,上书党中央事未做成就成了右派。
北大物理系位列反右冠首
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和副组长彭真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他们适时提出说右派还抓得太少,要进行“反右补课”。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在中共最困难的一九二七年将毕业于北大时毅然加入了共产党,后留学日、德,是党内少有的教育专家,曾任延安自然学院院长)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北大反右运动到此结束,今后一个不抓,明天起放寒假。直接领导北大反右的彭真听闻后,严厉批评江隆基右倾,用陆平顶替了江隆基,并调派亲信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兼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为北大物理系反右工作组组长,进行反右补课。于是北大物理系的反右夺冠矣。
二○○三年初版、二○○九年再修订版的《北大物理九十年》中写道:“ 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中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居全校各系之首,也居全国物理系之首。 ”(见该书P.57),“ 反右运动对全国的知识份子起了钳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巨大作用,对北大物理系学生的伤害尤大。一大批品质优秀并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青年师生受到了重大打击……。 ”(见P.58。该书两主编中的第一主编是一九四三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的老共产党员,反右惨剧后的一九五九年被委任物理系代理党总支书记以安抚人心,后离休于北大副校长任上)。再录一说,反右史专家《阳谋》一书作者丁抒,在一九九七年反右四十周年前夕发文《北大在一九五七》说:“ 当时物理系的学生似乎格外活跃,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校的右派学生,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 ”北大物理系学生何以遭此惨重打击,丁抒是作了解释的。丁文中还写有“在北大,谁在大字报栏前读后来成了右派的人写的文章时点过头,就是'点头右派'。谁看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时摇了头,那立场也就一目了然,是为'摇头右派'。”真是抓右派抓红了眼。二十多年后,北大所有的右派份子,包括许多己被迫害致死者,全都被改正了,也即北大右派100%抓错了,没错你改什么正!但是当局至今仍是不肯否定北大的反右运动。
一九五八年临毕业那学期我也被“反右补课”推下了深渊。杨述组长随手从桌上抓了枝铅笔,在一份黑名单上我的名字下面信手划了条黑线,黑线以上包括学生党支部书记和我这个团总支书记都戴上了右派帽子,黑线下面紧挨着我的那个同学在一九八○年戴上了一顶中国科学院院士帽子。据说我是北大最后一名中箭者,虽然我没有贴过大字报,也没有参加过大辩论,和李淑娴类似,她是主动向组织讲了自己的看法,我是主动向组织交了自己的日记。
戴帽后仍让我随班读到了毕业,是年夏被科学院应用物理所接受。北大物理系的毕业生即使不是右派也最希望能到科学院工作,他们竟推荐了我、录用了我,不可思议,要知道“右派就是反革命”!一九五八年我进了科学院,因此方励之所讲的科学院、以及由科学院兴办的中国科技大学的某些人和事,也略知一二。
一九六○年我被科学院政治部派人来物理所宣布摘去了右派份子帽子,自以为从此和他人一样了,可以自由地搞科研了。后来感悟,我只是个“摘帽右派”,摘帽右派(一九七八年后叫“改正右派”)仍属“右派”,依然受“革命群众”尤其是其中的“共产党员”的欺压。一九六三年,我所在部门对一九五七年以来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作了一次考核,我考了第一。事后其他所有人都升到了中级职称并长了工资,只我一人还是初级的研究实习员,当然这个廉价劳动力还是要利用的,用来搞科研。那时我躭的科研小组里有林彰达等二人,他们和方励之李淑娴同年入学北大物理系、同年毕业。林是共产党员、科研小组长,一九六四年初“阶级斗争”这根弦再次被毛泽东绷紧时,党员组长公然抢夺了我的科研成果。
一九六八年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时候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至此我已受辱十年,有如癌症患者历尽痛苦岂能再挨,南宋高僧的偈语“他从东方来,我向西方去”也给我以引领,剪颈自刎了。事后得知,右侧颈总动脉断裂半厘米,还只有点皮粘连着,了无知觉多日后竟被阎王老儿一脚踢回了人世间。其后还遭遇了更惨烈的精神杀戳,偶语依然泪满襟,不去多讲吧。我是说象我这样北大最“幸福”的右派尚且如此,其他右派难道不会每人都有一本血泪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一九五八年秋,科学院自产自销办起了科大(各部门自成体系也是“中国特色”之一)。同时还建立了中国科技情报大学,很快它即拼入了科大。科大校长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其实郭在科学院也只是挂个名,他还有一大堆头衔。除挂名的头面人物及开办时去讲过点课的著名老科学家外,科大的教职员主要来自科学院各研究所欲予淘汰的人员,有二大类,或是“政治差”或是业务差,前者为主。“政治差”业务棒的方励之也调入了科大。
前面讲到摘帽右派属“右”派,内控右派当然也属“右”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科大也逐渐抽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方励之既属“右”派怎会有好日子过?科大地址原在北京玉泉路(一九八九年入城部队就是从玉泉路杀向的天安门),文革前校内只授基础课,专业课由相关研究所的在职人员承担,笔者也曾是科大第一届和第二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那是在一九六三和一九六四年。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副统帅发布“一号通令”后,在京各单位紧急动员起来准备迎接战争,很多单位被指定疏散出京。次年,科学院各所很多人,包括和我同一科研小组的陈云女儿等人,当然也有我这个摘帽右派了,被赶去了湖北省潜江县的科学院“五七干校”,据说该地曾是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我们被当地人称作了“二劳改”,实际上也差不多。科大则被赶到了安徽合肥,与此同时科学院还在合肥建立了分院,以和科大呼应。科学院合肥分院“废物利用”了安徽省为争取在合肥召开中共“九大”于郊外盖的一片别墅区,科大的很多房子就需自建了,于是方励之成了科大制砖厂的主劳力之一,摔砖胚泥可是个重体力劳动。此前,他们刚到安徽时,方励之还当了半年多的“煤黑子”,下到一百多米的地下挖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地底,方励之神游到了光明的天体。回到地面后方励之为避蚊虫叮咬躲在蚊帐里阅读朗道(ЛевДавидовичЛандау,一九六二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苏联犹太人)的《经典场论》,冥想驾驭广义相对论去窥探早期宇宙。
也有人对我说,方励之离开制砖厂后被派去烧锅炉,炉内加好煤后他加紧时间开始阅读天文学文章,凭他扎实的理论物理基础(方励之在北大读的是理论物理专门化,李淑娴和笔者读的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很快他就成了天体物理学界的佼佼者,自此方励之没有再改变专门化领域。后来他担任了ICRA(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指导委员会主席,直至撒手人寰。
科大搬迁合肥后仍有多人嚷嚷着要回北京,最后由华国锋签字拍板,科大永留合肥。科大研究生院也称科学院研究生院,带研究生的导师是在京各所的研究员,研究生院自是要留在北京。当年我们(物理所和数学所的光棍和准光棍,笔者是老婆不在身边的准光棍,陈景润是真光棍)集体居住了近二十年的中关村八十八楼,后来大加修饰改成了科大研究生宿舍楼。科大合肥本部只有大学本科生,教师中的方励之等“老”人的户籍关系也保留在了北京。
物理所和科大
“解放”时接管了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后,中国科学院把物理所分解成了应用物理所、近代物理所、力学所、电子所、声学所、自动化所、地球物理所、气象所以及生物物理所等多个物理类研究所(指在京者,生物物理所应归入生物类)。不久,近代物理所改称原子能所(后来其中的物理部分独立成高能物理所)时,应用物理所也恢复了原名——物理所,且再分立出了半导体所。“物理”的学科范畴较广,派生出了那么多物理分支研究所后,物理学的主体仍在物理所,计有光学、磁学、激光、等离子物理、晶体学、低温物理、高压物理、固体电子学、理论物理等研究室。打倒“四人帮”后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一九五九年我所在的应用物理所从城里东皇城根大取灯胡同九号(原北平研究院物理所的所址)搬到了西郊北大附近的中关村,并改名为物理所,此时它也还是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大所。因而,直到一九八七年初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次把方励之开除出共产党时,物理所对科大一直有最大影响。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许良英(“解放”前是浙大物理系高材生、当时工作于科学院自然史研究室)、刘宾雁(著名记者)和方励之联名给一些右派名人寄去了“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信函,这三人发起(讨论时李淑娴也在座)拟于次年反右三十周年时举行学术讨论会,以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识。”信由方励之起草。力学家钱伟长接信后向“组织”报告了此事,据说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有份,引起了当年具体领导反右运动的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的勃然大怒。一九八三年发行《邓小平文选》时,已抽掉了其中有关反右的一系列指导性讲话、文章和文件,此后竟还有人敢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不是公然逆龙鳞嘛,于是下令把王若望(邓大人误认许良英为王若望了)、刘宾雁和方励之第二次开除出党,并严厉指责了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迫使胡辞去了总书记职务;另方面立马任命因右派事还被清华大学挂着没有“分配工作”的钱伟长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并于一九八七年犒赏钱伟长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次年犒赏费孝通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九八九年夏秋之交,政协副主席钱伟长第一个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在全国政坛上谴责了反革命暴乱,他比共产党官员还起劲。
一九八七年,科大副校长方励之被“撤职”,科大校长管维炎是被“免职”,由另一副校长辛厚文执掌了科大实权(当时在科大,党组织书记的权力不及同级行政长官,行政负责人曾是或仍为科研教学骨干)。管和辛都来自物理所,管曾是低温物理室的副主任,辛当过我们磁学室的党支部书记。辛厚文曾被起绰号辛厚皮,物理所内年龄相仿的同事间呼唤绰号屡见不鲜,辛厚文一九五八年毕业于东北人大(后改名吉林大学)物理系。管维炎是老共产党员,一九五一年入学北大物理系,二年后去苏联续读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然后是研究生。学成时曾要留他当中国驻苏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他想搞业务,回国后到物理所从事低温物理的研究工作,一九八五年去当了科大校长(编制仍在物理所,户籍仍在北京),直到一九八七年初被免职。一九八九年“六四”后,管维炎流亡到了欧美等国,最后去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任教,客死在他乡。微妙的是管维炎去国后,当局没有为难他的家属,没有收回他在北京中关村的住宅,甚至连家中的公费电话也没有停机,个中缘由岂我等小百姓能知晓。
方励之何时走上争民主道路?
李淑娴戴了帽子是“敌我矛盾”,方励之没公开划成右派仍属“人民内部矛盾”,二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二重天,共产党待之自不一样。一九五七年开始一九五八年结束的反右派运动,使很多知识份子清醒了,只有我这个所谓出身“好”中毒太深愚蠢至极的右派份子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时才初步觉醒,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时才彻底觉醒。方励之什么时候开始觉悟的我不知道,我总觉得他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崇高地位和他杰出的学术成就是分不开的。论文在国际上出名了,压不下去了,闷不死他了,就象科学院数学所的陈景润那样。陈景润只关心他的“1+2”——专注业务,那也很好呀。方励之不会仅止于此,学生干部出身的人习惯于关心周边他人他事,方励之自有一种社会责任心,他有着大爱,妙手着文章之外还牢记着铁肩担道义,达则兼济天下。在他身上能看到“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种中国知识份子的传统风范,那是来自屈原的“ 伏清白以死直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孟老夫子说“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笔者竟“穷”时也不安分守己独善其身,还唠叨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悲夫。在“党的领导”贯穿天下的国度里,哪有匹夫说话的份?即使知名如方励之若图妄议兴亡事,“六四”时如未躲进美国大使馆,说不定就被“乱枪击毙”了;后来哪怕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也敢关进监狱,彻底堵上了嘴巴,悲夫!
一九八四年方励之当了科大副校长(如果他没有“共产党员”的红顶子则绝无可能,若戴过右派帽子、那么早当副校长恐也不成,用数学语言来说红顶子和没划过右派是一九八四年时当高级领导的必要条件,但不充分),其后他才在民主和人权道路上不自觉地崭露头角施展抱负,一九八九年达到“中国的萨哈诺夫”地步。我无意贬低方励之对民主事业的真挚情操和担当精神,我只是想说和方励之有同样认识的人难道少吗?不管怎么说,我仍十分推崇方励之,他是中国知识份子的杰出代表,我为从北大校门走出这样一位物理学家感到荣光,蔡元培校长教诲学生“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方励之得其真谛,成了从北大发起的“五四运动”的真正传人。
《礼记·大学》中列有“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修为准则。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早期science(科学)曾被释为“格致”,稍后则把physics(物理)释作“格致”,Search into the Nature of Things,物理学是研究事物本性的学问,学物理的人最崇尚理性,最讲究实验验证,最实事求是,最服膺真理。在苏中两个一党专政的大国里争民主争人权的领袖人物都出现在物理学界,其他自然学科或社会学科是没有的,难道不说明问题?
钱临照先生包庇方励之
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物理学报》登出了方励之的第一篇论文,毕业五年,期间经历了残暴的政治运动、不止一次的下放劳动,就能在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真了不起。其后则一发不可收拾。除了他的论文品质高外,老一辈物理学家为他撑起了一把政治保护伞也功不可没。共产党为扼杀政治上的右字号大小人物,各报刊禁止录用他们的文章,不管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甚至是豆腐干短文。当时《物理学报》副主编钱临照先生把方励之改名“王允然”刊出了他那个第一篇。钱先生早年留学英国,他隐隐然说方的文章是Her Majesty(女王陛下)“允然”的,“文革”期钱先生巧妙地解释为那是“王竹溪先生说行”。比钱先生年轻五岁的王竹溪是《物理学报》的主编。方励之并不隐匿“ 我的学术生涯一启动,就得到过钱、王二先生的保护。 ”
笔者初入应用物理所时就听到了钱临照先生的名言“ 党总支书记嘛是给我们跑跑腿的 ”,那时应用物理所还没成立党委只有总支。其实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也说过类似意思的话,但是很多话只能由党的领袖说,别人说不是反党也是落后。于是曾担任过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即代理院长)的钱临照先生被贬去了科大,没有通告他本人甚至把钱先生的编制也从物理所划去了科大,以致后来钱先生九十三岁时即使将病逝于合肥也不肯回北京(治病)。
文理兼修的王竹溪先生
王竹溪先生是北大物理系的教授,教过我们热力学、统计物理和量子力学(为感激师尊,北大百年时笔者曾向王竹溪教育基金略表心意),他编著的《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导论》除中文版外,也有英文版,苏联人并将之译成了俄文版,享誉国际。王先生带领郭敦仁合着的《特殊函数概论》(时为讲师的郭敦仁据此教过我们“数学物理方程”课程)也远播海外。一九三八年王竹溪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仅二十七岁即为西南联大物理系中的清华教授,给联大本科生授课,后也是清华研究生杨振宁的指导老师。除教育任务外,JwuShi Wang(王竹溪)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八年间在英美中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近二十篇论文(那时的中国物理学报也是英文版),因此他又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一荣誉称号。在归国博士那些老先生中,王竹溪的论文特多,涉及多个物理领域,此外在生物物理、计量、物理学名词和数学名词审定等方面也多有贡献。
王先生还利用业余时间编纂了《新部首大字典》,收录汉字超过五万一千个,多于《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各字释义精当,并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古文、大篆和小篆。这些特殊字形没有字模,因此该字典在王先生过世五年后才由两家出版社合力出版,全书二百五十余万字。原稿中各字皆手绘,足见王先生的坚毅和严格。“新部首”由王先生发明,重码极少便于机器检索。这部字典的出版引起了台湾、日本、美国等处出版界的极大重视。
一九四九年王竹溪三十八岁,还处于出成果的最佳年龄段,可实际上有份量的学术论文皆发表于此前,虽然一九三八到一九四八年间的物质条件异常艰辛。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清华军管,此后王先生的主要学术著作是归纳自己以往的成就并博采众长以著书,所谓“著书立说”自是立说在前著书在后。“解放”后王竹溪先生有了多个头衔,挤占了时间和精力,更主要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显然,“政治”对学术的冲击力远甚于物质困苦。五十一岁时还叫他担任了北大副校长。然而,那些头衔没有保护得了六十岁高龄的王竹溪先生躲过被下放的噩运,他在江西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当放牛翁时,染上了血吸虫病,后来导致肝硬化,过世于一九八三年初,不到七十二岁,在中国著名科学家中显属早夭。
一九八○年的物理学院士方励之、管维炎和李荫远
方励之的第一篇论文属核物理领域,其后他只好转向“民用”物理。经钱临照先生关照,方励之与李荫远研究员领导的物理所理论物理室人员合作,发表了二篇固体能级和掺杂的论文,然后是激光方面的理论文章,到一九六五年方励之已在《物理学报》上发表论文十三篇,走出校门九年即有十三篇,实是杰出,他那时还只具助教职称。
科大搬去合肥后,方励之转向了天体物理,在这一领域他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因此,一九八○年方励之四十四岁就当选为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殊属年轻,和他同时成为院士的管维炎和李荫远分别已达五十二岁和六十一岁。搞理论物理的人一旦入了门,得心应手后论文就会一篇篇地出,当然也要是佼佼者。不象实验物理工作者,很可能多少年也做不出成果来,科研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甚至可能失败居多。在物理学界从事实验物理的人远远多于理论工作者。
方励之在回忆文章中写有:“ 李荫远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一九六二--一九六五年间,我一边在科技大学教书,一边在李先生门下作研究。 ”“参加李先生的研究组,对我有极大的帮助。 ”李荫远先生还接替钱临照先生担任《物理学报》副主编多年,王竹溪先生过世后则为执行主编。二○一○年耶诞节前,李先生给方励之发去电子邮件,说“ ……钱先生辞世不觉已十一年了,我手边只有他指导的科学史学生早年写的传略。我在网上读到过你的两篇回忆散文,都是关于大学刚毕业时期的,也许你真该动笔写回忆录了,不是写你正确与否,而是可以给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之采择与评论。 ”邮件中说的钱先生指钱临照先生。
李荫远先生一九四三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一九五一年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一九五六年初回到中国大陆,在磁学、光学、激光、晶体学等方面取得了广泛的理论成果。退休后淡出物理,连院士会议也不去参加,却编辑出版了《当代新诗读本》,且“看重涉及世势坎坷的篇章 ”,同情受迫害者。笔者和李荫远先生同在物理所大楼里躭过二十余年,印象中李先生是埋头业务、论文很多、远离政治的学者,谁知他在文革期“ 作为革命的对象,我有写不完的检讨,每天上班要先向毛主席请罪,接待外调时受尽斥责 ”日子也不好过。后来则“ 由于十年浩劫的后遗症,我的三代六口之家散架了 ”(二个女儿去了美国)。到去年底九十二岁的李荫远先生说:“ 当今出现的社会危机绝对不是个人的问题。 ”真知灼见呵。
国际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黄昆先生
方励之、李淑娴结婚时都已是被开除出党的右字号贱民,李淑娴的业师黄昆先生却不避嫌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在避之不及的年代殊属可贵。黄先生是中国大陆半导体物理教育的开拓者,创建大陆半导体产业的人也悉出黄先生门下,建立在半导体晶片上的数位产品现已应用到方方面面。
一九四四年黄昆在西南联大物理系中的北大物理系跟从吴大猷先生取得了硕士学位。吴先生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达十一年之久,请辞后被李登辉挽留为总统府资政,直至病逝于台北。
一九四五年黄昆考取了用“庚子赔款”培养中国学生的免费留学英国名额。去英后师从著名固体物理学家莫特(NFMott,一九七七年获诺贝尔物理奖),一九四七年成为博士。期间,发表了固体中杂质的漫散射理论,它在六十年代被实验证实,而被称为“黄散射 ”;后和小他七岁的英国女子理斯(A.Rhys,一九五二年只身来中国,成为黄夫人,并起中文名李爱扶)合作完成的固体多声子跃迁的量子理论,曾被叫作“ 黄-理斯理论 ”,一九九四年以来该论文仍平均每年被引用20多次,苏联人佩卡尔平行提出了该理论,因此它也被称为“ 黄-佩卡尔理论 ”;晶体中声子与电磁波的耦合振动方程,被称为“ 黄方程 ”,后世固体激光的基础论文之一。
黄昆到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之一玻恩(M.Born,一九五四年获诺贝尔物理奖)处做博士后研究时,玻恩邀请黄昆完成自己的心愿:用量子力学诠释和预测固体中的物理现象,将之提升到现代物理学的层面。黄昆接受后写出了《晶格动力学》(Dynamical Theory of Crystal Lattices),玻恩写信给爱因斯坦说:“ 书稿内容现在已经完全超越了我的理论,我能懂得年轻的黄昆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所写的东西,就很高兴了。”有人统计一九七五年到二○○一年三月,该书英文版(黄昆写)被引用五二五四次,俄文版(苏联人译)被引用三七六次,平均每年二百多次,至今牛津大学出版社还把它列入“牛津经典物理著作丛书”。
一九五五年的物理学院士黄昆、王竹溪和钱临照
一九五一年黄昆先生回到中国大陆后,除了扫尾《晶格动力学》外,停止科研达二十六年,服从安排在北大物理系教书育人。笔者有幸聆听了黄先生共计开过的三门课程:普通物理(一小部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固体物理教材由黄昆教授自编,半导体物理教材和谢希德副教授合编,课程也由两人合讲。后来,谢希德先生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市人大委员长。据说黄昆先生每次讲课前的备课时间长得吓人。黄昆先生讲课时物理概念清晰,王竹溪先生上课时满黑板的公式,数学推导严格,真是二极,学生们接受不同风格的训练,得益匪浅。我们看到他们两人的穿着都十分简朴,王先生的简直可以说邋遢。
笔者和其他同学也一起到黄昆先生家中去玩过,黄先生给我们看他的影集,他在英国校园里拿大顶的照片至今我还深有印象。我们称作“李先生”的黄夫人接待了大伙,黄夫人使我们看到了英国贵族气质,人也很美,其实黄昆年轻时也是个帅哥。李爱扶先生在二个男孩大点后就职于北大物理系实验室,一九五六年英国和埃及发生苏伊士运河战争时,李先生放弃英国籍加入了中国籍。
黄昆先生在科学事业上满是大胆创新,在政治上却十分胆小听话。他是二级教授,“文革”期他将每月二百八十五元工资中的二百元交了党费,即便如此仍是受到了冲击,说他是特务,夫妻两人加两个已是大小伙子的儿子挤居在一间卧室里。“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黄昆先生紧跟党中央发文《人民日报》痛批邓小平,因此在毛泽东死去并致“四人帮”垮台后,北大有些人对黄先生颇有微词,这个老实书生自感抬不起头来。中共领袖们对国际知名的科学家还是要加以利用的,就象四人帮和毛泽东优待陈景润那样,一九七七年邓小平把黄昆调出北大到科学院半导体所任所长,邓的女儿邓楠那时是半导体所的研究实习员。于是年近六旬的黄昆先生重拾科研,被国际固体物理学界的权威说作是在“灰烬中重新起飞”。毕竟廉颇老矣,捡起的是多声子跃迁理论提出后出现的新问题,也即修补扩充“黄-理斯理论”,于一九八八年发表了半导体超晶格声子的“ 黄-朱模型 ”,朱是黄先生在半导体所的助手朱邦芬(朱二○○三年成院士)。
一九五五年,黄昆、王竹溪和钱临照同时被选为中国大陆首批学部委员,黄先生时年三十六岁(最年轻的学部委员),王先生四十四岁,钱先生四十九岁。三人中钱临照先生后来也没有被拉入共产党。一九八五年黄昆当选为设在义大利的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当时中国只有二人),一九八七--一九九一年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二○○二年获中国最高科技奖五百万元RMB,这些荣誉主要是奖赏他在英国取得的学术成就。二○○五年黄昆先生八十六岁时逝世,和陈景润一样过世前黄先生已患多年帕金森氏症,连钮扣也要贤妻李先生帮助解开或扣上。
黄昆科研事业的被腰斩是一大损失
黄昆先生三十二岁回国,正处科研最出成果的年龄段,当年国际上成就低于黄昆的固体物理工作者,后来不止一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黄昆科研事业的被腰斩,对他本人、对中国、对人类,难道不是一大损失?
为什么要限定黄昆只能搞教育不能搞科研?“解放”后当局对北大盯得很紧,必须摒弃原有的欧美式教育理念,向苏联一边倒,把教育和科研分开来,分工教育的教师除了编写教材外不得经营“自留地”搞科研。这又是苏联“老大哥”祸害我们的一条锁链,却被中国奉为圭臬。如果科大也这么规定,方励之根本就出不来,他的教育任务也很重,教过普通物理、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天体物理……,与此同时他仍写出了大量高品质论文。方励之和黄昆先生的论文都属理论物理范畴,不需要实验或他人协作,是可以独自完成的(当然理论需被实验验证后,才能为世人承认)。对北大那么严厉,也有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他自认为一九一九年在北大受过侮辱,因而御赐北大“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此外,恐怕和黄昆先生自己的“组织性”太强也有关系吧,他不敢越雷池一步。
钱临照先生、王竹溪先生、李荫远先生、和李同岁的黄昆先生,他们放弃国外舒适生活,满腔热情回来报效祖国,对中华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原来他们的生活也不舒畅!遑论普通的物理工作者、普通的百姓。这些老先生们和某些演员例如演《建党伟业》的一些人相比谁爱国?假洋鬼子们赚了国人的钱到国外花,当局竟用这些外国人来教育中国人要“爱中国”!不过,和政治舞台上的演员相比,文艺舞台上的演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大群贪官污吏把大量大量的中国民脂民膏搬运到了国外,比一九八九年严重得多,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富了外国。为什么长期允许把家人送去国外的“裸官”们教育他治下的百姓“爱国”?把“裸官”赶下台去!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外籍院士李政道
另一位华人物理大家李政道,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一九五六年刊出合署论文并经实验证实后,第二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提出一年即获奖,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极为罕见,因为论文更新了对物质世界的基本认识。
美国物理学界是清楚的,微观物质世界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这一崭新观念是李政道提出的,对这一历史事实的叙述至今还可在多名诺奖得主及吴健雄(曾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等人的文章中查阅到。李萌发了不守恒理念后立即授意从事重粒子衰变的实验物理组(其中有三人后来获得了一九八八年诺贝尔物理奖)重新分析实验资料,从而证实了李的理论。这之后,杨振宁接受了不守恒的宇称理念(Parity idea),凑上来要求李不要发表己写论文,说可以在数学上把文章写得漂亮些,并扩大到分析轻粒子等基本粒子的衰变过程以表明宇称不守恒的普适性。在李政道的建议下吴健雄设计进行了最稳定的轻粒子即中子的贝塔衰变(β衰变)实验,这个著名实验最终完成了对宇称不守恒的充分证实。接受诺贝尔奖时杨以年长为由先予领取(论文署名是李政道在前)。获得诺奖二十五年后杨竟说两人合写的论文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宇称)文章在内。这完全违背了事实。中国大陆一些人用“政治”(例如迎合当局说“六四”等等)来模糊科学事实,以讹传讹,录用一人之说,还摆出貌似公允的样子,搅出了一潭混水。
一九四六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读书的李政道,经恩师吴大猷推荐赴美完成了学业,他是没有回国定居,但对中国的贡献实无与伦比。例如:一九八○年以来,李政道发起组织美国几十所主要大学在中国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笔者那位上课时自学梵文的同学就在一九八○年考取了李政道研究生去了美国(此人当年也被划成了右派,功课可比我好得多了);李政道用其毕生积蓄三十万美元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后来又在家乡苏州设立了奖掖中学生的“李政道奖学金”;在李政道的建议下中国设立了少年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后流动站,他建议和协助建造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接受担任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主任、北京现代物理中心(设在北大)主任、浙江现代物理中心(设在浙大)主任和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以致邓小平要当面感谢李政道,说:“ 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
一九六四年李政道将父母遗骸归葬到了苏州郊区的灵岩山南麓,二十年后建立的林昭墓地与之隔山相望。
科学无国界,尤其是不涉及“国家机密”的理论科学家,去到一个能够安心工作的国度,做出了科研成果,是对全人类作出了贡献,自然也是对故国的巨大贡献,难道不比憋屈在“爱国主义”桎梏下什么事也做不成强百倍?李政道对中国的贡献谁能否认!为什么黄昆不能既教书育人又从事科研?徒然使中国少了个诺奖得主。
比方励之年长十岁的李政道,同样是热烈的爱国者,他们都深爱着中华故国。
李淑娴是方励之的同志
李淑娴是方励之的同学,同志,贤内助。同为高中毕业生考入的北大,也在北大学生时期入了党,都是学生干部,同样功课好,又专又红。但是李淑娴划了右派,而且是在北大,比方励之就苦得多了。虽然一九五九年九月她已摘了帽,仍没有让她上讲台,而是叫她到北大物理工厂半导体车间当清洗工,强酸强碱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这位外形娇小的大姐,硬是天天上操场,用运动恢复了健康,坚强的意志令人叹服。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李淑娴才恢复教书权利,后和方励之合作出版过《力学概论》等专业书籍。
一九八二年暑期,笔者离开物理所二年后出差北京,到北大教工宿舍区的蔚秀园看望了李淑娴。那时方励之还没有调回北京,“两地关系”还没有解决,只能利用假期到北京和妻儿团聚。当时虽是暑假,方励之也不在家,他应联合国民教育科文组织的邀请到巴基斯坦给多国人员讲学去了,她家房间面积不算小,但空荡荡的,有一个五斗柜,上面放着个二喇叭收录机,说是给儿子听英语用的。我问方去讲学有报酬吗?有的,照联合国专家标准给美元,不菲,是给个人的,但方励之和以往一样把国外收入全部交公了。这和很多官员及那些“爱国主义”者比比谁爱国?
方励之是个热烈的爱国者,但是这个国家爱他吗?
在笔者印象中方励之的身体本是很好的,有国难投的沉重精神负担终致夺去了他的生命,弹性形变不易察觉,日积月累超过限度突然折断了,难道不是吗?想起了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一个归国画家的被迫害致死,他女儿说:“ 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方励之是个大爱中华故国的人,可这个国家爱他吗?!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中共第一到第五届的第一把手陈独秀说:“ 青年爱的理应是一个给他们以保障、以发展、以实现价值的国家,而非一味叫青年作牺牲、只奉献的国家。 ”“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方励之和我们那代人追求的理念也无非如是吧。
笔者在此回忆些方励之学长的点滴和关联事,“ 以给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之采择与评论。 ”(天怒人怨,要等二、三十年吗?)
如果说五十年代被划出校门的“五七”群体朦胧地看出了一党专攻的狰狞,八十年代的“ 六四 ”群体则从学校走上街头大声喊出了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的呼声,二者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良知,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他们在呐喊中逐渐坚定,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狱中说:“ 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 ”这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林昭们,方励之们,李淑娴们,王丹们,和现如今北大“叫兽”孔庆东之流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魂兮,归来哟,中华民族之魂,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李淑娴学长为方励之学长所写悼词的最后泣血曰“ 励之,看着我,伴着我,等着我! ”读至此不禁泪流满面。方励之学长,看着我们,伴着我们,等着我们!在天国里看着伴着等着我们完成你未竟的事业!
(二○一二年四月初稿,二○一二年九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