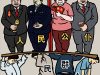那年风波后,王朔说要构思一篇新小说,我问他讲什么?他说:忍术。
是日本忍术吗?我问。
不是,是中国的。
可中国哪里有忍术?
他说,中国没有忍术这种形式,但是,忍的学问却融进了中国人骨子里。
这个忍,是忍耐的忍,也是残忍的忍。中国人不仅很能忍,而且很残忍,特别是对自己,对自己人,尤其残忍。
他的一篇小说里有句话,叫: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
在他看来,人死不是问题,活着才是问题,能屈辱地活着,才是真正的王者。
我理解他的表达,他说的那种忍,其实就是一种泼皮牛二精神、滚刀肉精神,或叫阿Q精神,拖不垮,打不烂,不屈不挠,绝不屈服。这也是一个种族生生不息,繁衍下去的理由。
举目世界,中国人的忍,恐怕是无双级别。元代,初夜给蒙古占领军,忍了;清代,剃发结辫,也忍了。
有人说,那是古代,那是汉人,不能代表中国人。
其实,当代中国人的忍应该还有所超越。你看,三年饥荒,十年艰辛探索,不是照忍?而且,五十六个民族一起忍。
经历了两次“活下去就是最高追求”的时代,基本也就没什么不能忍的了。
仅仅能忍远远不够,还得会忍,还得把忍变成一种博弈的手段,靠忍来征服敌人,那才是忍的最高境界。
他说他要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故事梗概是这样:某人比武失败,不服,但又打不过,于是,跟对方约定,咱不比武了,比忍,对方同意了。
双方的忍术从比忍耐力开始,忍耐指数不断升级,中国人始终无法战胜对手,于是,由忍耐级别升级到残忍级别。几道自残下来,眼见依然无法让对手屈服,中国忍者一怒之下,拿出终极忍术——切命根子。对方一听,傻眼了。说:你先。
中国忍者毫不含糊,挥刀就把命根子切了。
对方望之,吓个半死,立马表示服输。于是,中国忍者胜出。
活下去不是问题,能不要命根子地活下去,才是王者。
比自残,论输赢,这让我想起一个群体——天津混混儿。

早年间的天津,码头河运昌盛,谁能占住地盘,有活干,谁就能发财。于是,下层社会兴起抢地盘之风。但是,天津毕竟是租界地带,法制社会,有洋巡捕管着,胡来不行,打打杀杀,可能招致租界制裁。如果抓起来关几年,美好人生就荒废了,那不划算。
武斗不行,就来文斗。所谓文斗,就是比自残。不惊动警方,也不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
天津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对决,是在天津三岔河口某处。一块空地,架起十口铁锅,双方各出五人,跳油锅“炸果子”。“炸果子”就是炸油条,不过,这个“油条”不是面剂,是大活人。锅中注满油,下面用柴火烧,待油热冒烟,双方选手犹如点球决胜一样,轮番出场,跳进去,一个活生生的人,瞬间只剩一堆骨头。
形式文明,对决公平。最终其中一方4:3胜出。

其实,看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也应该记得其中混混儿的自残描写。
汉奸伪军司令高大成年轻时,从河北农村来到天津卫,他要和一个女混混儿抢地盘。
那是冬季,高大成找上门去,女混混儿的屋中有一个煤球炉子,炉子上坐着一壶水,高大成脚踩凳子,撸起裤腿,把铁壶拿开,用两指从通红的炉膛里,捏出一只红煤球儿,放在自己大腿上,立时“丝丝拉拉”一阵乱响,屋中飘满一股肉香,只见红煤球由红变暗,直到变白。高大成眼都没眨一下。
女混混儿看着红煤球变成白煤球,只说了俩字:认栽。地面就归了高大成。
天津混混儿太粗鄙,太野蛮,太低端。
他觉得“忍术”应该更斯文、有风度。中国忍术的最高境界在于不是战胜对手,而是战胜自己,这种忍耐和对自己的残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真正的流氓,忍要忍到无耻,狠要狠到无情。
忍到无耻,可以呼他人为爹(如石敬瑭),为爷爷(如郭沫若);狠到无情,可以杀自己的亲爹(如杨广)、亲兄弟(如李世民)。
历史是发展的,忍术文化也不例外。
对自己残忍,切自己命根子,那还算是有操守的。没操守的,就是市井做法,外面受气,回家拿孩子撒气。
在传统社会里,打孩子是自家的事,没人管。进入到现代文明,就不行了,有人会心软,打孩子过于残忍了,也会对周边人、对手形成心理震慑。厉害的,能让对方脆弱的心脏不堪忍受,向自己服软,哀告自己:别打了,看不下去了,我服你了,你说吧,怎么都行,只要别打你孩子。
这就是意志力的比拼!
当然,21世纪是文明时代,拿家人撒气的形式也文明许多,比如不施以暴力,文明地虐待,给对手看。
当然这种群体性的忍术,需要内部两方面的配合,一方要残忍,另一方要能忍,如此,才能形成震慑力。戏码方得完满,效果才能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