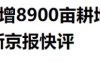最近读到金冲及先生谈百年中国复兴之路时,有一段话引出了我对“大跃进”的回忆。金说,“1958年的时候,我在复旦大学当教学科学部的副主任,接触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大跃进’提出的时候,大家都拥护。那个时候,我们到上海郊区去看,当时特别兴奋。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大家参加生产劳动建设祖国有那么一种劲头,到处都是炼钢炉,半边天都染红了,当时我想,中国人要是表现出那么一种劲头的话,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南方周末》2009年10月1日27版)我是“大跃进”的积极参加者,不过,我没有金先生那么兴奋,更没有“特别兴奋”;而“大跃进”的结果,却什么奇迹都没有能创造出来,除了极度的饥饿和倒退之外。
大跃进开始后,1958年6月,我们云南大学文科的师生到昆明茨坝工地劳动。出发前学校做了动员,我们个个在会上表态,一定要以“大跃进”的姿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劳动中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为什么个个都以同样的姿态,说同样的话?因为,“大跃进”运动正是在疾风暴雨的反右运动、交心运动之后发动的,不但师生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不能乱说乱动,就是属于“人民”这个范畴的师生,也个个言语谨慎,生怕祸从口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师生,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是众人的“反面教员”。据说这些反面教员之所以被划被整,是因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就要以他们为鉴,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按照我们那时的理解,党员领导干部传达的文件和讲的话,《人民日报》的社论,就体现了党的主张,体现了党的领导。所以,他们怎么讲,我们就怎么理解,怎么讲,怎么做。我想,这就是金冲及所说“‘大跃进’提出的时候,大家都拥护”的背景。我们在工地,强劳力拉车运土,其他挖土铲土。老师们单独在一处,做一些比较轻微的工作。说真的,个个都十分卖力,几乎没有人偷奸躲懒。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照样要过党团的组织生活,开“生活会”。会上,人人必须讲收获,讲体会,查自己的错误认识,提改进的措施。一次开会,轮到从法国回来的民族学家杨堃教授发言,他说,“收获很大!过去自己习惯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早上工作了两个钟头,到10点就要小睡一下。系上排课也要照顾我这个习惯,不能像工人农民那样起早贪黑地干。现在参加‘大跃进’,在劳动中就克服了早上想睡觉的习惯,在思想政治上也就战胜了一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觉得杨堃先生很聪明,既没有检查出什么实质性错误,又似乎在给自己上纲上线。那时的发言,我真分辨不出哪些是套话,哪些是真话。
“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大战钢铁。毛主席拍板,1958年全国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实现年产钢1070万吨。云南许多地方有更为宝贵的铜矿资源,所以云南就叫大战钢铁铜。1958年毕业,我分配到云南省临沧专区耿马县,县上又分配我到四排山区做文书;未及到职,又奉命到四排山区东坡乡参加大战钢铁铜。这时正值“大跃进”的高潮。耿马这个当时只有7万人口的少数民族众多的边疆小县,同样要积极响应。我初参加工作,一心想要努力完成任务,开个好头,首先在“大跃进”中挣一个好的表现。
东坡这一带有铜的“鸡窝矿”,矿量不大,品位甚高。耿马县钢铁铜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书记挂帅,县委第一书记王道传任总指挥,县武装部副政委李长松任副总指挥。我到东坡,大战已经开始,从各个“鸡窝矿”点挖出的矿石已经堆放在冶炼场上,成百的佤族农民正在轮流使劲拉风箱给十几个铸犁铧的化铁小炉鼓风,呼声阵阵,炉火闪烁,真是一片热气腾腾景象。王书记说,“我们没有什么铁矿,按规定,交一吨铜就顶40吨好钢!”
我在指挥部处理统计、文书,办理领导交办的工作,只要有空,我就主动去拉风箱吹小化铁炉,加栎炭炼铜。没过两天,炼铜的栎炭没有了,负责冶炼场的人连连到指挥部要栎炭。四排山各乡农民早已抽空,无法再调人来烧炭。没有燃料怎么行?王书记叫我告诉县委办公室,立即从福荣大山的拉祜族和耿宣坝子的傣族农民中,抽调800人来这里砍树烧炭。几天后,来了男男女女600多人,他们背着棉毯、衣服、罗锅、斧头,翻山越岭走了两天,按照指挥部安排,在对面大山里的森林中搭了一排排窝棚,在山脚下挖坑做窑,陆续开始砍树烧炭。好多天过去了,他们砍树很少,更没有烧出多少炭来。李副政委叫我去看看,我急急忙忙翻山越岭去看。原来,他们出工很晚,收工很早,头人贺板雅还要带领他们做佛事。
怎么回事?不是说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吗?我马上想到我已经得到的教导:这里的工作上不去,农民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就是没有开展阶级斗争,必须以大批判开路!那时时兴开“辩论会”,是推行强迫命令的好办法。我找了几个乡干部开会,布置晚上“辩论”贺板雅。“辩论”什么呢?我们商量好,他既然当过头人,必定欺压过群众。那么,就从他历史上欺压百姓批到他在工地上做佛事,拖砍树烧炭的后腿,破坏“大跃进”。晚上挂汽灯,几百人围坐泥地上,我作了简短的主题讲话,接着就是几个乡干部大声指责贺板雅。为了烘托气氛,调动情绪,当中不断有人带头呼口号,还有几个人把贺板雅捉到会场中央站着,指着鼻子骂。
第二天,砍树的进度果然大大加快了。我回到指挥部复命。过几天,冶炼场上还是说燃料不足。烧了那么多炭,怎么能不足?他们给我看:运来的都是火力不强、不耐烧的桴炭,不是栎炭。我马上跑到那边山上去。原来,福荣和耿宣新来的农民没有做窑,而是挖方坑,烧明火,这样当然省时、省工、省力,却只能有桴炭!他们摇着头说,我们不会做窑,我们只能烧这种炭!我毫无办法。
回到指挥部,接着有区供销社和卫生所的人来找我:“邹秘书,你们要留一些大树呀。现在是栎树、松树一起砍,大树小树一起砍,以后我们盖房子在附近就找不到木料了。”我叫福荣区各乡的干部注意留下一些大树,其他抓紧砍;山脚下做窑,一定要烧栎炭。不过一个月,两个山头茂密的森林就被推了个光头,在秋风里露出一片片黄绿的杂草。
12月底,上面通知我们暂停大战钢铁铜,让各乡农民赶快回家去搞秋收。农民一听,立即兴奋起来,马上走了。我们指挥部人员就地储存了化铁炉,抛弃了烧炭窑以及砍伐下来还没有用过的木材,撤回各自的单位。回到县城,王书记面有喜色地说,“全县搞了1.9吨铜,大块小块都是敲得当当响的真铜,全专区第一。”后来我到临沧,才知道我们县比较老实,真正是在炼铜。其他地方大战出来的,是黑糊糊的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用的“冰铜”。
1959年秋我回乡探亲,在重庆江北相国寺重钢四厂看望当车间技术员的表哥。厂里堆放着许多钢锭。我问,你们就是用这些钢锭轧钢材吗?他说,不行,这些都是各地报了喜以后送来的,高硫高磷,怎么轧?我说,我见到那些把好好的铁门、铁锅砸了炼出来的“钢”,还不如这些钢锭呢。表哥说,现在反右倾,你不要乱说话,谨防自找麻烦。离开这个钢厂,想到我参加的大战钢铁铜,想到渴望回家收割庄稼的各族农民,确实怎么也兴奋不起来。
二十多年过去了。1985年我出差到耿马县,还到下面各个乡镇去走了一圈。县委机关的、乡镇的干部几乎都不认识我,但他们知道我曾经在这里工作过,还能说几句佤话,对我特别亲热。县委领导问我,这些年来,你看什么变化最突出。我说,公路多了,电灯亮了,大楼多了,就是森林少了。森林少,也有我的责任。“大跃进”的时候,我在这里十分愚蠢地犯过一个错误,把东坡两个山头的森林砍光了,真对不起。他们笑笑,“这不是交学费吗?不知道以后还交不交!”
《南方周末》201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