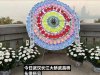一个悲痛的消息,我竟不想告知人们:
《上海文艺》杂志的康康先生走了。
阳后白血病。
突然得像:一分钟前他在微信里传来自测的两条杠,一分钟后,变成最简洁的讣告。
我对他的尊重,也许他都没感受得那么深。
男人之间不善表达,不必表达。
只有死后……
只有醉后,才知酒好。
这几年走了太多好人,才子,有趣之人……深觉世间寡淡了。
有人无真才华,无真性情,明明有血有肉,非活得跟蜡像馆里的站桩似的。不嫌累,不怕费腰。
而康康是正直、有趣、懂文学的,重要的是坚守孩提心态。我俩曾在微信深夜胡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压抑的作品,那句“在一切物种里,胡扯是唯有人类才拥有的特权,通过胡扯,人类得到真理”,竟让我俩笑得像神经病。
正是上海封城时,闹烟荒,他就在微信里委屈吼叫:上海怎么可以让我没烟抽,怎么可以,还是上海吗!
此声,余烟袅袅。
康康的才识、刚直,以及上海老男人的冷幽默,是我热爱上海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记孤傲的老克朗。
我热爱上海,只因为热爱那里某几个活生生的人而已。
亲爱的上海朋友,保持联系及失联的,尽量好好活着,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聊到肉蒲团再聊到上海冷风中打桩模子的朋友,不多了。
一个不好的现象发生在最近:好人不长命,坏人不偿命。
加倍珍惜自己。
近几年走了很多老友,借用李煜致兄弟的一个句子献给他们: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谁帮我带转一小笔份子钱。挽联就写:
康康从未迟到,只是早退了。
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