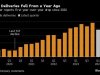我敬爱的父亲大人、爸爸郭海珍于北京时间2023年8月18日上午9时因肺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与我们永别了。他享年86岁。作为远在美国的儿子,我首先对不能回故国、家乡尽儿子之孝万分愧疚,也对自己在父亲多次重病、尤其是在弥留之际没有尽床榻服侍之孝羞愧难当、痛心疾首。然而,父亲却对我一直充满慈爱关心,一直惦记着我这个远在异国他乡、没有尽孝的儿子。在他去世前一小时,我携妻子和两个女儿一一向他视频问好后,他安详离去。他那时已经无法讲话,但我看出他对我们所说的话表现出称心满意。
1938年8月8日,父亲出生于青海省平安县洪水泉乡,与尊者达赖喇嘛的家乡非常靠近,此地离省会西宁也非常偏远。父亲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6岁年纪就从偏僻的农村考入西宁,就读当时来说青海省一流的高等学府:青海师专。从师专毕业后,他做了一辈子的教师,工作认真勤恳、兢兢业业、为人师表、教诲不倦,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可以说桃李满天下。在教育工作的中期,他成为了一名中学校长。作为校长,他清政廉洁、宽严相济,受到同事和教育部门的拥戴和称赞,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声望与美誉。我的脑海里至今还浮现出父亲作为校长讲课、讲话的音容笑貌、翩翩风度。父亲特别注重仪表仪容、注重着装的干净整洁得体,所以他一生给周围的人留下了气质高雅、卓尔不群的知识分子的美好形象。
父亲在家教上对子女们管教严厉,对我们的学习都有很高的期望与要求。尤其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父亲对我望子成龙,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精心培养我。他给幼小的我讲历史故事、文学名家,训练我的写作能力。除了学校作业外,他布置了很多游记、散文作业给我,我们一出去旅游,就回来写游记,以至于我不愿意再出去旅游。但是这种强化训练让我的写作能力在很小的时候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我人生的发展和事业成就产生了巨大的裨益。父亲也非常注重培养我们的情操道德,几乎每个周末,他带我们到大河边,与大自然天人合一、净化心灵。父亲为人诚实诚恳,他经常教导子女们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坑害、欺负他人。他对我也经常讲中国历史上的善恶是非,让我从小就具有了嫉恶如仇的正义感。
由于父亲从小的栽培并在各个学科打下的坚实基础,1990年,我最终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这让父亲非常高兴。但是我到北京后,由于知识面的扩大和六四的冲击,终于走上了一条与父亲不同的道路。父亲期望我能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其实按照人大哲学系毕业生的常规职业生涯,我会完全满足父亲的心愿。但是我却走上了一条叛逆的道路,誓与政治强权对抗到底,最终不得不在美国发展。我在读大学后期的一系列思想行为,以及没出校门就进牢门,最终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三年半的残酷事实,彻底地毁灭了父亲对我的殷切期望,深深地伤害了父亲对我的拳拳爱心,我的遭遇也使父亲和整个家庭受到空前的伤害和打击,整个家庭风雨飘摇、几乎粉碎,而父亲也因为我的事情在精神上产生了严重的抑郁症状。我为我的所作所为,向父亲作过多次的道歉,今天还想再次地向父亲说声抱歉,我为当年自己行动抉择时毫不考虑父亲的期望和对家庭的影响而表达歉意。
2008年我远走美国的举动,也让父亲内心非常挣扎,痛苦异常,他知道这一走也许永远会不了面。虽然此后我们通过视频多次见面,但永不能会面的结局却是由我铸成的铁的事实。自这几年新冠疫情以来,父亲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尤其是肺部感染,让他失去了一个肺的功能,并开始经常吐血。而在父亲最需要儿子在床榻前尽孝服侍的时候,我却不在他身边、不在床前。对此我深感愧疚、羞愧难当,内心经常吞下悔恨内疚的泪水。按照中国传统伦理,我的确就是大不孝之子,父老乡亲们再怎样责骂我也不过分。
父亲自己是个大孝子,祖父去世于1960年代的大饥荒中,而且死不见尸。我清楚记得父亲到老家用神柱代替祖父身体,迁移神柱到我们居住的湟中多巴镇一带,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让祖父与祖母安葬在一起。我们小时候,每年清明节、正月初三,父亲都要带着我们去上坟、烧纸。父亲的孝顺是我的楷模,但我却完全不及他的孝德,内心只有自责。
父亲一生也历经苦难、饱经风霜,他经历了多次的政治运动,让他变得非常的小心谨慎、委曲求全。他是一个善良正直、谨小慎微的人,面对狂暴的强权,处在基层的柔弱的知识分子,恐惧多于憎恶,无可奈何多于批评。我清楚记得他有次告诉我,他年轻时候经历毛泽东的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的阳谋后,惊恐万状,因为他绝对没有想到一个国家政府、一个英明领袖竟然公开撕毁诺言、用赤裸裸的欺骗将上当的人全部一网打尽。反右运动彻底颠覆了父亲对中共的看法,他看清了中共狰狞可怕的邪恶面目。从那时起,父亲对共产党没有一点好感,这主要是出于一个普通人的基本良知和安全感,他深感中共党内党外充斥着厚黑欺诈、残酷野蛮、蝇营狗苟、血腥斗争,将基本的中国人伦摧残殆尽,随时带给社会恐惧和危险。他一辈子也没有入党,有关部门要叫他作镇长、教育局副局长等,他都婉拒。在他眼里,中共就是一头野蛮残暴的巨兽、也如肆虐横行的龙卷风,柔弱无助的国人被它任意蹂躏、肆意侮辱。我刚懂事时就遇到四人帮被打倒,我能体会到父辈们当时在恐惧无助、饱受摧残中的少许兴奋。
改革开放和对教师待遇的提高,让父亲看到了希望,他不再在我前面抨击中共,甚至开始质疑我是不是要求过高。他经常感叹我:“生在福中不知福”,要是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整人、人斗人,就不会对现实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是,自习近平上台后,尤其是中共病毒肆虐、疫情清零政策实施以来,父亲本能地感到那股残酷野蛮、视人民如草芥的气息又开始充斥整个中国大地。无限期的隔离,生活的高度不便,天寒地冻中高龄如父母,也被驱赶去检测、去打疫苗。父亲感到他年轻时候经历过的野蛮巨兽、狂暴飓风,又开始残害践踏每一个中国人的健康、自由、尊严乃至生命。父亲自己也不幸感染肺炎,在疫情期间入医院多次,虽被抢救过来,但肺部感染却在他治愈后再次复发、不断扩大,终于夺走了他的生命。
父亲最终死于中共野蛮残暴的魔爪之下,但是跟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父亲对强权选择了沉默,因为柔弱无助的他们知道,反抗只会导致沉重的代价。他曾给我讲他上师专时有个非常优秀的同学被捕,原因是组织了个地下民主党来反对共产党,结果这个同学被判了无期徒刑。学校组织学生们还旁听了这次公审。父亲觉得那位同学非常可惜。父亲多次曾对我说,这辈子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被打成右派,算是在政治运动中幸存了下来。跟父亲不一样,我没有选择沉默,我从小就感到父辈们过得太窝囊,我们应该跟他们有所区别。不知是我的年少轻狂还是天生叛逆,我走向了一条与父亲相反的道路,却也因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在中共监狱里,当我切切实实地体验到中共铁拳的野蛮残暴、无情粗鄙后,终于理解了父辈们为什么那么谨小慎微、那么胆小怕事⋯⋯
父亲与我们永别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带着几个孩子在夕阳下、大河边散步的诗意画面,他40岁出头当中学校长时在全校师生前讲话时的英俊潇洒,他年轻时打乒乓球的矫健身躯,他暑假到大学宿舍来探望我时的淳朴慈爱,他看到我在北京写作出版的多部著作时的满意神情,他重病卧床时在微信群里给我的留言留音,一一都历历在目,如烙印铭刻在我的心上。父亲在弥留之际形容枯槁,但最后非常清晰地对我说的话至今萦绕在我耳边:“我们会再见面,再谈话”。这最后的话,也许指的是他和我将来要在天堂相逢了。
爸爸一路走好,儿子宝胜实在对不起您。您安息吧,我们子女们会好好照顾妈妈,永远纪念您对我们的无限恩情。

郭海珍遗照(郭宝胜提供)
不孝儿郭宝胜
2003年8月20日于美国维吉尼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