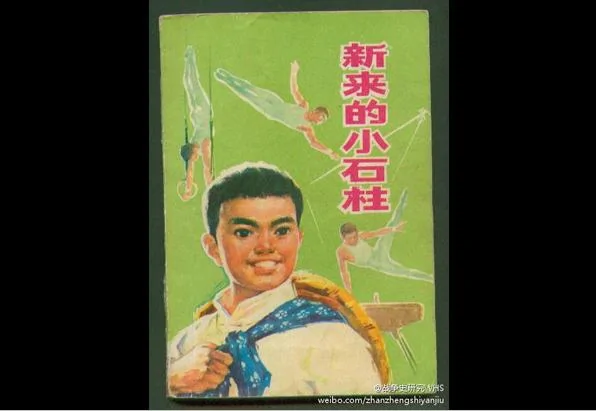1966年底,轰轰烈烈的大串联已经近了尾声,我们小学生也陆续停了课。没完没了的批斗会加上歇斯底里的喊口号实在让人疲惫厌倦,小城的日子变得无味难熬。等过了农忙季节,有四个玩得好的闺蜜们不甘心蹲在家里看着中学生们在全中国到处跑,开始密谋步行外出串联,想要看看远方的世界。她们一起来动员我,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跟着爸爸去过别的县,算是出过远门,而且会看地图、会用油印机,有一个朋友字写得好,知道怎么刻蜡纸。(当时闹革命这是必备技能。)
几个女孩子最大的不满十三岁,最小的是我,将满十一岁,居然雄心勃勃,要步行串联去北京,而且不打算邀请男生同行。那时候,男生和女生同桌都要划“三八线”的,如果一起出行,在小镇子上绝对骇人听闻。我们想给自己的队伍起名“半边天”红卫兵小队,后来因为资金问题,没有做成旗子把队名写上去。
我不知道她们几个是怎么说服的家里人,我自己出门却很容易,因为我的父母被各自的学校困在单位里挨斗或者批斗别人,对我的教育和日常生活鞭长莫及,我只要跟外婆讲学校组织外出就可以交待了。
我从小乖巧,外婆很信任我,几乎称得上是有求必应。她给我一块钱做零花,还有两斤粮票,用白毛巾裹了三个馒头,把舅舅下地带的水壶也装上了。我穿着表姐做的布鞋,家染的草绿棉布罩衣,书包里带了小红书和地图,一大早就兴头头冲到县城北关外的公路口与小姐妹们会合。萍萍的哥哥赞助了几个“井冈山”红袖套,我们戴上之后互相看看都很满意,自觉很神气地踏上了北上的乡村公路。田野里的庄稼都收完了,路边的白杨树落光了叶子,空旷的土地和远处秃秃的乔山实在算不得美景,但是空气中的“自由”感觉,却让我们愉悦无比。
正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附近村庄的土墙都刷上了各色宣传口号,牛栏猪圈甚至茅厕的外面也都画了红太阳,贴上了大标语,远远望去,还是花花绿绿地有些意思。路上不时有人骑自行车载着粮食口袋或是自家小孩子悠然擦过身旁,我们挺起胸脯,唱着歌向路人秀着心底的自豪;尽管旁边拉车的牛随意撇下几堆粪便,顺风刮过来一阵不好形容的气味,平时爱干净的女孩子们也没有在意,还朝着赶车的大爷挥了挥手……
第一站,我们打算赶到本县最北面的杨谈村,因为1965年我父亲带临汾地区教干校学生在那里接受半年“又红又专”再教育时,我也跟去住过一个多星期。当时住的是老乡家里的土炕,房东家的小女儿比我大一岁,带着我满村子转过。杨谈村没有大寨那么受全国追捧,村长王德合却也是远近闻名的国家级劳动模范,村子并不闭塞,常有下放干部、插队学生、参观学习代表什么的来来往往,所以我敢带大家去那里,起码有地方容身。
我们风尘仆仆走了一天,路上啃完了自带的干粮,黄昏的时候终于进了村。在大队部凭着几个红袖章住上了一间招待所,不收费也不要介绍信,还提供了免费的馒头小米粥配萝卜丝做晚饭。原来红卫兵出来串联可以随便吃住是真的!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吃过饭后很想出去转一转,参加村里的革命活动。
半山腰的山村,天黑得早,舍得开电灯的人家不多,在门口张望一下,半边山挡住了星空,山风吹得四处暗影憧憧,深不可测的夜色似乎藏了无数的秘密。我们有些胆怯,缩回房间借口疲劳挤在炕上说话,小声唱个“抬头望见北斗星”给自己壮胆,这时候才知道,其实我们真没有自己事先以为的那么勇敢无畏,心里隐隐有些后悔,可是又没人肯说出口。
黄土高原上的小山村,水是紧缺物品。我头年去的时候,知道村子里的井很深,摇水的辘轳要被绳子缠满好几层才能绞起一桶水,没有力气的妇孺必须得两个人互相配合,才不至于中途失手。洗洗刷刷在这里,绝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走了一天路,黄土满面,只有炕头两个热水瓶里的一点水,还要顾着喝,只好用半杯水打湿毛巾,凑合擦了一把。至于衣服上的土,屋里有布条扎的“甩子”(拂尘),用它在院子里抽打几下就算清理过啦。
紧紧关上房门,一夜无话。等早上睁开眼睛,阳光已经照透了窗纸,赶走了黑暗和恐惧。我们收拾一番,又成了神气的“红小将”。喝过当早饭的棒子面糊糊,我带着大家去参观村里的集体养猪场,又看了山坡上的花椒树和梯田,都是去年房东小姐姐领我去过的地方。到了下午,我已经想不出节目了,几个人枯坐台阶上发了几分钟呆,却看见一队七八个大学生举着旗子,背着背包,戴着绿军帽,摇摇摆摆走进了大队部。我们眼睛一亮,立刻跟着进去攀谈一番。
大学生们很友善,言谈中听出我们小学还没有毕业,判定我们是从家里“私逃”出来见世面的,却没有戳破我们。下午相跟着一起去听辩论会,串联的大学生们在围拢的社员面前,大谈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有听没有懂,只能作崇拜状地望着他们熬时间,那效果就像是十多年后我在复旦校园见识过的低年级女生听高年级文科男生侃尼采和萨特的情景(一笑)。
大学生红卫兵还给我们分派了任务:刻印传单。大队部有蜡纸、钢板和笔,内容就是文革十六条和伟人语录。我们有了用武之地,不再急着离开村子北上。第三天推了一上午的油墨磙子,五颜六色的传单堆满了一桌。午饭时我们正在讨论接下来怎样到襄汾去搭乘火车前往太原,有两个戴帽徽和红领章的军人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想去北京串联的红小将?伙伴答曰“是”,而我差点脱口说“解放军叔叔好!”紧急刹车堵住嘴巴,憋得脸都红了。
军人说他们有任务开吉普车到临汾,愿意捎小将们一程送我们去那里的火车站。同桌吃饭的大学生立刻撺掇我们答应。这样的好机会当然不能放弃呀!车马上就要出发,我们只来得及冲到房间里抓起一摞印好的传单和自己的背包,跟微笑着的大学生们摆手告别后,急急忙忙爬进了军用吉普,四个人挤坐在后排,当然不会有安全带。我们几个平时连公共汽车都极少坐,都是生平第一次坐“小车”,兴奋到脑袋发晕,恨不得放声高歌宣泄激动的心情,根本就没有留意到一丝蹊跷。
出了杨谈村,一路下坡,车走得很快。每经过一个村子,我们就把车窗摇开一条缝,把花花绿绿的传单塞出去,引得一群穿开裆裤的孩子们追着吉普车奔跑跳跃,抢着去捡飞舞的传单。我们虽然知道这些孩子未见得会去阅读传单上的文字,也许最终只是拿去做了引火的纸媒甚至厕所用纸,心里还是充满成就感。“撒传单”的活动被各种文学作品、电影戏剧之类存入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本身早就成为一种“革命”的仪式,不会有人质疑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快乐的时间总是飞速消失。车子经过两个村庄之后,我觉得窗外的景色越来越面熟,不由心下狐疑,这是去哪儿啊?然而,军事任务似乎不能容人打听,只好沉默等待,连撒传单的心劲儿也没有了。半个小时后,真的看见到了我们前天离开,再熟悉不过的县城北关路口,车停下来,两位军人客气地请我们下车回家,说是任务有变,今天不走了!!!我能看出他们嘴角难掩的笑意,终于彻底明白:我们被哄骗着送回家了!解放军也不能信任了吗?让这件事惊呆的几个小姑娘,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得谢过解放军,泱泱地各自回家。
我见到外婆,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一块钱和二斤粮票,原封没动地交还给了她。外婆吓了一跳,以为我不舍得花钱买饭吃,三天只就着凉开水啃了三个馍馍,心疼了我半天。我心头惭愧,好几年都没有跟家里人提起这次虎头蛇尾的串联。
2022-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