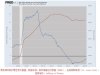重庆的冬天,比较阴冷,或者说,是把阴冷演绎到极致的冷。比如说我太太头一回来重庆,记得户外有12度,然后没过两天,她竟然生了冻疮。北京则比较干冷,小风儿杀气腾腾,但是,重要的事情只说一遍,“羽绒服里莫要穿毛衣”,否则,一进屋你就像搬过砖一样汗流夹背。波士顿还要不一样一些,如果大冬天显示有12度,还没小风儿,然后又出大太阳的话,阳光直射半小时,能把你丫烤死。
家里93岁老爷子的身体,新冠阳过之后感觉是一年不如一年了。2022年之前,一天能走一万步,每天上街逛两回,各种凑热闹,打望美女,乐在其中。阳了之后,每天走得了两百米,赶紧停下来大喘气,八抬大轿——我推的轮椅,马上接驾。
这个冬天,左脚莫名肿痛,一个星期去了三回医院,仍然查不出个所以然,似乎什么都是好的,似乎好了一些,比如,不怎么痛了,但是,仍然肿着。腊月二十九,我们老家的领导关心民众疾苦,已经把老中医带来了家里,看了一个多小时,开了药,罗列了一些注意事项。
本来希望他的左脚可以和重庆的天气一样,在正月里好起来,现在看来,乐观了一点,老祖宗讲的“病去如抽丝”,不算瞎说。
大年初一的下午,太阳出来了,推着他去江边逛了一大圈。一个固定打卡的地点,又让他失望了,镇上唯一的报刊亭,年初一不开门。老头每天都要买报纸看,阅读量巨大。亭子里的老板大老远一看到老老邱同志,像打了鸡血一样冲出来:
“客户你好,《环球时报》、《报刊文摘》、《新周报》,一共7块钱。”
这个《新周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报纸。
总之,大年初一这一天,精神食粮没有买到,左脚仍然肿着。逛街逛到一半,革命的老同志已经在轮椅上睡着了。
我们小镇上,有一条黄溪河,涓涓细流,在此地汇入长江。童年的时候,黄溪河不是细流,是一条小河,夏天河水会涨起来,淹没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石头,父亲和母亲会轮流搀扶我们过河去小学上课。
那个时候,母亲是我的右脚,父亲是我的左脚。现在,右脚已经永远离开我了,左脚肿痛着。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老头在轮椅上醒过来,说:
“他妈滴,还是美国人在搞鬼,又是贸易战,又是病毒,又搞垮我们的股市,还把我的左腿搞成恁个样子。”
如此这般,“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讲述了一千遍的故事又讲了一千零一遍:抗美援越的时候,美国人就用了气象武器,搞得天天下雨,泥泞不堪,我们支援的物资,根本送不上去。我和我的老兄弟小徐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都表示没有听过,老头并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听过,说,你们懂个屁。
如果按照时下有理不“杠”非君子,三观不对盘立即拉黑的思路,我和我家90后这父子关系迟早得陷入僵局。
不过,大年初一这一天,天儿暖洋洋的,而且为了他的左脚,已经搞到我的左膝盖又胀又疼,但是一切以欢乐祥和为主基调,我提出我俩一起演唱一首他最热爱的《红梅赞》。
“来,我先起个头:
红梅花儿开,
朵朵放光彩……唱!”
“红梅花儿开,
朵朵放光彩,
昂首怒放花万朵,
香飘云天外。
唤醒百花齐开放,
高歌欢庆新春来,新春来!”
老头说:“不唱了,脚胀!”
我没忍住顶了一句嘴,“要我说,你的这个左脚,肯定跟美国人没得关系,只能叫‘人穷怪屋基,瓦漏怪桷子稀’。”这是重庆言子儿,土话,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大约是说,自己不找自己的原因老是把自己不幸的原因归结到其他因素上。
这下捅了马蜂窝,90后在轮椅上大声批评:“你们这些小崽儿,不读书不看报,天天刷手机,迟早吃大亏。”
我再也不敢吭一声,想想,我们不仅读书看报,而且还办过报,只是比较难搞,越搞越难,快要办出神经病来了,只能作罢。
故乡的长江边放了很多免费的乒乓球桌,让老百姓锻练身体,老头这两年看到那些活蹦乱跳的中老年老头老太,满腔悲愤,羡慕不已。
他观看了一刻钟总结说:“中美关系,小球推动大球,乒乓球也是有过大贡献的呦!”
如此这般,我又必须得承认,我家90后的三观,似乎又并不偏颇。
我说:“我的老同事采访过中美乒乓外交的见证者,其中有一个细节,说是那个最重要的美国球员叫科恩的,是个嬉皮士,他在北京访问的时候,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了一个预案外的问题,他问周总理,如何看待美国的嬉皮士运动?周总理回答说,年轻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可能会作出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最终他们都会选择真理。”
大年初一的这一天,我讲的这个小故事,说明我读书看报,让老头琢磨了好久,表示很有意思。
回家的时候,我们住的这幢楼,进大门前有个小坡,外加一扇随时自动关上的大门,推轮椅的人会非常不便,大门里面,有两桌打麻将的退休老太太,每天输赢10块钱左右,乐此不疲。
我推着老父亲一到门口,总会有一个80岁左右的老太站起来,帮我们拉着门,几个月如一日,我们说了一百多遍谢谢。
有一回我实在没忍住:
“这个雷锋老太是咋回事?又不是咱家佣人?”
老头说:“哦,那是以前我们副县长的太太呢。她年轻的时候,就是还没嫁给副县长的时候,有点经济上的事,我就是负责侦办的人,事情不大,都没什么钱,东西也退回了,我就找她谈了一次,给上头也汇报、担保了,我让她不要有负担,好好工作。”
我说:“你担保有个屁用。”
老头说:“啷个没得用,人家后来好多年都是先进,嫁的先生也很有出息,还当了副县长,两个娃儿都是大学生。有些事情,重一点,毁别人一辈子,轻一点,救别人一生。”
我说:“现在流行的话,枪口抬高一厘米,你听得懂不?”
老头说:“听不懂,抬高一厘米鸟不是飞俅了。”
老太太有一天在楼下碰到我,说老头的左脚肿痛哦,我说去看了一回,好像问题不大。老太很震惊,“还问题不大,你要高度重视,你们老头是从来不说痛的人,他都说痛,肯定嘿痛!”
“以前反右的时候,你老爸的同事差点被打成右派,上面喊你老爸检举他,你们老头说,这个人没得问题,上面说,你不检举他,你就有问题。你们老头说,‘他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其他无可奉告。’你老爸后来吃了不少苦头哦,不过还好,最后两个人都没打成右派。”
如此这般,我们老头的三观是个什么底色,“无可奉告”。
我在新年的时候帮他整理他读的报纸,实在太多了,也找不到收旧报纸的人,只能堆在客厅的角落里。有一天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连续有几天的报纸,都折在同一个内容上:自由前进党候选人哈维尔·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阿根廷股市狂飚、全国大罢工考验米莱新政……
某一天轮椅出行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
“你看得懂一个叫米莱的人?”
他云里雾里:“啥子?”
我说:“哈维尔·米莱,阿根廷的新总统,他在达沃斯喊了一句口号:‘自由万岁,妈的。’”
老头又想了很久,突然有点小兴奋:“这个人值得研究哦。”
我说:“研究个屁,他是美国人的走狗哦。”
这回轮到老头没劲了:“那倒是,货币都用美元了。”
正是这个莫名奇妙的话题,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成为了我俩在逛街的时候偶尔可以聊聊天,互动一下的动力,事实上我发现,他根本就是前读后忘记,但是似乎有什么神秘力量让他非常关心这个“疯子”的一举一动,事实上,还推动了我大量阅读有关米莱的几乎所有内容。
有一天经过银行门口,我说:“米莱有一句竞选口号,‘我要炸掉中央银行,这不是一个隐喻,这是字面意思。‘要得不,疯狂不?”
老头说:“字面意思是个啷个意思?”
我说:“就是真的炸掉,或者,高度准确地说,叫摧毁。”
老头说:“因为阿根廷通货膨胀噻,民不聊生,钱不值钱,国民党反动派倒台的时候,我们买他妈一斤米要几捆钱。”
有一天刷短视频,看到一个金教授,在台上讲,南美洲总是提供教训,非常高兴米莱再次提供一个教训。我把短视频给老头看,他看了一万年,耳朵也听不见,饶有兴趣地贴在右耳边听了半天。
我说:“一分钟的短视频,你硬是看到我把三国演义都读完了。”
老头把手机还给我说:
“投机分子。”
我说:“你这个老公安思想不对头哦。”
老头说:“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啷个刚开始就下结论是教训。”
老头说:“投机分子的特点就是你把他带到派出所,裤裆里面来一脚,他该说的不该说的、真的假的全部说了。”
我忍不住笑起来,破例给他买了麦当劳冰淇淋。
老头吃着冰淇淋跟我说:“你说的这个人叫啥子,我又搞忘了。”
“米莱!唉,跟你讲话太累了,麻俅烦。”
“还有你说的那个经济学家,叫啥子克?”
“哈耶克,算了,你吃冰淇淋,要化了。”
“哈耶克,米莱,人就是要学习,不学习要落后。”
老头的甜食整完了想起来一个话题,说:“你晓得不,米莱这个疯娃儿,以前是踢足球的,后来发现足球救不了国,去学经济学,当总统,救国,我觉得了不起,年轻人要有报国救国的志向。”
我说:“那万一他反而害了国呢?可能性不会低于百分之五十。”
老头说:“对头!同意你说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主席讲的这个沧桑,就是不断改革、不断发展、不断前进,这是必然规律。”
我说:“厉害了我的老头!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子。”
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企业老总的电话,讲了很大胆的思路,和现在热衷的企业出海有关,我琢磨了半天说:“不急不急,三思而后行。”
老头推开门进来,说:
“我觉得这个叫米莱的人还有一个特点,有点像重庆崽儿,做事情果断,不拖泥带水,你觉得呢?阿根廷这个地方,报纸上说的,叫做国难当头。国难当头的时候,容不得三思而后行。”
我说:“重要的事情说两点,第一,不要半夜三更偷听我打电话;第二,朋友要做大事,我先冷静分析,不拱火,没得错。”
老头说:“那是那是,我的听力不好,没有偷听,是你讲话声音大。”
我在新年的晚上乱翻书,钱穆注《论语》,在“三思而行”下面,注曰:“事有贵于刚决,多思转多私。”
黄溪河流入长江的地方,总是有很多人钓鱼,我还经过一家鱼具店,生意不错,叫“忘不钓”,无语。
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我和朋友汤总去姐姐工作的绢纺厂玩,她的一个老头同事嫌我们太吵,把我们带到旁边的鱼塘钓鱼,钓了一个下午,一条鱼都没钓上来,汤总没耐心了,扑通跳进水里,东游西窜,冒出头来说:
“日你妈里面根本就没有鱼。”
要钓鱼首先要确认水里有鱼,据说是芒格说的,反正鲁迅肯定没说过。我想哈维尔·米莱叫嚣“国家是魔鬼发明的,上帝的制度是自由市场”,是不是他发现水下已经没有鱼了。
关于哈维尔·米莱的话题,在黄溪河边,渐渐告一段落,天气越来越暖和,老头的左脚,慢慢有了转机。甚至,在我离开重庆的时候,我还预约了阿根廷的作者,为我们带来“自由万岁”的米莱后续的内容。
在我家90后那颗“什么都是美国人干的”的心里,似乎,还埋着“真理万岁”、“报国万岁”的三观。
我们还未到互相拉黑的程度。
腊月二十九的下午,去重庆巴南区的中医院帮父亲拿好中药,想起明天就过年了,应该去南山看看母亲。
天下着小雨,叫了辆滴滴专车,山路弯弯,开了一半,师傅说:“你定位在西南门,你要去的这个南山龙园小区,还有别的门不?”
我突然有点小尴尬:“师傅,我要去的这个地方,不是小区,是一片墓园,你要是不想去的话,我可以换一辆车。”
师傅说:“哦,这样啊,下雨,天冷,没事的,你去好也叫不到车,我在那边等你。”
我在南山龙园的半山腰上呆了半个小时,把这一年所有的事都和母亲讲了一遍。雨越下越大,墓碑前放的白色小花,心事重重地散开来,像这一年无数个哀伤的碎片。
重新把花扎好,压在一块石头下面,我说:“妈,我回去了。”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说:“爸,我去看过我妈了。”
老头说:“哦。山上还好不?”
我说:“山上有啥好不好。山上的人只希望山下的人好。”
他说:“那倒是,你看我这个左脚,南山也爬不上去,心有不甘啊!”
记得前年底母亲在ICU里去世的时候,我还在国外,我的老同事去家里告诉了他,几个同事作好了所有准备,甚至连救护车都安排了,老头听了看着窗外,沉默了好久,回头说:
“我晓得了,辛苦你们了。”
这是疫情三年他遭到的第二次沉重打击。
2020年初,我的60岁的哥哥心梗去世。老头有一周都没怎么说话,有一天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
“文化人,问你一个问题,老公死了的女人和老婆死了的男人,都有一个特定的称呼,但是娃儿死了的人却没有,是不是?”
我说:“没有。”

邱兵,重庆巴南人,李植芳老师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