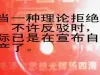2004年,毛泽东生前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历时三年写好的回忆录《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经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等单位整整审核了四个月,最后决定:该书极不宜发表!
毛泽东的女儿愿出一百万人民币买断版权,阻止出版,不但说明张玉凤写的是实情,而且里面有毛的不为人知的丑闻。
据一个曾去聆听毛泽东训教的高官回忆说,那天为了一点儿事,张玉凤和毛泽东绊起嘴来,最后张玉凤一边往外走一边大发雷霆,对着「红太阳」狂吼道:你去死吧!当时把毛气的瑟瑟发抖,那位官员在旁边吓的目瞪口呆,以为张玉凤将大祸临头,结果事后什么事也没发生。
还有一次,毛张俩口子绊嘴,各自说了一些过火的话,后来张玉凤赌气说:谁反悔,谁是狗!每次吵嘴张玉凤都不说软乎话,反悔的每次都是毛泽东。毛气的在纸上反复写道:她骂我是狗!她骂我是狗!她骂我是狗!……以此解压。

邵华与妈妈张文秋、姐姐思齐、妹妹少林50年代
初在北京。这一家有几个女人共同侍候过毛?
中共的高层机密太多了,都不能解密,否则这个组织就得自行解体。
毛是1976年9月9日咽气的。李**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到关于毛与张玉凤的关系问题。
李**写道:毛大部分的时间都和张玉凤在一起。毛自一月病重后便常和张一起吃饭。江青和别的领导要见毛都得先透过她。江只好通过张玉凤打听毛的情况,传递消息,取得毛的支持。为此,江送给张玉凤许多东西,像手套、西装、衣料之类。甚至张生孩子所用的尿布,江也送去。据同在毛身边做服务工作的孟锦云说,江青让张玉凤在毛面前多说江的好话,使毛多见见江。张也很卖力向毛说了,鼓励毛多见见江。但是张不明白毛的心理状态。
张玉凤确实不理解毛为何如此讨厌自己的最后一任老婆,当年江青怀孕时,毛并没有和在苏联养病的贺子珍离婚。后来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毛顶着政治局极大的压力才与挺着大肚子准备要生的江青结了婚。现在为何讨厌江青到无法见面的程度?张玉凤并不知道,毛最无法忍耐的是有人跟他分权,而江青就是打着毛妻子的名义在搞自己的势力范围。
李**写道:张和我一向就相处不好,她对毛的控制力越来越大,我们的关系便日益紧张。她要毛每顿饭喝一小杯茅台酒。我反对,怕烈酒容易引起咳呛。但毛说他已戒烟,以前也不大喝酒,一点点茅台不会怎样的。喝一点对睡觉可能有帮助。张很喜欢喝酒,在她的鼓励下,毛完全听不进我的话。

张玉凤与毛生的儿子。
李**还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九七二年底,张玉凤怀孕了。张耀祠跑来找我商量。汪东兴和他都提出,要好好照顾张玉凤,能平安生育下来。我向张耀祠说,毛早已没有生育能力了,何况这时已近八十岁,又在重病以后,体力虚弱,这不可能是毛的孩子。
我说「在我这方面没有什么照顾好不好的问题。张玉凤的行政隶属在铁道部,铁道部有自己的公费医疗医院,她可以去做产前检查,可以在那儿生产。」张耀祠说「正是这件事要你办。张玉凤讲,主席说了,要给她送到一个好些的医院去。所有的费用,由主席的稿费出。」我看汪东兴、张耀祠两个人都是这种态度,再争下去,也没有用处。于是我将张玉凤介绍到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院看到是我介绍的,认为张玉凤来头不小,可能是那位首长的夫人,或是文化革命中窜红上来的「新贵」,自然要待如上宾。到八月张玉凤生产的时候,给她住进高级干部病房。张分娩以后,的确有许多政要显贵来探望,其中还有张的丈夫刘爱民。江青和张耀祠都去了,送了吃的和尿布等东西。江青一再向张玉凤提出,及早回去上班。张产假期间,由她妹妹张玉梅代替工作。张玉梅比较单纯,没法子替江青向毛传送消息。
张产假期间,由她妹妹张玉梅代替「工作」?姐妹俩侍候一个男人?这是一般人实在无法想像的事情,更何况发生在「一句顶一万句」身上。这哪里是什么国家领袖啊,明明是毛氏私家**作坊。人民报萧良量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抄史
作者:才差二斗(czrd)
毛泽东亲自回忆第一次婚姻,是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她。”
毛泽东的这个妻子叫罗大秀。和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罗大秀并没有自己正式的名字。那个年代的女人们,就一个乳名,出嫁随夫后就把夫姓冠在前面。比如毛泽东的母亲姓文,嫁到毛家前乳名叫七妹,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的就是一个文七妹了,韶山冲里人叫它“毛文氏”也是不会错的。后来有人把文七妹叫成“文其美”,想必是另有用心吧。小罗姑娘出嫁前的乳名唤做秀妹子,她在姐妹中居长,所以她的父母就叫她“一秀”或“大秀”。大秀家居住在韶山杨林桥炉门前,与南岸毛家相隔不过六里之遥。她的父亲叫罗鹤楼,有三个女儿,而毛贻昌(即毛顺生)有三个儿子。这正是罗鹤楼选中毛家结亲的一个原因。大秀生于1889年10月20日(《韶山毛氏族谱》载:罗氏生于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日丑时),大秀18岁那年(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坐着花轿,吹吹打打,明媒正娶地嫁到了毛家,她比毛泽东大四岁零两个月,石三伢子那年才十四。大秀性格温柔贤慧,勤劳俭朴,人也生得体面丰满,与毛家人相处的也是不错的。
阳历1910年春(2月),罗大秀患痢疾去世的(这种病七天左右就会要命),其时还不满21岁。对于妻子的死,17岁的毛泽东心情是悲伤而又复杂的。从本质上讲,妻子的死比13岁那年毛泽东因为父亲骂他“懒惰”而闹到以跳塘投水相要挟那一次深刻得多。当父亲正式提出要送他去湘潭米店当学徒时,毛泽东痛苦极了。对他来说,这正是他人生的十字路口。读书与学徒之争,在这个家庭中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丧妻之痛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忧烦从两面同时向毛泽东袭来。一个17岁少年的心,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该有多么残酷!同年秋,毛泽东才第一次离家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到长沙求学是1913年的春天,年满二十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合并于第一师范)。1925年他带着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父家拜望过。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而且离开韶山,就是从炉门前走的。
斯诺的《西行漫记》里有两处错误:一、“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不对。罗大秀嫁到毛家时不到二十。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是凭记忆随口说的。或者是斯诺记错了。二、“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也不对。一秀在毛家生活了三年,感情是相当不错的,大概是因为某些复杂的历史原因吧,没有承认。在毛泽东的家谱中,对毛泽东的婚姻是这样记载的:罗氏是毛的原配,杨开慧是继配,贺子珍是续配,江青是再配。根据现有正史,毛泽东(1893——1976)一生有过四次婚姻。第一次婚姻:1907年与罗大秀(或者叫罗一秀)成亲,毛泽东14岁。第二次婚姻:1921年春节前后(也有说1920年后期的),与杨开慧结婚。第三次婚姻:1928年5月在袁文才、王佐等两位“大媒”的一再催促下,毛泽东和当时的“永新第一美人”贺子珍(又名贺自珍)同居。第四次婚姻:1938年11月19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这是毛泽东的最后一次婚姻。近百年来,毛家五代人分别是:毛的父亲毛顺生,毛泽东和他的弟弟毛泽民、毛泽覃,毛的儿子毛岸青、毛岸英,毛的孙子毛新宇,毛新宇的儿子毛东东(2003年月12月26日,毛新宇的儿子在爷爷110岁生日这一天出生。如果不是剖腹产,我想这简直是一种天赐的巧合。这个孩子的乳名叫东东。)
几段野史:
一九九○年底,大陆流亡作家京夫子出版了《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关于毛泽东的恋情有这样的独家记载:
其一、毛泽东与陶斯咏(陶毅):在罗大秀与杨开慧之间夹了一位陶斯咏小姐。估计这个陶小姐是毛泽东的第一个自由恋人。陶斯咏与向警予、任培道,同为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的三位杰出的女弟子。杨昌济还有三位杰出的男弟子,那就是毛泽东、蔡和森、萧瑜。陶斯咏于一九一四年参加了毛、萧等人创办的学生组织“新民学会”,大约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前后,毛泽东与陶斯咏在长沙共同开办了一间“文化书店”,进行革命活动,“两人深深堕入了爱河中”。于是“两情相悦,愿作鸳鸯不慕仙”。——京夫子这段材料的来源自萧瑜的《我与毛泽东行乞记》(萧特之《毛泽东传》)。说法现在看来是有些硬伤的。但从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年谱》里,有许多条毛泽东与陶毅通信、登山、组织学会活动的记载,而且,即使是在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么伟大而神圣的时刻,毛泽东也抽出了时间去看望在某大学读书的陶毅。有一首词以前说是写给杨开慧的,后有人分析是写给陶毅的:“《虞美人&S226;枕上》(1920年)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其二、毛泽东与李一纯:婚后五年,杨开慧生下岸英、岸青两个儿子;毛泽东则“奸污了同住在一座院子里的中共另一位早期领袖、朋友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大约在第三子岸龙出生前后,毛泽东又有过一次喜新厌旧的移情别恋,杨开慧跟他狠狠地闹过一次家庭矛盾。——李立三太太(李一纯)“被强奸案”来源于中共早期领袖之一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的回忆录。有硬伤,不可信。
其三、毛泽东与丁玲:“他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来。他封贺子珍做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替我执掌文房四宝,海内奏折。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代拟圣旨……那是慈禧干的事,大清亡在她手里……’
他是个很风趣的人。在他最落魄的日子里,也没有忘记做皇帝梦。他扯着我的手说:“看来瓦窑堡民生凋敝,脂粉零落,不是个久留之地,……”
一九八二年盛夏,刚从美国访问旅行了半年回来的丁玲,在大连避暑时,亲口对同住在一所疗养院里的一位“爱好文学的中年科学工作者”讲的,所谓“爱好文学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大概就是京夫子自己。说法也有硬伤,不可信。不过老毛对他喜欢的女人老是爱题个诗什么的,给丁玲真是写过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其四、毛泽东与“两个骚货”:贺子珍离开毛泽东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秋天。而这一年的冬天,蓝苹(江青)才从上海抵达延安,第二年的夏天,她才有机会进入了毛泽东的生活。贺子珍动不动就要拿枪“毙掉那两个骚货”当然既不是江青,也不是丁玲,而是史沫特莱跟吴广惠(吴莉莉)。史沫特莱是年仅25岁的美国女记者,一九三七年春上到延安。据一位不肯透露姓氏的中共老人于一次闲谈中提及,史沫特莱跟毛泽东见面,第一次握手,第二次拥抱,第三次亲嘴,使得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大为惊讶这洋人的礼节。亲亲嘴也就罢了,一亲还“亲上半个时辰”——毛一位警卫员偷偷跟自己的老乡说。吴广惠的事迹,则引自斯诺的前任夫人韦尔斯的一段文字。吴广惠参加过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曾在中华戏剧学校任教,一九三七年初由一个共产党员保送到延安学习。她年轻(26岁)漂亮,教养良好,梳的是三十年代城市女性最时髦的及肩卷曲长发,还涂着唇膏。她被指派为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中英文翻译,跟史沫特莱住一个窑洞。史沫特莱住里间,吴广惠住外间。毛泽东本来的亲嘴对象是史沫特莱,后来却变成吴广惠了。一天深夜,贺子珍尾随毛到了吴广惠的窑洞,大力拍门,门开后,见到毛与吴便歇斯底里大闹起来,史沫特莱闻声出来相劝,竟遭贺子珍持手电筒殴打。这件事以毛泽东下令将她们“驱逐”出延安而告结束。一年以后他告诉斯诺:“我下令从延安驱逐了三个女人。”三个女人,还有谁呢?就有贺子珍。被驱逐的吴广惠后来不知去向。这段故事是真,姻缘有假。
其五、冯凤鸣与孙维世:这时又出现了一个冯凤鸣。冯姑娘原是一位南洋富商的千金,回广东投身抗日,曾参加中共东江抗日纵队,后保送到延安,在延安平剧院做演员,与郭兰英、孙维世、张醒芳并称“四大美女”。从我们后世的眼光来看,起码其中最有名的郭兰英就不能算作“美女”。不过在当时都算。毛泽东看她演出,嘴里不住地称赞:“小冯,小冯,强过郭兰英……兰英演什么都是一个样子,劲头十足…….凤鸣却是演什么就像什么……”江青看在眼里,明在肚里,为了讨好毛泽东,竟伙同李富春的夫人蔡畅“大姐”,将冯姑娘骗到毛的窑洞吃霄夜,让毛把她给占了。冯凤鸣是个血性姑娘,此后不久便从延安消失了踪迹。这段故事有硬伤,不提也罢。
“四大美女”的另一位孙维世,也被毛泽东占了。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养女,也曾在延安平剧院当演员,后赴莫斯科专修俄语。一九四九年学成回国,已是一个二十多岁、人见人爱的“大美人”。这年十二月,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孙维世临时充当专列上毛的俄语教员。一天晚上,孙维世于昏昏糊糊之中,以纯真的处子之身,伺奉了“伟大领袖”。“伟大领袖”竟玩世不恭,说三大战役,同登仙境。要说孙维世确实是死于文革中的迫害。享有“保护了一大批老同志和文艺工作者”盛望的周恩来,竟然未能出面保住自己这位养女的性命,诚属怪事,可想其中一定有隐情。这故事中可能与孙在延安时与江青演戏争风头有关,与婚姻无关。
其六、毛泽东与俞珊:俞珊是江青前夫俞启威的妹妹。据美国记者沙兹伯里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新皇朝》中文版一书中称,“传说,俞启威认为他的前妻不足以匹配新中国的统治者,故意安排俞珊接近毛泽东。俞珊文化水平高、聪明、迷人,样样胜过江青,但,这仅是传闻。”沙兹伯里启发读者,中共官方称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间从香山迁入中南海,实则从三月二十五日直至十一月,他都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其间,江青被送往苏联养病,「毛泽东此时是否金屋藏娇,与俞珊在香山鬼混呢?似乎颇有可能。一九四八年五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迁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俞启威时任张家口市市长。“传闻”正是这时将俞珊引见给毛,以为邀宠。问题是,俞珊虽出身名门,毕竟“俞”娘半老,年已四十上下,似不可能。有硬伤,不可信。
其七、毛泽东与刘松林:说毛岸英战死沙场,毛泽东深感悲伤,儿媳亦痛失丈夫,经常扑到“爸爸”怀里要岸英。这举动颇令江青忌恨,于是采取防范性措施,吊销了她的中南海出入证。毛泽东知道后,另安排了一张出入证,并嘱她今后直接来见他,不要再去找江青。一九五三年九月的一天,他们又搂在一起想念亲人,相对垂泪“很久”。不料,“恰在这时,江青一头撞了进来,见了他们的模样,顿时打破了醋罐子,歇斯底里大发作,又哭又闹的,什么难听脏话,都骂了出来。”这次“扒灰”受挫,导致了毛泽东心情极坏,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破口大骂他的老朋友梁漱溟。胡扯,附会。极不可信。
其八、两位青岛佳丽的小说故事:一九五六年夏季,青岛歌舞剧团有两位年方二十、俏丽迷人的女演员,一个叫大玢,一个叫小芳,先后由组织上安排,去接受一次“光荣的政治任务”,即获选到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经过一番七弯八拐,又是洗浴、又是验身、又是梳妆打扮的折腾,被送进了毛泽东在青岛行宫的密室,让她们替毛泽东洗澡。大玢因为害怕,错过了为毛服务的机会,被出浴之后的毛打发送了回去。虽有司机语重心长的告诫,“今晚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还是忍不住讲给了同室的好友小芳听。小芳为之错过好时机顿足叹息:“你傻,你真傻!你差点就跟了毛主席去北京,叫做进宫呀!”第二天,小芳也被接走,她比大玢有出息,再也没有回来。大玢也在这一天被送到遥远的东北边境,在小兴安岭当了一名伐木工人,一辈子没有结婚,却跟采伐场一个又一个的单身汉睡过觉。直到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已经四十二岁、变得又老又丑的大玢才“落实政策“返回青岛。条件是,她必须忘记这一切。至于小芳,则不知所终。故事讲的太传奇,不可信。
其九、毛泽东与上官云珠: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到了上海,住西郊宾馆一号院。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安排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跟毛泽东幽会。先是一道吃霄夜,吃完霄夜一道游泳。一号院是上海专为毛泽东修的行宫,内有一座三十米长的室内游泳池,绿波荡漾,清澈见底。毛与上官游了一会儿,手拉手,在水中你一句我一句对起了唐诗。对到后来,就在池中水浅处成了好事。京夫子在这里有几段的细节描写,读来颇似香港色情杂志《龙虎豹》上抄得的文字:“主席……轻些,轻些,侬真雄伟啦……妈呀,阿拉站不住啦……”第二年,毛泽东又到上海,与上官云珠重会。每次上官都要拋下女儿,跟毛住上好几天。一九六五年,她甚至被毛泽东带进中南海,公开同居,又随毛乘专列回上海。此后再没有见过毛泽东的面。一九六六秋天,她被江青下令逮捕,后死于狱中。这是模仿《龙虎豹》的写作手法写的,搞笑。
其后被京夫子详细写到的女人,还有庐山服务局的会弹琵琶的服务员白玉莲,杭州西湖别墅擅长按摩的保健护士杨丽清,等等。她们都各占了整整一个章节的篇幅。这本书的女主角,的确是从专列服务员,一直干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的张玉凤﹙张毓凤﹚。这个人物在毛泽东的晚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毛泽东死后,她还在一些与毛有关的仪式中出现。从文革中过来的中国人,都记得她那总是伴随和搀扶毛泽东出现在公开场合的身影,她那说不上秀美却总算端正的容貌,有点像京剧样板戏《海港》里的女主角方海珍。她的故事也在中国的平民百姓中流传甚广。对那些传说,那些逸闻轶事,她始终是默默无言。毛泽东死的时候,她才卅七岁。她有一天会开口向我们讲述一个真正的毛泽东吗,就像“白头宫女说玄宗”?
李志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特地提到:“毛喜欢年轻单纯﹑容易控制的女孩,好象特别喜欢女演员。吴广惠,江青,冯凤鸣,孙维世,俞珊,大玢和小芳,都是女演员。一九五三年韩战结束,援朝志愿军陆续回国,由一帮漂亮姑娘组成的“志愿军歌舞团”回北京后,竟直接隶属于中央服务局,改名“中南海歌舞团”,主要任务就是陪“中央首长”跳舞。毛泽东当然是主角。许多女孩子跑到老首长彭德怀家里,哭诉遭受的凌辱。彭德怀大怒,责问毛:“主席,这些孩子都是从朝鲜前线下来的,都是我的部下,你要留作后宫吗?共产党也兴这个吗?”随后,他下令撤销“中南海歌舞团”,为她们另行安排了工作。看看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怎么写的“三个女友”的故事。
第一个女友:发生在“专列窃听事件”中。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二年春节过后不久,毛的专列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可能是大托铺之误),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王延春数人应召来到毛的隔壁车厢等候晋见,“很久”毛才出现。会谈开始,李志绥、幼儿老师(毛的女友)、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录音员刘凑过来,对着幼儿教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么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他:“还听到什么?”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幼儿教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此事一经发现,当然得到果断处理,所有录音装置立即撤除,涉案人员坦白交代后被调离。毛泽东的心里,也由此埋下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对他的“中央”,对他的越来越与他疏远的党内同志们的深深疑惧。更使他震动的是,他被窃听监视了几年,身边竟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的人,最后让他知道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看来除了“女友”,没有谁真正靠得住。毛泽东有许多“女友”,要一一数清是不可能的,连他自己恐怕都办不到。所以可叫做“无数”。中南海春藕斋舞厅旁专门为毛修了一间“休息室”,放了床铺。舞会时常见毛泽东乘着舞兴正酣,拉一位女孩子进去,呆在里面少则半小时,长则一个多小时。这些伴舞的女孩子,都是从各军兵种政治部文工团选来的女演员。另外在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也有一些“女友”。
第二个女友:在上海,毛泽东及随行服务的“一组”住在锦江饭店南楼,毛与一位女机要员住第十二楼。凌晨四点,一名新来的卫士到毛房间倒茶,不料一个女人光着身子从床上掉了下来,把这名卫士吓得赶紧跑到八楼找李志绥。后来才知道,是毛与这位女机要员吵翻了。她有个男朋友,想结婚,毛不让她结婚。这次又讲到结婚的事,她便说毛将她作为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非常生气,将她踢到床下。他俩根本没注意到卫士进去倒了开水。毛把汪东兴叫进去,要汪立刻开会批评她。汪进退两难:“这怎么好。随便批评一下,传到毛那里去,毛说我们敷衍了事,这就说明我们知道内幕,才马马虎虎过去。但是批重了,她沉不住气,说出真相,等于将毛的丑事抖露出来,毛会认为丑化他。”最后汪想了个折衷办法,批评她不尊重主席,让她作了自我批评了结。这位女机要员是湖南人,毛的同乡,在中南海跳舞认识的。毛泽东曾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中国老百性耳熟能详的这首《七绝》,原来是这样产生的,真是哭笑不得。那位照片上的“女民兵”,文化革命期间曾广为刊印。平心而论,毛的这位女友飒爽有余,而风韵不足。毛泽东确实是喜欢那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人。所以江青偏要骑马驰骋,贺子珍惯使双枪。杨开慧没赶上参加红军,不然以她投身革命的积极和刚烈,一定也是骑马打仗的好手。这位女机要员化装成“女民兵”,倒不一定是投毛所好,她天生就有几分女民兵的性格,以致竟敢指责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煞是憨勇可爱。据说江青见了《题照》,不依不饶,一定也要毛泽东为她同样题诗一首。于是就有了另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题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李进”同志是江青同志的笔名。文革以后,不少人把这首诗加进浓厚的性意识,逐句新解。现在想想,倒是解得有些妙。《为女民兵题照》是一九六二年二月的事,《题仙人洞照》是同年九月的事。这年的十二月,毛泽东又作了一首词《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词前有一则小序:“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据说陆游的这首词,是毛泽东一位女友抄来给他看的,以表达排遣心中的失意与不平:“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这才有毛对她的劝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题仙人洞照》和《咏梅》,后来都被称为反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光辉诗篇,表现了革命领袖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
第三个女友:一位文工团员,她是江青在外地时第一个整晚待在毛房内伺候他的女人。不但自己奉献,还把姐姐嫂嫂们都介绍给毛,名副其实的“内举不避亲”。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毛在无锡太湖的梅园请那位文工团员、她二姐和二姐夫一起吃饭。饭后毛叫二姐夫回家,让二姐住了三晚。二姐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期间毛把曾希圣和柯庆施叫来,讨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汪东兴愤愤地评议:“竟然还有这样“王八式”的男人。”接着又讥笑,“她的妈是死了,不死的话,也会来。这一家子真是一锅煮。”那位女文工团员有滴虫病(在团内,舞蹈服装是混穿混用的,极易互相感染),使毛成为滴虫携带者,又传给他的众多女友。李志绥一面用西方进口的最好的药给她们治,一面劝毛也接受治疗。毛不以为然:“既然对我没有什么害处,那又有什么关系,何必大惊小怪哪!”李说一旦传给了江青就不好说明。毛笑了笑:“这不会,我早就同她讲,我老了,办不了事情了。”李再劝他将局部清洗干净。毛说:“没有这个必要,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
这三个故事,女主角只有两人。加上窃听事件,一共三个女主角。李志绥对这三个女人显然都没有特别的反感,基本上可排除“曾有嫌隙、藉写书之机报复”的因素。
李志绥写这三个女友的故事,都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在场证人,那就是汪东兴。一九九五年八月五日,在李志绥去世近半年之后,美国华文报纸《侨报》“转载”汪东兴等人的公开信:《辱华反共的丑恶表演——我们对李志绥及其「回忆录」的看法》。看完汪东兴等人的“看法”,不禁失望。一是公开信没有具体地指出李志绥写的哪一条关于毛泽东的回忆与事实不符,通篇只说李志绥本人不是东西。二是公开信的签名多达一百三十五人,其中毛泽东身边的旧工作人员只有三十几人,其余不是只数面见过毛,便是干脆跟毛没有一点关系,八竿子都打不着。这就大大削弱了其自身的战斗力,削弱了其作为“知情人”的公信力。后来林克、徐涛和吴旭君合写的《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一书。和书中的观点正好相反,据一位接近过林克的学者透露,林克曾私下承认,李志绥所言毛与众多女友淫乱一事“都是真的”。观《历史的真实》全书,没有一处敢于正面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究竟淫乱与否?”其作者在这样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上,采取这样一种公然的回避态度,当然也就很自然地让我们看出了林克等人的胆怯。
毛泽东最后的女人张玉凤和孟锦云。再来讲几个故事听:张玉凤最出名的一例,是骂毛泽东作“狗”。一天,护士孟锦云一觉醒来去接张玉凤的班,走到毛的卧室门口,听到里面毛在大声吵嚷:“你给我滚!”“滚就滚,”张玉凤的声音也很激动,“谁不让我走谁是狗!”毛泽东气得发抖,“你骂我是狗,你……”后来毛把张骂他是狗的话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了有关工作人员。“我要不滚,你就是狗”这件事李志绥也提到了,而且更为生动。
那是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李同两位心脏病专家朱和陶到游泳池毛的书房内见毛,一进去毛就叽里咕噜说了一套。张玉凤不肯翻译,毛发了脾气,举拳跺脚,张才说明真相。原来前天,即六月八日,张玉凤出去了,毛要读文件,等了很久。张回来,毛很生气,写字条说:“张玉凤,滚。”张即回骂:“我要不滚,你就是狗。”毛对李志绥等人说:“我的脾气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朱陶二位听完,不禁愕然。
第二个故事是民间流传张玉凤在毛泽东身后的“名份之争”。一个皇朝已经结束,先君走了,她似乎有一种“秋菊式”的执着,一定要讨“一个说法”。她接连向党中央打了三次报告,要求为自己和孩子正名。邓的批示是:“这类人儿太多。我们不要管什么李玉凤、萧玉凤,不要开这个例。郭沫若同志去世后,也有许多女子领了孩子来提要求。统统不能承认。”倒是胡耀邦觉得应该实事求是,至少得有个妥善的安排,于是让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找张玉凤个别谈话。冯文彬色胆包天,竟依仗权力,将她弄上了手,满足了巨大的好奇心,但还是没能给她“一个说法”。张玉凤一气之下,写信告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后由胡耀邦出面,撤了冯的职务。
除了众所周知的张玉凤,还有一个发掘出来的“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这就是孟锦云。孟锦云到毛泽东身边,是一九七五年初夏。准确些说,是五月。那年孟锦云被留在中南海,在毛身边当贴身护士,陪伴毛泽东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四百八十九个白天与夜晚。
一九五九年,十二岁的孟锦云考取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那时她看到一些年纪较大的老同志经常到中南海“出任务”,也就是陪中央首长跳舞,心里羡慕极了。所谓老同志,不过就是十几二十岁左右。到了一九六三年四月,她十六岁,成了老团员,也被派去陪舞。在“春藕斋”舞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看过毛跟别的女团员跳过一曲之后,孟锦云主动上前邀毛。这时奏的舞曲是《喜相逢》。
“你是新来的?”
“我第一次来。”
“怪不得面生。小同志,你叫什么名?”
孟锦云报了姓名。
“这名字好听,你跟孟夫子同姓呢。”
顺便说一点,毛讲究禁忌。除了“面相学”,还好留意“姓名学”。汪东兴的名字,据说是毛重用他的一个原因。有汪,“东”才会“兴”。江青的名字也是他亲自给取的,这之前叫蓝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胡宗南攻占延安,中共中央流亡黄河边期间,毛给自己取了个化名叫李得胜——“离开就能得到胜利”,他后来果然得胜。中南海舞会上,有个伴舞的女文工团员被问到名字叫“双华”,毛立即说不好,“两个中华”。文革首次接见红卫兵,清华附中一个献袖章的女将被问到叫“宋彬彬”,毛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便说“要武嘛!”结果宋彬彬改名叫“宋要武”。有人说,张玉凤也是凭着一个好名字,而让毛一直留用在身边的。所谓“游龙戏凤”。
又问到她的老家湖北,更高兴了,连说“是我的半个小同乡!”这就是陪毛泽东跳舞的许许多多女友中的一个,认识过程非常简单,是由孟锦云自己回忆的。在孟去中南海做护士之前,毛泽东还有一位贴身护士“小李”,一直伺候毛伺候得好好的。孟来了以后,毛开始左看她不顺眼,右看她不眼顺,经常喊她“滚”。这是真滚,不是假滚。跟孟在一起却老是有说有笑,打趣,讲故事,等等。
“主席,您嘴巴底下有一个痣子,听我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痣子呢。”
主席听了,看到小孟白白净净的脸蛋上,也有一个小小的痣子,便笑着说:
“你的脸上也有一个痣子,那你也有福噢。”
“那可不是,您的痣子是湖南痣子,我的痣子是湖北痣子,长的地方不一样。”
主席哈哈大笑:“没想到,你还是个小九头鸟呢。”
有一次,孟锦云对张玉凤说:“张姐,我都快三十岁了,我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张果真把孟的想法告诉了毛:“主席,孟夫子想要个小孟夫子啦。”
“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吧。”
孟锦云想要小孩,如果不是想要一个毛的孩子,干嘛要张玉凤跟主席替她说说?她要跟丈夫生孩子,与毛泽东和张玉凤何干?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小孟想请个假,回去与丈夫同房。但这样理解显得牵强。当毛的贴身护士虽不自由,并不是连跟丈夫同房的机会都没有的,除非你不想同房。毛的回答也有意思,明显是不想跟孟生孩子。其时孟锦云才二十七、八岁,毛却已力不从心,李志绥也早告诉他无法再生育的实情,所以才有“等我死了,她再跟她丈夫去生吧”的潜台词。
到底谁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是张玉凤还是孟锦云?其实是无关紧要,也无从考据的。而且“最后一个女人”的意思,也本来含混不清。是指最后一个跟毛泽东睡过觉的女人,还是指毛泽东最后发展成“女友”的女人﹖看叙述者力图表明的意思,应该是指具有女友身份、最后一个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女人。
某春日,毛泽东到户外蹒跚走了一圈,半开玩笑地说:“张姐,孟夫子,你们二位是我的左膀右臂噢。”他没有说错。一个左右了苍茫大地沉浮的人,一个“扭转了乾坤”的人,最后就剩下这两个年轻女子,扶着他走到生命的终点。
李志绥出生于北京,祖父做过清朝皇帝的御医,父亲曾留法勤工俭学,后成为国民党的高官。李志绥十六岁受洗为基督徒,在抗战结束的前一年毕业于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曾任职南京中央医院,一九四八年底赴澳大利亚悉尼,担任海上的船医,一九四九年六月,应中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之邀从香港回到北京,在香山“劳动大学”(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代号”门诊部工作,一九五○年秋季进入中南海门诊部,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四月获毛泽东接见,专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并在毛健康恶化病危之际任医疗组组长。毛死后,李志绥曾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回北京复职三○五医院院长,年底退休,一九八八年八月与妻子同赴美国芝加哥与儿媳团聚。他的回忆录,就是旅居美国以后,花了三年时间在芝加哥的寓所里完成的。李志绥一生的经历,无疑是极为特殊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他的多幅与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合影,更为他在毛话题上发言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提供了有力的左证。他的保健医生的职业,也颇为方便和不可避免地接触和了解到毛的大量隐私,包括毛的病理状况、性能力、性心理、性观念和性习惯。这绝非藉助来源于别人的材料,进行想象发挥的「小说家言」可以相比。绝大部分读者的判断是,它是真实的。我以为,即使没写“性生活”,或者即使写了“性生活”,李志绥的书都当然是极有阅读价值的。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或依另一些人说的,工作了十八年之久;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人类的影响和研究价值,也远非一个英国的王妃所能比拟。跟随这样一个人物这么多年,一定有许多独特的见闻和感受,让人饶有兴趣。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只要基本上秉持一种中肯、严肃的态度,它就会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至于写没写“性生活”,为了一个什么目的,为还原于真实还是为了钱去写“性生活”,他到底写了多少,而且怎样写的“性生活”,其实倒还真是其次。
读者群和影响面的不断扩大,负面批评也随之而来。以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首的一百三十五人签名公开信《辱华反共的丑恶表演》,从李志绥的个人身份和人格,到此书的目的及出版过程都进行了否定。一些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也出面“证伪”,认为李志绥其人其书都是骗人的。毛泽东的秘书林克,保健医生徐涛,护士长吴旭君,合撰《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一书,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以相当的篇幅批驳李志绥,还有一部分篇幅用以温馨地回忆毛泽东。当然,这些批判遭到了声势更为浩大的反击。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正面评价,都是基于“非毛”的立场;几乎所有的负面批评,也都基于“护毛”的立场。两种立场截然相反,不共戴天。
张玉凤与毛生的儿子。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出版后不到四个月,已着手撰写第二本书《中南海回想录》的李志绥猝逝于他在美国的寓所。李志绥的死因,也一度成为人们的话题。美国警方的报告是因心肌梗塞自然死亡,他的次子李二重却怀疑,其父死于谋杀。一是死亡现场洗手间里,一卷厕纸的卷筒中轴被抽出来,拉成一条类似绳索的长条﹔二是牙膏、牙刷被扔进了马桶,似乎是谋杀者以此种方式泄恨,表示李「臭不可闻」﹔三是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是下午四点,而下午三点李二重出门上班时李志绥还好好的。
(转载)
关于张玉凤
张玉风
图片中间是张玉风的儿子
张玉凤原是毛泽东专列上的一位普通列车员,一次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连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被“大太监”汪东兴发现后,立即调张玉凤到毛泽东车厢里专门侍候毛泽东。不久又调入中南海丰泽园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编者注:从中可以看出汪东兴对“主子”是一付十足的奴才相)时年张玉凤仅18岁。最后又提升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享受正部级待遇。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张在毛泽东身边整整侍候了十八年。事实上她与毛泽东同居了18年,这期间张玉凤为毛泽东生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儿子是1963年出生的,毛泽东亲自取名为“张南子”,意即“南海之子”;跟江青的女儿一样,从母姓)。
在毛泽东死后,张玉凤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为两个孩子正名问题,要求公开承认是毛泽东的儿子。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同意张玉凤的要求,无疑给“伟大领袖”的脸上抹黑。当时,华国锋已大权旁落,胡耀邦表示同情张玉凤和孩子的命运,问题最后到了邓小平手里,他说:“这类人儿太多,我们不要管什么李玉凤、萧玉凤,不要开这个例,……”。
胡耀邦觉得总应该跟人谈一谈,做做思想工作,并进一步安排好张玉凤跟原先那位丈夫复婚,过正常人的生活。胡耀邦说:“她才四十岁的女同志,本身有什么错?是毛主席要了她十八年吆。
关于张玉凤
2012-12-0714:04:07|分类:人物春秋|标签:|字号大中小订阅

转载▼
西域顽石
张玉凤原是毛泽东专列上的一位普通列车员,一次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连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被“大太监”汪东兴发现后,立即调张玉凤到毛泽东车厢里专门侍候毛泽东。不久又调入中南海丰泽园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编者注:从中可以看出汪东兴对“主子”是一付十足的奴才相)时年张玉凤仅18岁。最后又提升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享受正部级待遇。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张在毛泽东身边整整侍候了十八年。事实上她与毛泽东同居了18年,这期间张玉凤为毛泽东生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儿子是1963年出生的,毛泽东亲自取名为“张南子”,意即“南海之子”;跟江青的女儿一样,从母姓)。
在毛泽东死后,张玉凤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为两个孩子正名问题,要求公开承认是毛泽东的儿子。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同意张玉凤的要求,无疑给“伟大领袖”的脸上抹黑。当时,华国锋已大权旁落,胡耀邦表示同情张玉凤和孩子的命运,问题最后到了邓小平手里,他说:“这类人儿太多,我们不要管什么李玉凤、萧玉凤,不要开这个例,……”。
胡耀邦觉得总应该跟人谈一谈,做做思想工作,并进一步安排好张玉凤跟原先那位丈夫复婚,过正常人的生活。胡耀邦说:“她才四十岁的女同志,本身有什么错?是毛主席要了她十八年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