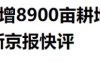我的母亲是资深的小学老师,在不大的南通小教界,颇有影响。对于如何培养、引导学生,自有她一套因材施教的独特方法,我也是受益者之一。
我1950年出生于上海。6个月时,父亲解放前的一桩“棉纱”案,遇时局更迭,草草了结,被公安抓走半年,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俩匆匆回到南通。由于抓捕现场受了过度惊吓后,我自小落下孱弱胆小、记忆力特差、不愿与人交流的病根。1955年我5岁,“肃反运动”中,父亲因在上海为谋生曾经“参加国民党”,于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审查时“畏罪自杀”。叠加因素,使我的病根加重,出现了类似现在说的“自闭症”。母亲以一个教师的职业判断,认为若不趁早让我溶于社会,由老师因势利导教育,拖久后极易脑心障碍,影响一生。因此她决定,让我早一年上学。于是1956年暑假后(是年我刚满6周岁),母亲与学校打了招呼,让我进入了北浩小学。之后的事实证明,母亲当年的分析与决定是正确的。
北浩小学
北浩小学位于南通市育婴堂巷原12号。一年级时,当时我家还租住在环西路的朱家,走路也就十分钟路程。北浩小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好大。学校有南北两个施教区域。南区是个四合院,朝南有四间平房,一、二年级各两个班;朝北是教师宿舍及办公室;北区是一座两层楼,上下层各四间。楼下是三、四年级各两个班,楼上是五、六级各两个班。在南北施教区之间,是大大的操场。操场围墙边长着一排杨柳树,学生们踢球,偶尔会将球踢出校外,常有一些胆大的学生,蹭地爬上了树,翻出墙外捡球。
北区的两层教学楼的后面有个小操场,那里有一间音乐教室,一架风琴,老师总能弹出动听的歌曲,音乐课,似乎是学生们最自由的时光。另外,小操场还有一间劳动工具房,里面放的是扫帚、铁锹、铲子什么的,黑咕隆咚、脏兮兮的,经过时能闻到一股臭味,我总掩鼻而过。小操场设有2张水泥板的露天乒乓球台。最西头是厕所,男厕在外,女厕在里。到了下课时,楼上楼下学生们一窝蜂冲向小操场,为的是能抢到乒乓球台,占上一个位置。当然还有不少,是憋不住了去上厕所的。
一年级时的情景,我现在记得很少。那时我比同学们小一岁,加上原本就矮小瘦弱,那显得就更小了。我长期窝在家里胆儿小,进了学校怕与老师同学们交流。因此,老师与同学喊我时,都爱在我学名“王明”前面,加上一个“小”字,是亲热,还是蔑视?我不知道。有时连打上课铃的校工杨二爷爷,见了我也笑容可掬摸摸我的头说:“小王明你好呀”。随他们喊去吧,小是事实,我才不在乎什么大小呢,学习第一嘛。
学校到家两点一线,那时放学后也没啥作业,我要么看看书,要么就爱搬搬象棋子儿,宅在家里不串门。班上有一位李姓同学与我稍许有点来往。他住在朱家的南面,后窗紧挨朱家院子。他来我这儿主要是常与我下象棋。
进入了二年级后,我的“自闭症”好转,心智突然被打开,记忆力好了很多。渐渐爱说话,上课也能主动举手发言,回答老师提问题时,声音高了,学习成绩逐渐上升。班主任王湛老师、算术龚吉林老师,对我最为关心。小学毕业,我能考入市重点初中——南通市第三初级中学(现名为崇儆中学,又名实验中学,下文简称三初中),她们功不可没。在北浩小学的六年,不仅治愈了我的“自闭症”,更是接受到启蒙教育,对一生影响重大。那些年,除了学习上课外,社会上各种运动此起彼伏,也影响到我们小学生,让我经历了一些课堂以外的事,从无字处读书,刻骨铭心,难以忘却。
一条“反动标语”
记得二年级下半学期的一天,平素和蔼可亲的班主任王湛老师,一脸严肃,陪同瘦高严峻、不苟言笑的陈坚校长来到教室,发给每位同学一张白纸,要求大家自然而快速地(不许刻意)写上“打倒反动派”、“共产党万岁”两行字,并签上姓名,写完后当场被两位老师收去。我们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云。过了一段时间,耳闻是有同学写“反动标语”,具体情况学生们并不清楚,没多久大家淡忘了,直至放暑假无人再提此事。
二年级的暑假里,我家从环西路搬迁到育婴堂巷原8号,距离学校更近了,相隔4个门牌号,在家里就能听见操场上同学们的欢笑声。但我实在不喜欢住这儿。因为房子变小了,变矮了,一间房搁三张床,住5口人(那时弟弟5岁),室内空间太小。幸好有个二门堂,我看书写作业,大多在那儿。搬家完全是外婆的主张。母亲在东郊的催诗小学上班,每周周末才回来,星期天下午又去学校,聚少离多。外婆带我们姐弟仨生活,并掌管家庭开销。她认为朱家住房条件确实是好些,但房租高。而育婴堂巷8号虽差些,能省就省。将租房费省下来,贴到伙食上是正道。孩子们都在长身体,不能太亏了。
暑假后我升到三年级,教室移到北区的二层楼,我们班在一楼的东首。开学第一天,王湛老师领进了一位徐姓新同学,高大个子,皮肤白晢,面带微笑。我起初跟他少有来往,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我在班上最矮,坐第一排。与我玩的只有隔座的袁姓同学,我崇拜他是全市小学生短跑冠军;还有就是老邻居的李姓同学,我俩是棋友。而徐同学全班个子最高,坐在后排,我俩挨不上;二是那位徐同学,同学间传说他曾经写了“反动标语”,降级到我们班上的。这让我又记起了二年级时,陈校长让每位同学写那两行字,原来是为了查对笔迹,寻找“嫌疑犯”。虽然这都是传言,老师也没公开说什么,但我内心还是设防的。后来我与徐同学之间有了来往,而且一直相处很好,完全出于偶然。
一天放学后,我在二门堂里埋头看书,徐同学经过家门口,看见我后主动招呼,很羡慕地说:“你住这儿?离学校好近。”他告诉我,他家住在寺街,并邀请我以后去他家作客。这是我们之间的首次对话。言谈间,他温文尔雅,慢条斯理,我觉得他不像是写“反动标语”的坏蛋,倒更像是我的大哥。有一天我真的应邀去了他家,开始了之后漫长几十年的交往,并陆续了解到不少关于他家的故事。我知道了,居然我们两家还沾亲带故。我的姑奶奶就嫁了他族亲堂叔,按辈分算,徐同学还长我一辈。
徐同学的父亲文质彬彬,因五十年代初与朋友办了一份报纸《同人报》,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徐同学的母亲颜如玉,气如兰,声如百灵鸟,性情极温柔,优雅贤淑。她是三初中的语文教师,并知道我父亲曾经是南通知名语文老师,并认识我的母亲。第一次见面,记得她温柔地摸我头说:“小王明,真像你爸爸,唉……。”不知她为何长叹一声,但我还是感动得心头一热。
徐家大院进门有棵高大的银杏树,郁郁葱葱,据说三百多年了。到了金秋季节,徐同学会约我采果子,我们用竹杆打,或干脆爬上树摘,总会有满满的收获。高兴了,我们就用启海腔学小贩吆喝卖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一分洋厘买八颗。”这么一个充满乐趣的大宅院,我一下子就爱上了,成了这儿的常客。在长期的接触中,我感到徐同学知识面广,思想深邃,品学兼优,与他结成好友。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了“反动标语”一事,他毫不隐瞒,如实向我讲述了当时情景。
徐同学大我一岁,他三年级我二年级时,同班有位龚姓同学,每每见到徐同学,总在背后骂他是“小右派”,这很伤徐同学的心。徐父被打成右派,本已造成了家庭悲剧,而现在还要在同学中备受歧视,犹如伤口洒盐,心口扎刀。所以,徐同学对龚同学恨了直咬牙。但是,徐同学心想,反抗会适得其反,更不能回去告诉父母,徒增他们的烦恼。于是,徐同学从开始敢怒到不敢言,继而忍气吞声,再后来就不屑一顾。心烦了,就唱当年流行的那首“我是黑孩子”的歌来安慰自己:“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乡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
有一天下课时,龚同学不仅一个人,还领了几个同学,齐声骂徐同学“小右派,小右派”。面对如此嚣张的挑衅,徐同学终于忍无可忍,冲进厕所最里边,见没人,拣了地上的小瓦片,准备在墙上写“打倒龚××”。刚狠狠写了“打倒龚”三个字时,不料杨二爷爷来回摇上课铃了,徐同学赶紧扔了瓦片,溜进了教室。
过了没多久,“打倒龚”这三个字,被人发现并举报到校长室。也许是当时徐同学写字时,过于愤怒,用力过猛,加上地点在厕所最里面,墙面石灰长期受潮,所以,发现三个字时,“龚”字上半部的“龙”,石灰斑驳脱落,字迹模糊,仅依稀可见;而“龚”字下半部的“共”字,则较为清楚。这样,粗看似乎是“打倒共”,细看则还是“打倒龚”。陈坚校长带领好几位老师仔细辨认,凭她们多年的教育工作经验,大家都认为这不太像是“反动标语”,更像是学生之间的发泄行为。但是,在政治挂帅年代,谁都不敢作出最终决定,只好向公安局作了汇报。
出现场勘察的警员,首先认定这是学生所为,而且肯定是一条“反动标语”,性质严重。随后作了布置,从二年级向上,所有学生都对笔迹,一个不放过。徐同学很快被锁定了。当时徐同学的班主任是郑瑶年老师,她是南通革命烈士顾迅逸的夫人,不仅是有名望的好老师,在社会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她与陈坚校长一道,对徐同学作了问话,了解了事情经过后,都认为龚同学侮辱人在先,徐同学发泄在后,徐同学做法欠妥,但没什么大错,更不是写“反动标语”,不能将这一冤案错定于仅9岁的孩子(徐同学也是6岁上学的,三年级时仅9岁)。而警员却不是这样认为的。他单独将徐同学一个人带到现场,指着墙上,严厉审问道:“这三个字是你写的吗?”徐同学看了警员,毛骨悚然,老实地回道:“是的。”警员再审问道:“为什么要写?”徐同学如实回道:“我恨他。”于是,警员认为有了人证、物证、作案动机,且徐同学“供认不讳”,于此就此结案,将徐同学抓进了位于东郊的“教养院”(相当于现在的拘留所)。
北浩小学的陈坚校长、郑瑶年老师闻讯大为震惊。将无法确定三个字,想当然地定成了反动标语,并将9岁的小学生关进牢房,天下王法何在?她们的教师责职大于天,并没有放弃徐同学,坚持不懈的努力,向公安部门多次申诉,最终公安局再次另派警员仔细甄别,最终确定这是一起冤案,三个月后释放了徐同学。而后,家长让他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回到学校,插入我班。
徐同学没有因此颓废,仍旧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在小学考初中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省重点中学——南通中学,全班仅三人。我则考入了另一所重点初中——三初中。从此我与徐同学来往较少,各奔东西。虽分开较久,每次仍一见如故。他之后上了大学,也当了老师。如当年保护他的陈坚校长、郑瑶年老师一样,视培养保护每一位学生为己任。
在这一离奇的案件中,陈坚校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想不到有一天,陈校居然也成了“历史反革命”,事情是这样的:
又一个暑假过去,我顺利升到了四年级。依贯例,开学第一课是校长讲话。我发现这次讲话的,不是陈坚校长。她去哪儿了?不久,我发现她常蹲在北区小操场那间又臭又脏的工具房扎扫帚,又看见她在打扫厕所,这让我非常惊讶。那么一位仪态肃然,让学生感到敬畏的校长,怎么会遭此旁落?不过,自从陈校长扫厕所后,我明显感到厕所较之前干净亮堂许多,墙上刷上了白灰,少了臭味,蝇蛆不见。沿着厕所墙边,还种植了一些绿意盎然的花花草草。
有天早上,刚进校门,见陈校长低头站在大门口,脖子上挂了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陈坚”。那陈坚的名字,还用红笔浓浓地打上了叉。我不由心里一酸,又一颤。心酸的是,那么受人尊敬爱戴的校长,一直教导我们要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怎么会是“反革命分子”?颤栗的是,父亲也参加过国民党,若不“畏罪自杀”,放至时下,是否也横遭此横罪?在我年少不谙世事的内心,已是有些不寒而栗了。
徐同学很多年后,多次与我回忆起陈坚校长。他说,陈校长是个大好人,当年若不是她与郑老师坚持申辩,那个冤案,对他的一生将是毁灭性的。因此,当陈校长落难后,徐同学主动地常去位于建设路的家中看望她。若干年后,陈校长被落实政策平反。徐同学念及陈校长终生未嫁,是孤寡老人,一直到照顾她起居,直至陈校长去世。
大食堂与大炼钢铁
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要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于是,政府发文号召全民捐铁,大办公社食堂(那时城市居委会也改为公社了)。我们家将锅子、铲子、勺子,只要沾了铁星儿的,都捐给了居委会。吃大食堂、大炼钢铁成了我在三四年级时的难忘经历。
我家吃的食堂,位于育婴堂巷东巷首与寺街交界处,那儿有个“程香君疔疮诊所”。程医生让出了临街的房子,开办了食堂。食堂门口张贴的标语:“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尤其醒目,看了让人血脉偾张,共产主义似乎真的来了。
开办大食堂初期,“放开肚皮吃饭”喊得震天价响,政府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不限量,就是吃菜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甚至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摆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处处是世界大同的热闹气氛。食堂门口有只喇叭,到了开饭时,就播放着亢奋的歌:“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我听了歌声,就知道开饭了,条件反射开始咽口水,直奔食堂而去。“大食堂”刚开办时,吃的是真好,大米饭、红烧肉、大白菜、豆腐汤,有荤有素。吃饭时,食堂的大方桌子摆上了四个菜,管吃管添,热气腾腾。男女老少,欢聚一堂,边吃边说说笑笑,比在家里吃得好多了。吃完饭碗筷一推,有炊事员奶奶洗涮,咱啥也不用管。
大食堂不能白吃呀,大人们吃饱喝足炼钢铁去了,我们学生们也不闲着,被组织起来除四害灭麻雀。北浩小学很多同学,根据政府统一的时间,在老师带领下,同时鸣放鞭炮,敲锣敲面盆,拿着绑了红布的竹竿,沿着大街小巷,边挥舞边叫喊。一时间城市杂音四起,树上麻雀吓得满天飞,直到耗尽体力而坠地死亡。场面之壮观,前所未有。这样闹腾,究竟能灭多少麻雀,我们不知道,就感到真好玩。老师读报纸,说有一天麻雀死了三万只,谁知真假。
除了参加“除四害”,我们也曾被老师带领,去炼钢工地参观,宣传鼓动,现场还举行了赛诗大擂台。炼钢工地设在南通中学操场。那儿只见一个个小高炉,炉火正旺。一位师傅头戴安全帽,满脸灰土,挥舞着拳头,激动地演讲:“我们日夜守候在高炉前,每天汗流浃背,身上的衣服就没干过。大家都没有回家,困了,就在炉子前眯一会;饿了,就吃食堂送来的包子。熊熊的炉火,照红了每个人的脸,炼红了我们的心。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今年钢产量要达到一千万吨,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让钢铁元帅升帐。”看了现场,听了演讲,我幼小的心,也被点燃,有一种满怀投身伟大事业的冲动感。那时候几乎人人都学了作诗,诗句都是以七字句为主的顺口溜。诗歌也要大跃进,每个地方每天写出了多少诗,与炼出了多少吨钢一样,都要上报。那天,在炼钢现场,我们学校六年级一位学生朗诵了一首诗:天上多少星,小孩数不清;全民盖土炉,神仙数不清。为此这位同学获得诗歌擂台头等奖,奖品是一朵大红花。
大食堂、大炼钢铁,让我热血沸腾,却好景不长。不久我发现食堂里饭菜不够供应了。以前是敞开肚皮吃,现在是去晚了就吃不着。有几次,我依旧是听了:“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的歌声后才走向食堂,但迟到了,没饭也没菜。吃饭前开始有人抢位置,老人们抢不着,还大呼小叫。打饭时,给谁多了,给谁少了,给谁干了,给谁稀了,领导吃小灶了,炊事员偷着吃了……总之,为了吃,每天都有吵架的。有一天早晨,我肚子饿了咕咕叫,没等喇叭歌声响,就去了食堂。看见有一锅粥已熬好,却没人吃,另一锅粥还在熬,许多人排队在等。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奇怪。炊事员奶奶说:“早上一只猫偷吃粥,急吼吼地掉在锅里烫死了。”哦!原来如此,难怪不抢了。我饿,顾不了许多,一共吃了两大碗,打着饱嗝,背起书包上学去了。
大食堂实在是撑不下去,只好宣布散伙。大炼钢铁,也因炼出来的铁疙瘩质量太次,成为废铁而停办。我们家,又重新买了铁锅、铲子、勺子等,升起了久违的炊烟。
大饥荒来了
六十年代初,我四五年级时,天灾加人祸,饥荒席卷大地,人们都笼罩在恐慌气氛里。因为有外婆的存在,一家人日子过得虽清贫,但心里很稳当。我没有失去父亲的那种艰难无助之感,也渐渐适应了没有父亲的日子。母亲住校,虽然每周仅见两天,但有外婆无微不至的关爱,我并不感到孤独。
外婆经过许多苦难,她对大饥荒嗤之以鼻,对我们说:“人到世上不是享福的,是来还债的。苦日子既然躲不了,我们就笑着过。”我听不懂其中的意思,但这句话还是记住了。
当时我尚年幼,除了常感到饥饿,对社会形势并不知情,偶有饿死人,或某地方有“人相食”的传闻,只是大人间口中相传而已。我虽未曾亲见路边饿殍,但的确看到,包括外婆在内,不少人由于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的,也常常看到街头巷尾,来自外地或乡下的乞讨难民。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家路上见到一位白发老人,在垃圾箱中寻吃的,回家告诉了外婆,她从家里盛了一碗粥让我赶紧送去。看到老人感激的眼神,我很开心。那几年,虽然粮食已开始配给,买米除了货币,还得有粮票,我们家人也常吃不饱,但这一碗粥让我懂得了“与人为善”的内涵。
我们姐弟仨都在长身体阶段,外婆怕饿着我们,她总让我们先吃,最后吃些剩饭菜就打发了一顿。到了1961年,粮食供给越来越少,大家都吃不饱,开始有了粮荒的威胁。外婆想了许多办法,不让我们挨饿。她有时带我去菜市场,专拣那些黄烂的菜叶,只花几分钱,可以满载而归。外婆一手拎一个篮子,迈着小脚,踩着石子路,欢快回家。我有时也抢着拎,外婆说:“你长个子了,不能累坏的。”回家后,外婆将黄烂菜叶洗净煮上一大锅,没有豆油,就放便宜的腥气十足的羊子油,再放些许盐,能让我们吃个饱。除此之外,外婆还会让我们换换口味。寺街北濠河边上有几棵榆树,外婆让我陪她一起去采树叶。她用竹杆不停地敲树枝,那些青叶子就被打掉了下来,我在树下一片片捡起,不一会,能捡到一大袋子。外婆用清水将榆树叶洗干净,切碎撒上盐,用手搅拌,再撒些不多的面粉,然后捏成一个个榆树叶面团,放进笼格里蒸。不一会榆树叶清香四溢,嚼一口,有点涩,但尚能咽下,主要是可以填饱肚子。榆树叶子吃多了,屎拉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后来见了榆树叶不敢吃了。
那时候,我深深体会饥饿的感觉。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胃里并不是锐利的痛感,而是那种慢慢的虚脱。胃里没有食物,大脑没了营养,人也麻木了,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了欲望。上音乐课,老师教那首“我们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两手指挥喊道:“齐唱,大声唱。”我真唱不动。想想还是大食堂日子好,那真是“共产主义”。
无论是烂菜叶子,还是榆树叶子面团,即便是这些不能被称之为食物的食物,外婆也很少能够吃到嘴里的。她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让仨孩子饿着。记得她一度小脚常浮肿,皮肤呈现出吓人的青紫色,手指按上去,立马是一个很久不会回复的凹坑。我那时真的不懂事,不知道外婆已经有病,肚子饿了实在熬不住,就会拉拉外婆说:“我饿,我饿。”
在大饥荒的少年时代,记忆中除了榆树叶的青涩味、羊子油的腥气味外,还有一个味,也是今生不能忘的。在姐弟仨中,外婆最宠我,偶尔也会对我有一点点偏心。每月姨妈会准时从外地寄伍元生活费给外婆,我只要听到邮递员在大门外叫:“沈琪芳,盖章”的喊声,就一溜小跑,迅速从外婆枕头下,熟练拿出那枚她的方型小图章,递给邮递员叔叔。然后再将盖了章的汇单,送到外婆手上。这是我最爱干的事。因为我知道,外婆又要给我打牙祭了。外婆拿了汇单后,会拉起我小手,去十字街邮局取钱。回家路过石桥头的烧饼店,她每次总会给我买一只甜烧饼。那个刚出炉的烧饼,又脆又酥又香又甜,百吃不厌,是我吃过的最美味食物,至今仍好这一口。
在我上小学时,那烧饼的香味,与榆树叶面团的青涩味,羊子油的腥气味三种味道,还有徐同学的冤案,陈坚校长胸前的牌子,大食堂大炼钢铁的场景,诸事种种,都记在心中,七十年来,从没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