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同样的问题,已经离职的小桃说,“我身处其中的时候也觉得很难去对抗,四周好像有密密层层的网,空气稀薄,让人无法呼吸。”
工作时,她时常觉得自己像个行尸走肉,领导、同事、家庭、社会舆论……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压力都让她身不由己。
在这里,请假似乎是不被允许的。
在身体实在撑不住后,小桃请了次病假,随后便被校领导约谈,“为什么别人都行只有你不行,赶紧回来工作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而另一位年轻同事请病假后,一位老教师和她的搭班老师奚落这位同事,“以后要多上课了,因为她经常生病。”
时间长了,小桃觉得似乎有病也不能请假,不管怎样都要上课。
渐渐地,她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了。听从内心的声音好像变成了一种“错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界限变得暧昧不明,只有违背心意的痛苦是尖锐可感的。
同样身不由己的还有艾金。她曾被交代完成文化户口册的内容,需要挨家挨户地打电话,了解儿童就学情况。
其中一户人家的电话一直打不通,艾金向领导反映,只得到一句,“这种事要自己想办法,不能说打不通就不做了。”
中午吃饭时,领导提起这一茬,数落艾金年轻没经验,遇到困难不知道自己想办法解决。晚上艾金又被叫去谈话,依旧是那几句批评。
她叹了口气,“我人生地不熟,连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我没有任何办法,就是这样也要被追着说教一顿,我不敢想象拒绝了工作会是被怎样‘教育’。”
她们就像螺丝,被不断地拧紧又拧紧。旁边的螺丝有的锈了,有的断了,她们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也会受不住断掉。
艾金想过辞职,但在发现需要7万的违约金后,她说,“拧我的扳手下重力了。”
她的家庭并不富裕,母亲在一家小厂做工,父亲的单位不景气,现在每个月工资在两千块左右。
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她眼巴巴地看着其他的小朋友吃烤肠,旁边的小孩私语,“你看她盯着看。”在小同学们涌进便利店抢购面包时,艾金也挤进人流,但两块钱的面包在手上停滞了几秒,又被默默放回,“我只有一块钱。”
现在,那个买不起面包的小女孩默默熬着,努力攒钱,希求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真能攒够7万,脱离苦海。
但就像马里奥的闯关,攒够所有金币不是唯一的通关条件。
对艾金而言,父母的不支持是辞职最大的阻力。他们说“编制是铁饭碗”“当老师很有面子”“这是最好的工作”云云。而对艾金忍受的工作重压,他们漠然置之,“什么工作都这样,再忍忍。”
现在艾金不再和父母谈起这些,她知道答案是被钉死了的。
考虑再三,小桃向校长提交了辞呈。
面对她的辞职申请,领导拖着没批,反复打电话给小桃父母施压。同样是那套和编制有关的话语,小桃的家里人用贬低的方式输出,“像你这样没能力的人,辞掉编制什么工作都不会要你!”
极端的时候,他们以断绝关系相逼。
在一天天的辱骂中,小桃哭到崩溃。从教一年的经历让小桃患上了抑郁症,她曾无数次想从楼上一跃而下,想一口吞下所有的药,她苦笑,“他们宁可失去我都不愿意失去编制。”
最后,强烈的求生欲让小桃捂住耳朵跑出了围城。
从何而来的非教学任务
2019年10月,乡村教师李田田发文《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各级领导针对基层学校的频繁检查,迎检、扶贫、写通讯稿等等非教学任务令教师不堪重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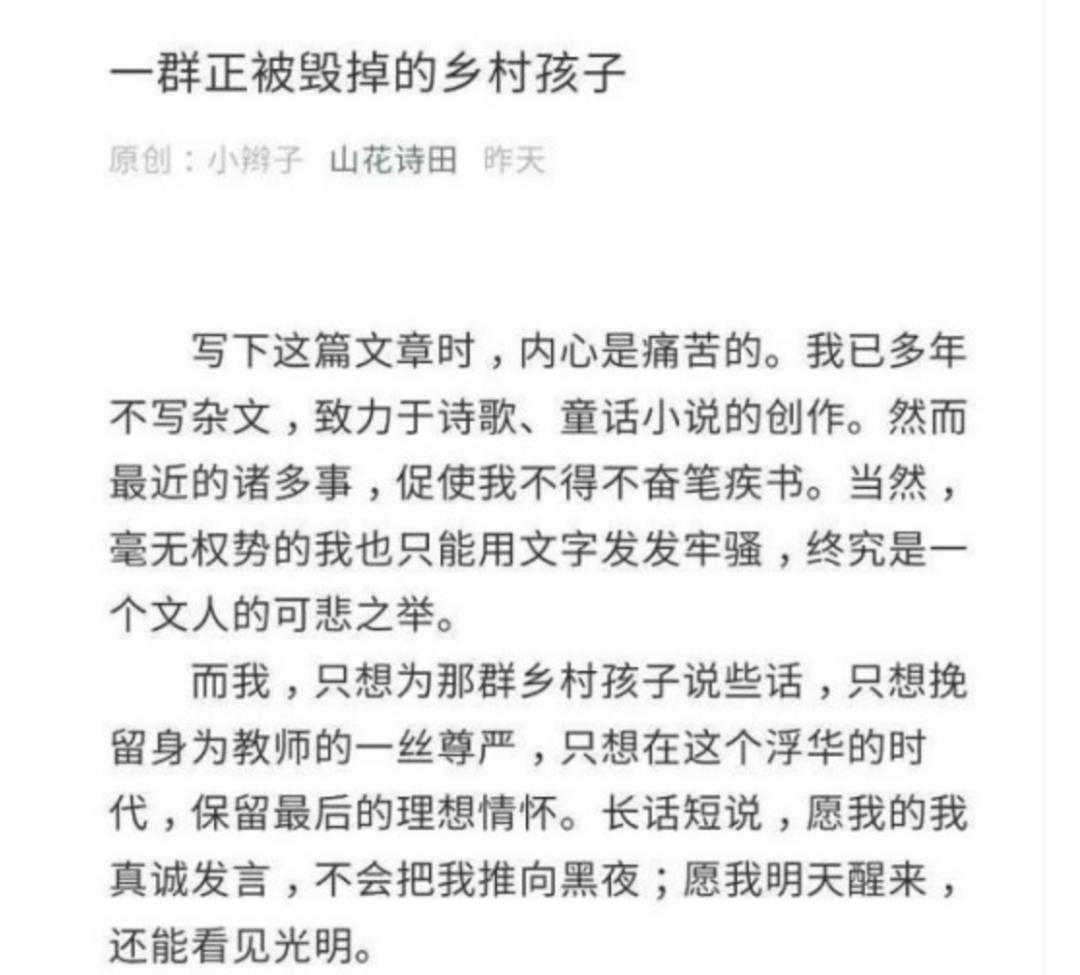
这篇文章引起舆论哗然。两个月后,中央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指出应切实减少非教学任务,“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
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文件规定,自2022年9月1日起,禁止摊派非教学任务给老师。
2023年10月,23岁的小学老师坠楼自杀,留下了还未完成的各项检查、评比、活动。
就像拦不住的洪水,即使筑起一道又一道大坝,依然会倾泻而出,最终一位年轻教师用结束生命诉说自己的反抗。
令人疑惑的是,非教学任务为何屡禁不止,它们到底是如何进入校园的?
为了更好地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了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雷望红分享她的看法。
近几年,雷望红与其研究团队奔赴河南、湖北、湖南3省9县进行县域教育调查,形成研究著作《县乡的孩子们》。在书中,她结合丰富的一手资料,深入探讨了教师们所承担的非教学任务的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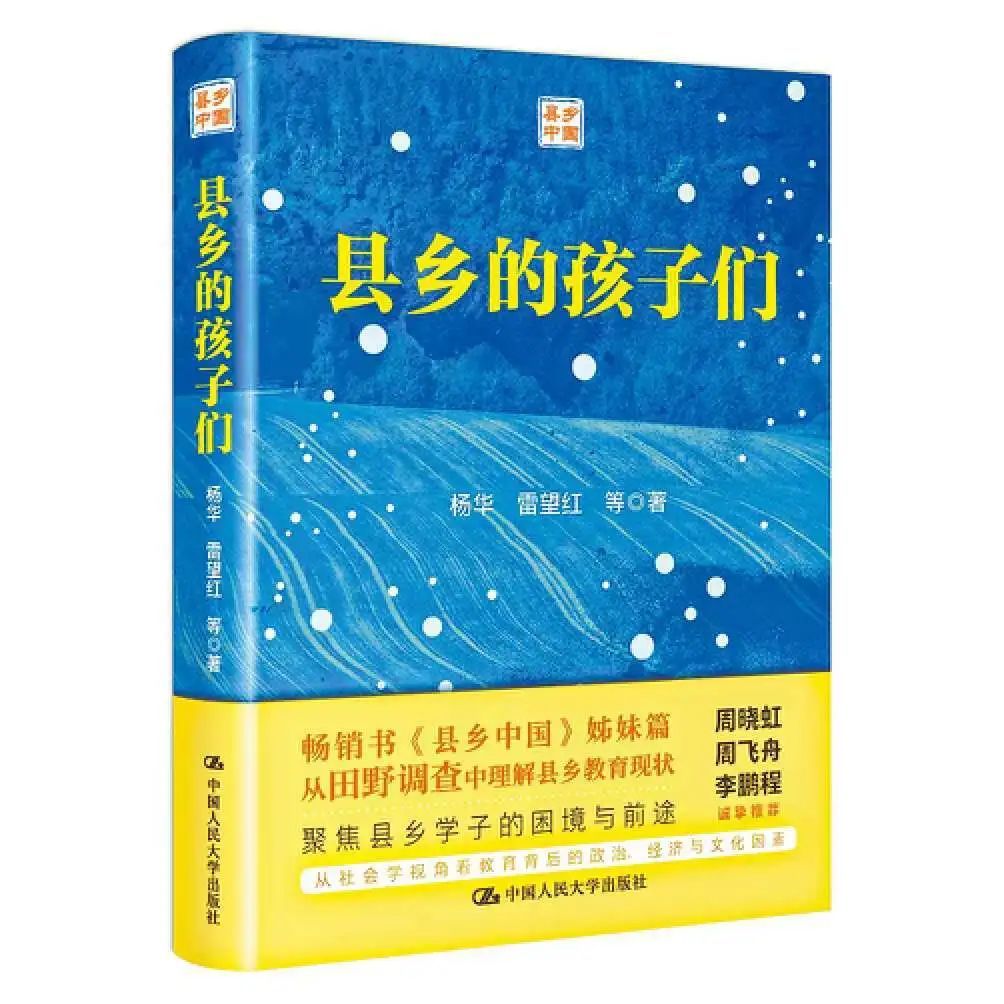
雷望红表示,大量非教学任务的出现与我国当前的规范化建设、精细化管理等要求有密切关系。
规范化建设注重工作落实和留痕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督促工作落到实处。但在问责机制的压力下,各部门往往会产生大量材料和文件以证明工作开展情况,而精细化管理又可能导致工作过度细化,原有任务量成倍增加。
例如某些学校的禁毒工作,不仅要开展相关会议,还要组织学生参加禁毒知识竞赛、禁毒作文比赛、画禁毒手抄报等等。
每个小活动都需要策划总结、拍照拍视频留痕,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这无疑耗费了老师们的大量精力。部分一线教师还反映,本来学生对毒品知之甚少,但禁毒工作“过火”后,反而可能激起一些学生对毒品的好奇。
可见,本意良好的要求如果矫枉过正,不仅增加教师负担,还可能适得其反。
那么,这些任务产生后为何会进入校园呢?
雷望红认为这与学校的组织特性有密切关系:
一,学校高度组织化,内部分工明确,容易找到责任主体;
二,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时间弹性;
三,教师队伍的文化水平高,完成上级任务的能力强;
四,学校是一个高度动员型的组织,师生高度服从组织安排,具有纪律意识。
在这几点优势的加成下,相对于其他部门,学校容易更快更好地落实工作。这也使得县政府在区域竞争的压力下,更倾向于将任务分派给教育局以完成政绩,其中自然包含了大量非教学任务。
而教育局被纳入垂直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后,就进入了对上负责的阶段,即下级要对上级交代的事负责。在这套体制下,下级难以违抗上级指令,只能回应和执行。
同时雷望红也指出,相对于其他掌握人、钱和各种项目资源的强势部门,教育局处于弱势地位。
此前,孙敏在接受腾讯新闻知识万象的访谈时也提到,他们曾询问教育局领导和科室负责人“为什么不能帮学校挡住上面压下来的任务”,相关人员表示,“就算其他部门不通过政府来施压,我们也不可能次次拒绝,因为我们老师职称定级、学校发展需要的项目资金政策支持,都在这些部门手里!你不配合,以后你有求于他的时候,怎么办?”
上级的指令加上平级部门的强势地位,教育局被围困其中,只能妥协。大量非教学任务就此层层下发,开始进入校园。
繁复的工作主要堆积在小学和初中。由于高考是教育政绩的集中体现,高中校长比小学、初中校长更有底气拒绝与教学无关的工作,因此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明显需要处理更多的琐碎事务。
而在结构性缺编的环境下,诸多中小学的在编教师被迫同时承担教学与非教学事务,就像艾金那样,需要抽出课余时间,挨家挨户打电话填写文化户口手册、统计问卷数据等等。
而这种情况的结果往往是更具机动性的教学空间被伴随强硬命令的行政事务挤压,教师失去教学自由,学生的学习环境不再纯粹。
“辛勤的园丁们”面临的是结构性困境,是一套已自成逻辑且运转“良好”的系统,这不是一篇文章、一次调查、一个简单的呼吁能轻易撼动的。
可无数处在系统末端的教师依然苦苦挣扎,反复追问着吕老师遗书中的那句,“什么时候老师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积极乐观的孩子呢?”
吕老师走后的第7天,艾金讲完练习册,拉开一张凳子坐下,双眼无神,呆滞放空。她恍惚想起八年前的某个午后,她的初中语文老师也这样坐下,带着同样的神态,呆滞地望着不知通向哪里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