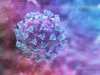脑的研究,并非只针对神经系统疾病,如帕金森氏症、老年痴呆症、脑瘤、癫痫、智障等,更重要的是研究脑的认知功能,如记忆、学习、情绪、语言、亲密关系、美感等。人的“社会认知”行为非常复杂,必须把内在的身体情况、对自我的认识、对他人的感知及人际之间的动机仔细整合,以达到娴熟的社会功能,这一过程称为“社会认知”。
目前神经科学的研究确认,人脑额叶内区的前部就是掌管社会认知;此区掌管了我们的自我认知(self-knowledge),对别人的感知(person perception),还有“体会别人的心理层面的能力(mentalizing,另有一词mentalist,心灵主义者、算命者、自称能看出别人思想的人)。此区受伤的病患就失去了上述的社会认知功能。这些知识,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傅莉受伤后拒绝外界的原因。
难道她被自我暗示,脑伤后感知别人的能力降低,最好是减少接触外界,以自我保护?有一天她忽然说:
——我的脑子要早清醒几年我怎么受得了?
——你的意思是,你受不了只是左侧瘫痪?
——可能吧?反正我现在不敢想像前几年的我。
——前几年你难道没意识到自己残废?
——我不知道。
脑伤病人的这种时间差,和单纯的肢体瘫痪者比起来是何等幸运。也就是说,清醒更为痛苦——这个情形,颇可拿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作一旁注:正常人装糊涂是为了少痛苦,脑伤者则是失去了感知痛苦的能力。
在我的经验里,一个脑伤者与社会的关系,毋宁病人被社会(正常人)所误解的成分更大,人们似乎只有能力接受她的肢体瘫痪,却不懂她的脑力、心智、情感的瘫痪。这方面的“医盲”很普遍,仿佛那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一般人对此连常识都没有;这当中,又以社会不能忍受脑伤者的非理性反应为尤,相形之下社会反而是病的,难怪西方文学常以疯癫者为主角。这是一个社会接受度的文明深浅的问题。
四、凄凉萧瑟的荒原
‘一个人的往事因失忆而消逝时,他这个人也就逐渐消逝了。我们对现在的理解和对未来的展望,依赖我们与过去沟通的能力。当我们失忆而不能在时间中旅行,就失去了关于我们是谁、向何处去的根基感……。’
上述这段文字,是从《寻找记忆:大脑、心灵和往事》中摘录出来的。作者夏克特教授是哈佛心理学家,自述曾在北卡的一间退役军人康复医院,专门记录脑伤病人的记忆。〇三年我回北京奔丧期间,在一个亲戚的书架上偶然看到这本书,顺手借回来读,却一直读不进那些抽象的理论文字。虽然我身边就有一个现成病例,并也天天为其失忆的种种情景焦虑,免不了也会用自己的“心理学盲”,去图解那种种,尤其渴望解释她“拒绝外界”的执拗。
夏克特教授说,人对往事的记忆有三个系统:语义记忆,掌管一般知识;程式记忆,学习技能和形成习惯;但记忆的提取必须在一定时空背景之中,带有某些线索的,这是因为提取者乃是相应事件的参与者,提取时带有主观体验,这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内存系:情节记忆。脑伤者常常还能保持前两种记忆,却失去许多第三种记忆的能力。
这本书讲了很多脑伤病例,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关于吉恩的故事。三十岁的吉恩,1981年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严重脑伤,大脑额叶和颞叶大面积毁坏,忘记了他的大部分往事。“在心理学意义上,一个人若失去了对全部往事的情节记忆,那么他的人生就会变得贫瘠乏味,就像凄凉萧瑟的西伯利亚荒野一样。吉恩的心灵空白一片,生活一无所有,没有一个朋友,安静地和父母一起生活。”——失去情节记忆的人,每天重复日常生活,也不会思考计划未来。
据说伊拉克战争里,两万美军伤患中20%有外伤性脑伤。一位神经心理医生说,脑伤是一种公众所知甚少、也不愿面对的一个烦恼,“在这个国家,你若脑子受伤,就没人理你了,因为我们这儿太推崇智力。人们一提起诸如精神、心灵的事情就有点害怕;你得了脑伤还能指望谁呢?”这种情形,在当年的越战老兵悲剧中已经很明显,那些有脑伤的老兵,“最终不是进监狱就是进医院,或者流落街头。”
傅莉究竟失去了什么?我不懂专业性的描述,因此说不清楚。她并没有忘记她的全部往事,却似乎一直喜欢说童年,好像那个时代的“情节记忆”拽住了她;她也可以学习新东西,只是意愿不高;至于未来,她确实很茫然。过去模糊了,未来也渺茫了。
我只隐隐觉得,她失去的智慧中的高级成分,其实是一种分寸感,极微妙的区分能力,或者说辨别微妙差别的能力。记得父亲曾教我,人的高级能力中,有一种区分差别的能力,极为重要,辨别越微妙差别的能力越强,这个人越有能力。虽然父亲大致是在讲为文之道,我后来慢慢懂了那也是人的一种魅力。傅莉曾是这样的一种人,我在书中说她:“从前的她,腰板直挺、胸有成竹、事无巨细地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现在回味起来,指的就是她那非常细腻的分寸感魅力,如今我已无法描述得具体而微了。她对人对事,是可以一眼之下就拿捏出一个合适分寸的,那种天生的直观能力准确得很少出错,乃是一种天赋,后天学也学不来的,所以她的人生,除了人力难违的天道大势作梗之外,只剩下驾轻就熟、气定神闲而已。这点天赋,被车祸撞得所剩无几。
五、人可以重新装配一次吗?
她孩童或少女期的性格,顽皮、恶作剧、幽默、绝不饶人等等,都露出来了。这是她被重建的迹象吗?如按气功,讲究练功时默想自己七八岁时的样子,一切都以返童为好,这倒是顺乎人被重建的理路。但她也许就像被重新装配过了呢?
伤残,是否也伤掉了一个人的优秀成分,还是病痛折损了人的意志?做物理治疗最忌讳凑乎,可是她如今做不到,就对付。她曾是何等一个连对付、凑乎的下意识都没有的人,却被惰性淹没到了脖子。我已经到了无休无止跟在她身后叨唠、纠正她的动作错误的地步,可是一点效用都没有。脑伤将她剥夺得所剩无几,已经没了逞强、认真、不低头的那份天性,毋宁是过一天算一天。她其实从未自觉到脑伤是需要一切从零学起的,所以她退化到了幼稚状态,在面对极度频繁的体能锻炼时,惰性便会作为一种天性而生,就跟小孩儿的偷懒一样。
然而就在她茫然于脑伤和瘫痪之际,她过去的医学知识却也回来了一点。美国人五十岁以后风行服用阿司匹林,家庭医生要我们效仿,她却很有职业性的警惕,说阿司匹林对血管里的高血脂堆积和血栓虽有化解作用,但它有抗凝血的副作用,对容易出血的人来说,隐患也很大。“别忘了你得过胃溃疡!”她说。
她与外界的交往能力,所谓social skills几乎等于零。这样的残疾,也许只比痴呆稍好一些。她只剩下一点自理能力,在一个封闭环境里有基本食宿供给的存活能力。这种结果,究竟是脑伤的程度所致,还是因为我们长期脱离医院?唯一能确定的是,我必须陪她到终老。以此而论,我下决心离群索居,买一栋与世隔绝的房子生活,仍不失为下策。
我要陪她再长大一遍。欢乐和悲苦,都像是孩子式的,是苦也是乐。一切都是她原汁原味的。我同她一道去走那条被重建或者被装配的路,掐指走了二十年。我反而是幸福的。

民主进步党
tsneroSdopl9f0l8la4t62u29l7mf003a512315m1l300m392u1434hic8tl·
陈俊翰律师因疑似感冒引起并发症,2/10前往台大医院新竹分院急诊,虽经医护人员极力抢救,仍于2/11凌晨不幸逝世。
我们闻讯感到无比震惊与悲伤,俊翰的家人低调办理后事,年节期间未对外公布,今日委由民进党党中央代为发布消息。
感谢各界关心,也请给家属空间处理相关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