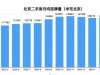——2003年10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国际研讨会 “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书面发言
我是上海人,没资格谈北京。二十多年前在北京上学留校,总共才三年,现在回来教书,也不过三年多。主持人一定要我来,拖到昨夜,胡乱写了一点,念完拉倒:
我于北京的所谓“文化记忆”,是从北京朋友那儿零星听来的。譬如1986年我与阿城在
纽约的一次闲聊,可以说来大家听听。

他说起他一位中学同学的祖父,曾是大清国禁卫军的老兵丁。这位老兵丁对孙子说,他在紫禁城城门口站岗,皇帝出巡,兵们就齐声高叫:
吾皇万岁!吾皇万岁!
老兵丁当上禁卫军那年,十八岁,光荣极了,那时噎有照相馆,他就特意穿着全套军服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当胸绣着斗大的 “勇”字。不久大清帝国灭亡了,可是老兵丁一直珍藏着自己光荣的禁卫军照片。解放后,这枚照片不能挂出来,老头子还是珍藏着。 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抄家,这枚老照片当然被抄没了。老头子实在受不了,怎么办呢,他就顺着胡同摸到红卫兵聚集的一处院子,看见许许多多抄家物 资堆在院子里,准备一把火烧掉。老头趁个空子溜进去,居然找回了自己的照片,揣在怀里跑回家,一路庆幸,高声叫道: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阿城还认得从前宫里的老太监,老太监有自己的“文化记忆”。譬如皇帝幸临宫女,是夜里点了牌子,宫女脱光了,由太监扛进皇帝的房间。这些情节,我在李翰祥导演的清宫电影里看见过,可是据老太监亲口对阿城说,皇上行房,太监们围着伺候,到一定的时辰,太监会跪着提醒:
皇上注意身体!皇上该休息了!
又譬如琉璃厂,如今还在。阿城说,在他小时候,也就是50年代初,许多店铺的后院房内还雇着不少穷文人专门抄写文物文件,写一笔好字,一千字的工钱,好像是一两毛钱。
这些细节,在我这上海人听来,真是有意思极了。可是北京朋友中,似乎也就阿城格外知道、格外留意这类事,其他北京朋友的 “文化记忆”,十之有九可就是解放后的新北京了。
譬如刘索拉说起她的高干朋友们,有些关节我就不能立刻听明白。譬如索拉说王朔是“军区大院儿的孩子”,说起她自己,却说 “咱们是胡同里长大的”。什么意思呢?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她的亲叔叔是鼎鼎大名的刘志丹——我终于明白了,就因为 刘家官位高,所以进城后分配的住处是胡同深处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
我记得1978年来北京上学,有一天在哪座楼顶上往下看,看见一户完整的四合院正在大装修,雕梁画栋,油漆一新,一打听,说是刚任命的文化部长黄镇同志马上就要搬进来。
上个月有朋友在鼓楼附近一家“竹园”宾馆请吃饭,进去一看,好气派,亭台馆榭,古木繁花,一打听,原来是康生的旧宅,昔日的王府,早先的主人,曾是有名的小德子与盛宣怀。
再譬如老同学吴尔鹿,八年前在国子监街买下了自己的四合院,种满花草,给我讲起北京老四合院的说法,我记得这么两段,一说是:
“天棚葡萄金鱼缸,肥狗壮丁胖头。”
另一说是:
“房新树矮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
下面我倒可以说说我对北京的“视觉记忆”。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在1974年,为了看“文革”期间的全国美展,刚到美术馆,人山人海,原来江青同志才来视察,刚离开。群众纷纷语告,在工农兵的画面前,江青说:
“什么叫艺术,这就是艺术。什么叫伟大,这就是伟大。”
那时,北京的旧城墙早已拆干净了,全城的四合院一户也没拆,绿树成阴,京津唐一带大地震还没发生,所以四合院不像后来成了破烂混杂的大杂院,“清明节” 天安门运动也还没发生,所以天安门广场非常空旷。当时的长安街还走着骡马大车,所有人穿着中山装人民装,所有街面或楼道都堆着大白菜……除了故宫天坛颐和 园,北京到处挂着国家机关的门牌:国务院、外交部、统战部、财政部、宣传部、总政治部、中央军委、警备区司令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华 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等等,等等,等等。
多年后,我在安东尼奥尼题为《中国》的纪录片里看见了六七十年代的北京,空旷,荒凉,沉闷,我看了,居然很亲切,那是我这辈人关于北京“文化记忆”的经典版本。概括说来,北京不是明十三陵,1972年。选自法国70年代摄影集。
清帝都,而是一座共产党的城市,一座被共产党成功地乡村化的城市,一座完全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城市,就像今天电视里出现的朝鲜平壤,空旷,荒凉,沉闷。
但在一小部分准共和国青少年的记忆中,北京是骄傲的城市,这种骄傲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家长的行政级别与官位高低。我所认识的北京同辈只要问你住在北京哪 个区、哪个大院,上过哪所中学、小学,甚至托儿所,就掌握你的出身、地位与重要性:是区级还是市级,是民盟还是政协,是军区还是中央军委,是中央还是中央 直属,是中央办公厅还是中南海,等等,等等,等等。
他们说起朋友时,十之有九不是朋友的名字,而是对方家长的名字,这些名字不用介绍,譬如 刘少奇、邓小平、邓颖超、陈毅、彭真、叶剑英,等等,等等,等等;另有一批家长的名单也无须介绍,譬如郭沫若、老舍、曹禺、胡风、郑振铎、吴祖光、徐悲 鸿,等等,等等,等等;还有一批名单恐怕也无须介绍吧,譬如傅作义、蒋光鼐、梁启超、梁漱溟、章乃器、黄炎培、马寅初、梅兰芳、齐白石、张伯驹,等等,等 等,等等。
在上海、台北、香港以及海外,也住着不少民国共和国政要名流的后人,但没有一个中国城市像北京这样,密集居住着这么多历史人物的家属。他们有的 闭口不语,从不说起以上人物,有的对于上代未曾公开的轶事或屈辱如数家珍……今日出版盛世,你可以在无数书籍中读到北京的“文化记忆”,可是很难读到关于 以上人物真实生动的描述。
譬如今年初夏,北京播放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其中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解放后借住亲戚张伯驹家里十六 年,死在张家。大家知道,民国年间张伯驹变卖房产,购买晋唐时代的稀世文物,解放后又将文物捐献国家。可是他晚年怎样呢?我有一位京城朋友曾是张伯驹的忘 年交,说起这位民国公子的最后岁月——70 年代末,张老先生每天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对着所有节目张嘴傻看,除了吃饭,一刻不离开,直到夜里上床睡觉,直到死,天天如此。
我们应该请张伯驹之流来参加这次会议。但从他晚年的故事中,我们看见,北京的文化记忆,他个人的文化记忆,在他身上似乎冻结,终止,没有意义了。
我不懂历史,更谈不上北京的“文化记忆”。我对北京甚至一点也没有“都市想像”——北京的“都市想像”可不是谁都可以“想像”的,它需要的根本不是“想 像”,而是权力——1949年以后的北京“都市想像”,首先是,也只能是毛主席的“都市想像”,例如拆毁城墙、到处建立苏式工厂之类,而他的想像全部实现 了。改革开放后,北京的“都市想像”是历任市长譬如陈希同、张百发,以及今日王岐山等等连同大群开发商及所谓国际建筑大师的宏伟“想像”,例如“民族风 格”的建筑大盖帽、拆毁胡同四合院、起建歌剧院、奥运会场、中央电视台之类,他们的想像,也全部实现,或正在实现中。
总之,在北京,我看不出北京居民的“都市想像”,北京居民的义务是尽快配合大规模迁移,他们被“请”出北京,落户郊外,将他们在北京城所剩无几的“文化记忆”尽快抹杀干净,实现政府的“都市想像”。
算回去,民国北平的“都市想像”,是将古老帝都改造成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城市;1949年后的北京“都市想像”,是将这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城市改造成革命 化、军事化、乡村化的城市。1979年以后的北京“都市想像”,是将这座点缀着古都遗迹的准共产党城市化妆成香港化、美国化的摩登城市。今天,北京以无数 欧美城市、街道、小区的名字,命名北京城无数角落——北京过去二十年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北京的想像力、全中国的想像力,甚至全世界的想像力。
自然,“都市想像”也意指反方向的,历史的想像,在字面上可与“文化记忆”是一回事。我不是学者,以我的十二分非专业的定义,只要发生过的事情,哪怕是 关于昨天,都应该算是“记忆”,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甚至宣称“未来也是记忆”。可是诸位知道,关于北京的想像也好,记忆也好,只要是在北京地面上,最好 不要随便“想像”。大致说来,凡越是遥远的、消失的人事,越是安全的、可说的,越是切近的人事,则糊涂一点,能不说,就别说。
胡风在1949年写过一首献给新中国的诗篇,其中有一句话: “时间开始了”,意思是说,1949年以前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哪来记忆呢?
五十四年过去了,情况与胡风的意思正好相反:1949年以前的 “时间”与“记忆”循序恢复了,反而是“时间开始”后的这五十四年,还是最好不要随便记忆吧。今天,我仔细看了本次座谈会的每一篇论文题目,“时间”全部指向1949年以前,全是被准许的“文化记忆”。
这很像是老人的记忆:越是切近的事情,越记不得,越是早先的事情,记得越清楚。北京是一座古城,或许正需要这种“局部失忆”的记忆。也好,北京的变化, 是持续消除记忆的过程,我们先来试着恢复纸面上的零碎记忆吧——那位前清的老兵丁尚且终身守护自己的记忆,我们是不是应该向这位大清国的禁卫军小兵丁好好 学习?! (2003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