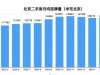可怜那些学子与平民,竟不晓得他们从一开始就触犯了天条,而去幻想他们响遏行云的呼号和森林一般挥舞的手臂能正天听、挽狂澜。
这个政权是暴力革命的产物,最终也要用暴力来捍卫它。想变天吗?无妨一试,但他们当年流了那么多血,你们就要还这么多血来。这绝不是戏言,而是见诸《人民日报》的大块文章和政要的公开讲话。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什么民族的福祉、社稷的安泰之类都被简化为――到底是你还是我来坐江山!
这正是现代中国的困局。执政者已断然排除了和平变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苍生之福,又会堕入强权阴谋和政治仇恨的历史因循之中。说到底,千年来每一次改朝换代,终不离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说这是一次创世纪的伟大尝试,其结局竟也并无例外。
九、
我离开了煞气重重的崇文门,折向北行。
一路仍是劫后景像,又发现南北走向的好些路段沥青层大面积龟裂损毁,当为重型战车轰隆辗压所致。就在某个路口,我意外看到了已绝迹多时的白制服交通警察。以下这些细节,或许有助窥探屠城黑日之军与警的微妙关系――
路心的交通岗亭已被战车撞翻,交通警背著手站在路边,无所事事。马路已无正常交通,民用车辆极为罕见,却不时有拉著“为民送粮”横幅的军车在未及清理的障碍物之间绕行。显见得在居民的抢购风之下,首都存粮已见危机。再者,廿万入城大军的给养消耗也颇惊人。交通警神情沮丧地目送著军车,那些车牌标志和识别号码是他闻所未闻的。有路人向他搭腔,交警回应以满口京腔,于是一下子围拢了好些平民问这问那,我正好听到两句对答。市民不知问的什么,警察嘴角向远去的军车一撇:“他们连我们也打!”市民又问:“这些大兵在北京还呆多久?”交警以尖刻的京腔答道:“您问我,我问谁去呀!”
可以想见,戒严部队的总攻时刻、行动路线以及“强制措施”的具体所指,首都交警大队全都蒙在鼓里。我记得第一支从西南路冲击广场的军队前锋杀至,在靠近前门的“东方明珠大酒楼”路口值勤的交通警还在岗上,当其时那位警察也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战斗一起就溜之乎也。
平心而论,凡长驻北京的卫戍区官兵、武装警察、刑事警察、交通警察、户籍警察甚至包括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内心大都同情民运,只不过交通警察仅系准军事组织,与公务员近同,政治纪律不那么严密,故能斗胆讲几句大实话。
甚至于军队,这一路我也得睹奇景。又经过某重要路段,这里有多辆军车残骸,其中一部履带式军车烧毁得那样彻底,以我对兵器的无知,竟认不出它原先是装甲车还是一种军事指挥车,总之烧成一堆废铁,右边一大截履带脱落,像一条僵死的巨蟒瘫在路心。一切都显示当时战况之惨烈。此处现驻扎著大队士兵。我初时骤见路边绿地竟然坐满了穿草绿军服的大兵,吓得几乎掉头而去,却又恐显得形迹可疑,唯有硬著头皮向前骑行。殊想不到这里的气氛要比前门、崇文门轻松百倍。兵们摘下钢盔,敞著风纪扣,在草地上矮树下或坐或卧,像郊游野餐似的。只有当官的仍戎装肃整,挎著手枪四处游动。他们对路心的劫后景像熟视无睹,事不关己。附近是新一代的高层住宅楼群。那些不识天下凶吉大事的孩童憋闷多日,择这好天气下楼撒欢来了。士兵们很喜欢逗孩子玩,百无禁忌的小童钻入士兵丛中,连跑带跳。兵们乐不可支,或搂抱,或将孩子举放于军车上。孩子们的父母先是戒备而后也趋前拉话。我见状也下车缓行,听见许多对答。市民的问话大抵千篇一律,士兵答:他们是沈阳军区开来的,六月五日才进城,一直停留在这里。有的兵为了回应尖锐质询,拉开枪膛给市民展示里头并无子弹,又说他们这一路根本没有配发弹药;有的兵被问道,路心被毁的军车是哪一部分的?兵漠然回答:“不知道。”当官的根本无意监听部下的对答,至于市民更大胆的话语,当官的都装听不见。
可惜我无法多作逗留,目标是安定门――首都机场――广州。每一阶段都吉凶未卜,唯有谨慎从事,少去招惹,以免无事生非。依照妻子的路线图,我绕开重兵把守躲、杀气腾腾的建国门立体交叉桥,也避开大片使馆区,但散布好几处的外交公寓总不能完全绕过,也就看到了一些戏剧性画面。这里多了些小轿车,均系外交官的黑色专用牌照。这些轿车都装扮得像庆典花车,除了车头两面国旗招展,车后天线杆也绑上更大幅的国旗,车身则贴满五颜六色的外国国徽,隔一两条街也识别得出这是外国使馆的专车。我想,这是派驻那些政变频仍、内战不息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习惯沿用的应变措施,却在北京派上用场了。一幢外交公寓前,接送侨民撤退的大巴士正在装运大小行李,连等候上车的外国孩童都手持一面小国旗。
即使未曾亲睹六四惨况的人,只要看到这些场景,便可相信这个国家的确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场专制对民主、野蛮对理性的战争。
十、
终于到达安定门约定地点。刘心武已在等候,他待在车里没动,只用失神的目光打个招呼。
我认得《人民文学》的车,司机却是新面孔,既不是以前给王蒙开车的老杨司机,也不是那位曾给“借”出去拍过两部武打片的地趟拳全国武术冠军。
我把单车放到地铁站出口处。相信妻子要过好多天以后才敢到这边来取――如果它还在的话。
钻进车里,刘心武简短说几句有关机票和航班的事,便归于沉默。司机亦无言。这张生面孔令我颇不安,更不敢多话。再等一会。《人民文学》的王清风来了,我稍觉宽心,是他送我们去机场。
车子发动,起行,一路窗外大同小异的战乱景像,四人都各怀心事,默不作声。直驶离城区,开上通往首都机场的公路,王清风才给我介绍,这位年轻司机也是刚“借”来的。大陆单位的司机时常被借来借去,不足为怪。介绍毕,王清风也不再多言。刘心武更是一路沉默。
通往机场的道路并无军队踪迹,更无截查哨卡,这倒是怪事。内乱一起,占领电视台、电台、电讯电话局、报社、机场都是通例,亦系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和光荣传统…..机场指挥塔从平坦的柏油路尽头迅速崛起,第二个目的地就要到了,而此际稍稍松弛的心弦又再抽紧,包括司机在内,一车人都颇觉不安,实不知此刻首都机场成了什么样子。
拐入停车场,又看到多辆撤侨巴士。前些天尽管各国驰电紧急撤出侨民、专家、留学生,却无法抵达机场,有先见之明的英美等国,在五月份戒严令生效时已包租下靠近机场的假日酒店,临时安置侨民,一有风吹草动便直奔国际机场。那些动作稍慢的则要滞留到这时才得以返国。
望去国际航线候机厅门口净是箱笼行李、男女老幼;国内航线大厅之混乱更难以想像。然而,我们之忧虑倒不在于此,机场如无戒严部队把守,想必是另一系统的人马把关,重点甄别和防范“XX分子”出走。我们都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分子”,总之,所谓空弦落雁,铁腕强权之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惊弓之鸟。
王清风早年也是行伍出身,很精明强干。他让我们安坐勿动,证件交他去办理登机手续。王才进去一会就转回,一切办妥。他说国内航线反而很冷清,多数国内搭客都困身城内,无法前来。听机场工作人员说,昨天飞广州的航班才六个乘客。看情形,大厅里也并无异常情况。
我们其实到得太早,这种时局势必要加大时间提前量。接下来,只剩下沉闷的等待。我自是无话可说,只听见刘向王交待若干编务,其中提到已征集多时的《人民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册。其实,在纪念册上赋诗题词的群贤,如今其中不少人的命运已难预料……
十一、
终于起行。我和刘步入大厅,果然不见了太平时的熙熙攘攘,但旅客还是有一些,想是今日城内气氛已略见松弛之故吧。我注意到各航线办理机票登记之处,都是清一色民航职员,并无加派身份神秘的人手;进而又留意到,一些样子太过年轻、神情却憔悴不堪的乘客,他们是临时前来购票的。机场的惯例都不向外售票,只能在城内民航售票处预购,只有个别常年出差而又门槛很精的人才晓得如果某班航机有空位,机场间或也发售即时机票,但仍须出示个人证件以外的单位证明。而我看到现时这些临时购票者似无此类单位证明,口头向民航职员询问交涉,然后一亮窝在手心的证件――我相信那是学生证,机场职员一改平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孔,慨然允诺,并即刻著手办理,收款、开票――就这么简单快捷。
这些细节,我想刘心武也注意到了,但我们没有交流感想,只低头走自己的路。
唯一出现的武警制服,是进入候机休息厅的检查关卡,此处向来就有的,一切运转依旧,也许只是我的心理感觉,那几位男女武警对学生模样的乘客的检查放行,似乎比旁人还快捷利索(后来我得知,机场很快就被严密控制,此前的松缓再不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