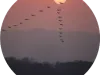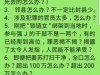几年前,台湾某电视节目一个嘉宾的一句“大陆人消费不起茶叶蛋”引爆中国网络,网友们纷纷晒出自家的茶叶蛋进行各种炫富各种摆阔……老实说,我觉得这件事一点也不可笑。
台湾与大陆,几十年前都是偏见与一母同胞的党国教育的覆盖。大陆的小学课本上,必定有歪戴帽子斜挎枪的国民党匪兵举着皮鞭挥舞在劳动人民的头上,旁边配曰:试看台湾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悲惨生活;台湾的小学课本上,歪戴帽子斜挎枪的变成了“共匪”,旁边配曰:试看大陆人民在共匪统治下的悲惨生活……
不得不承认,国共两党起步都是苏俄训导的,怎么说也是一母同胞,思维与作派,也就惊人的相似了。所以双方互相丑化起来,就是切换一个概念的事。
但是,台湾后来不是转型了么?台湾不是亚洲小龙起飞了么?小龙起飞的起点可以定在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说,它起飞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经济的起飞及领导人的明智与勇气,带动了政治的转型,转点可以定在20世纪70年代,它转的时候,正是我的童年时期。
大陆这边当然知道台湾不缺钱,特别是我们的课本,说老蒋往台湾跑的时候,带走了多少黄金白银云云。何况富人家吃肉,穷人看不到肉,总是能闻到香的。总之,我小的时候,就很恨台湾国民党反动派了。其时我经常听人说,台湾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派特务前来大陆联系业务,甚至派飞机,从天上给大家扔手表、大米啥的。我得承认,我那时候就很有特务的潜质了。至少我经常恨恨地想,台湾特务咋不联系一下我呢?不联系,至少我在地里打花杈的或者拨玉米棒的时候,能给我空投一块手表,或者金条啥的。甚至正干活的时候,我都会仰望天空——没法仰望星空,因为干农活必得大白天,而且标准的45度,可叫仰望日空?但是很遗憾,每次都让寡人失望。失望之余,当然更要痛骂国民党反动派了:老不要脸的,你那手表大米都酒到哪儿了,姑奶奶这儿一次也没捡到!
我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是否知道大陆人民,包括我这样一个农家穷孩子的心理,只知道,大陆号称从20世纪80年代起,也撅起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撅起是值得狐疑的。第一,撅起前政府就有言在先了,先让一小撮人先富起来,比如王石那样的,至于绝大多数人,就瞪眼看着吧;第二,中国的换算办法,从来都是国富。比如秦国那个时候,商鞅改革顶多是国富国强,打仗不怕自己死,更不怕别人死,砍头就象割韮菜,割回来还是计件工资与计件奖赏;但是,国富国强的背后,却是民穷民弱民卑民贱民愚的。总之,不要以为撅起了,人人就能吃蛋了。
我68年出生的,但是小时候,真没吃过蛋。我说的是囫囵蛋。茶叶蛋也好,煮鸡蛋也好,没有记忆。
娘也养鸡——那时候家家农民养鸡,但养鸡不是为了自家孩子吃蛋,想的美,养鸡是为了卖蛋,并且当时流行“鸡蛋换盐不找钱”。也就是说,鸡蛋与盐是等价的,农民拿蛋,来换一些高昂的工业日用品——所谓的工农剪刀差,也就是政府对工业产品高定价和对农业产品低定价,新中国所谓的原始积累尽在农民身上榨取矣。
娘养鸡也跟她绣花一样仔细。每个鸡什么特点,长什么样子,说不好听点,娘养鸡比对她的孩子可能还要仔细,因为孩子变现时间太长,且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可以自动形成传帮带的生态链;鸡没法互相照顾,且变现较快。说来也怪,鸡确实跟人一样,总有一些鸡,比其他发育较快,男的英俊无比,女的漂亮优雅,娘对它们就特别的偏爱。当然娘在选鸡的时候,就很有经验的,每只小鸡娃,掂着它的一只脚倒挂一下,娘根据它们的叫声与形态就能判定,哪个是母鸡,哪个是公鸡,甚至娘还端详小鸡的容貌,来判定谁将来长得好看。总之,公鸡有一两只就够了,母鸡愈多愈好,那些长得漂亮优雅的小母鸡,总得娘的偏爱。爹知道娘偏爱她这些小鸡,每次从菜地回来,总是用菜叶包一些他摘回来的各色菜虫,拿回家就犒劳给这些小鸡了。
我清楚地记得,某次我坐在院里,看着这些鸡四处觅食。其时有一只公鸡,强吃强占,我有些看不惯,手里拿着一粒石头子儿,拼命砸了出去——结果,我撞祸了,我发现,娘最喜欢的,而且也是我最喜欢的那只,最漂亮最优雅的模特鸡,翅膀扑楞楞,翅膀扑楞楞,栽到地上,不动弹了。我吓得大叫,娘啊娘啊,我娘就跑出来了,一看她最心爱的那只鸡死了,当场就哭了。于是我娘开始破案,问我怎么搞的。我分明知道,肯定是我的石头子儿砸到了这只鸡的头上,但是,看到我娘眼泪汪汪的样子,我没勇气承认,我是杀手。于是我摇头再摇头,不知道,就看见她正吃着东西,就扑楞开了。于是我娘继续破案,她发现了鸡中间的一只菜叶子,突然明白了,把我爹叫出来,声泪俱下的批评他:都怨你,都怨你,你从地里弄的菜虫子是不是太大了,噎死了我的鸡?
爹说,菜虫怎么能噎死鸡?
娘说,别说了,以后再也不要往家给我弄那了,都是你找的事儿。
爹无话可说,讪讪地走了。
爹娘从来没生过气,但是,唯有这次,娘真跟爹生气了,而爹,明明是替我背了黑锅。我得承认,这桩事我从来没有给爹娘承认过。一者是它在我心里烙印太深,二者,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是不敢承认了。
娘养这些鸡,除了换工业日用品,甚至还能充当医药费。比如请村里医生给孩子看病,她就需要攒十天半月的鸡蛋。所以鸡是村民的流动银行,平时看鸡,大家都挺上心的。有时候鸡会迷路,甚至跑到别人家,被别人关了起来,成了别人家的。娘养鸡用心,每个鸡都认识,甚至知道它们的特点,所以,别人家想关我们家的鸡,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娘也很智慧。比如某家鸡跑到另家了,某家上另家寻回,一般的说法是:你家这个鸡是不是我家的?对方一般斩钉截铁地:哪里是你家的,明明是我家的。而我娘,根本不用此法。有次,一只鸡跑丢了,娘先去串门破案,终于在对过一家看到了,那只鸡正在她家给圈着呢。于是娘直接走过去,说:哎,我家的鸡怎么跑到你家鸡圈里了?对过大娘心虚气弱地说:那谁知道,我也没看,是你家的,你就快抓走吧。
我前面说,没有吃囫囵蛋的记忆。意思是说,小时候,只记得喝蛋汤了。而且这个蛋汤,还得是有亲戚来了才能出现。记忆最深的是大姐夫结婚前后常去我家。他是女婿,去了经常有优待,有鸡蛋汤给他做。鸡蛋汤做的很讲究,就是一锅水,打上一半面疙瘩,一半面糊,煮开后,打蛋花。农村主妇最会打蛋花了,就是鸡蛋一头去灶台上一磕,磕出一个缺口来,然后撕掉缺口处的蛋衣,缺口朝下,把蛋液洒向滚开的汤锅里,这个时候就要看主妇的水平了,就是用蛋不多,一个,顶多两个,就满锅黄黄白白的漂着蛋花。然后洒上些香菜,放些香油,没有香油的话,我娘会弄一点食用油,放进勺子里,勺子放到火上,眼看着油变热,往里面洒些葱花,葱花一见热油,变黄,香味也出来了,然后连勺子带油葱,伸进汤锅里,噗,汤锅一阵小沸腾,就满屋飘香了。
那时候大姐夫的村里比我们村富些。富的标志就是,他们村一个工分一至两块,而我们村才一毛两毛。一个工分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壮年男人一天给生产队的干活所计的10分!比如我去干一天,顶多5分,算半个工分,年终分红,半个工分是一毛或两毛除以二!
大姐夫村比我们富些,而大姐夫也有个特点,在我们家吃饭,老留着一些肚。比如我娘煮的稀饭特好喝,他喝一碗后,就不再喝了,但等我娘刷锅时,发现还剩一些,就会要求家庭成员来加饭,其时我是加饭专业户——甚至我大学毕业没结婚前,只要路过我一个闺蜜家(她老公是我同事,时间长了我俩成了闺蜜)门口,她就会逮住我,快来快来,我早上做的饭多了,中午做饭腾不开锅,我热热,咱俩一块吃了,我才能做新的……我发现,只要大姐夫在,他也是加饭专业户,我娘一说饭没喝碗,他就掂起自己原先的碗,来,我加,而且一加,还能加两碗的样子。我怀疑大姐夫享受他的鸡蛋汤的时候,也留着肚呢,总之他自己喝过之后,总会从待他客的主房,跑到茅草屋的厨房,一到厨房,就发现我们几个孩子在喝蛋汤,就马上调侃我们了:看来我以后得多来,我不来,你们也喝不上蛋汤是不?我一来,你们都能跟着我喝了!
二姐小时候身体弱,好生病。按娘的分析,二姐跟二哥挨的太近了,也就是说,娘怀了二哥之后,二姐就吃不上奶了——乡村很少有一岁就断奶的,很多都是好几年才断奶,一者是人穷没钱买零食,二者是孩子闹了,把奶杵给孩子是最省心的哄孩子办法。甚至有些孩子,临上学前,都要跑他娘怀里,吸几口奶(没水也吸)才心满意足的跑向学校。总之,娘认为对不起二姐,没奶之后,摊的白面小煎饼把二姐养起来的。所以二姐一生病,不能吃饭,娘就拿两枚鸡蛋放灶台一边,扣上一个捣蒜的蒜臼子。也不知道烤多长时间才能烤好,只知道那鸡蛋烤出来以后,金黄金黄的,香味溢满整个屋子。二姐比我大五岁,二哥比我大三岁,我闻着那香味,真的不能自抑,但我知道,那是二姐的病号专用饭。终于有一天,我站到娘身边怯怯地说:娘,咋我就不生病?
我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二姐正在吃她的鸡蛋。其时她已吃了一枚。按娘给我的回忆,二姐把第二枚让给我了。但是很遗憾,咋我就不生病,及第二枚鸡蛋,都是娘事后讲给我的。我只记得前半截,金黄的鸡蛋,满屋的鸡蛋香,就是不记得后面,为了一枚蛋,我跟娘抱怨,我为啥就不生病。
高中同学老韩说,他每年过生日,他娘就会给他煮鸡蛋的。太奢侈了,我家没有。我86年考上大学的,清楚的记得,预考之前(我们那时有预考的,过了预考,才有资格参加高考的),同学玲玲的父亲给她送来半篮子咸鸡蛋,看得我惊心动魄——她爹可真舍得!她家可真有钱!其时我爹也经常去学校看我,但看我都是给我送饭票和菜钱的。清楚的记得,爹有一次批评我:三毛钱给你,放都放烂了,都不见你花!
86年至90年,读大学期间,不记得怎么吃鸡蛋。一是钱的问题,二是,在大教室听课,发现一些人吃过煮鸡蛋后,真心不好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鸡蛋在我这里,由满屋飘香,变成臭味难闻的。或者说,煮蛋,确实没有火边的烤蛋香!
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开吃鸡蛋了。现在我最喜欢的一种吃法,就是煎蛋,我一定把它煎得黄白黄白的——宾馆里那种煎得流蛋液的,我不接受。我把它煎得两面黄白黄白,然后夹到小碟子里,洒上些许白糖,它就是我最喜欢的早餐了。感谢党,感谢中央,感谢主席,我终于吃得起蛋,不用蛋疼了,但是我真不敢保证,大陆其他人都吃得起蛋了。台湾人不是偏见,不是宣传,毕竟,大陆这么大,有些是第一世界了,有些,第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你有蛋吃,并不代表所有的孩子都有蛋吃。阿门,愿上帝保佑所有的孩子,都有蛋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