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审查已经进入我们的血液中
腾讯文化:您写作大概三十年了,在您眼里文学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阎连科:我最初的写作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逃离土地、要成家。但是真正到了后半生,自己就说不清文学是什么样的存在。到这时文学可能真的进入到血液中、生活中,我就是要这样活着,(于是)就这样写下去了。
腾讯文化:提到您的书经常会跟"禁"这个词联系起来,禁与不禁,这中间有边界吗?
阎连科:我认为“禁”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但是我一再强调:一个作家被禁,并不等于他是好作家;一本书被禁也并不等于这本书是好书,不禁也不等于是坏书。一部小说的好与坏要靠小说本身来说明。
我今天的写作已经不再把握任何边界,只是希望自己的思想和想象能完全飞扬起来。我经常说:别人不解放自己,自己首先要把自己解放出来,没有任何禁锢、没有边界地写作。这个写作既包括内容,也包括形式,更多的可能是在艺术上。一个作家不要去审查自己,因为会有很多人帮你审查。
腾讯文化:但是很多人在取材上会不由自主地作出取舍。
阎连科:我一直特别相信一点,中国作家从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之后,我们每一个作家血液中都有一个本能的自我审查。就像我们阅读的课本一样,从一年级读书,课本其实是被很多人审查过的,审查已经进入我们的血液中间了,所以这个边界其实是本能的。
当然,有时自己可能不会发现它的存在,我也是通过写《丁庄梦》才忽然发现它是自己经过自我审查的一次写作。这部书不管好与坏,仍然被禁掉了。经过自我审查之后写出的这样一部作品,仍然没有让广大读者进一步阅读。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既然)有人帮我审查,那我就自己解放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腾讯文化:但是实际上比如说拿《丁庄梦》来说里面反映的现实可能是您以前作品里面尺度最大的一部?
阎连科:《丁庄梦》是我最温情的一次写作,特别是对人的爱和理解、日常人性的挖掘。这本书被禁掉可能是题材的原因。我想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艾滋病问题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
有人说,如果这部小说是别人写的也许就没问题,但因为是我写的,可能就会得到一种特殊的关照。《丁庄梦》给读者带来了更多现实意义的思考,但它并不像《受活》《日光流年》那么有难度。更散文化、更传统,在小说艺术形式探索上还有欠缺。
我认为这部小说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是值得去禁的,它是一部充分表达主旋律和正能量的小说,人物、故事都充满了温暖。禁它的人是一时脑袋糊涂,早晚会醒过来。
腾讯文化:您一直提倡的“神实主义”,在《丁庄梦》里表现得也并不是太多。
阎连科:“神实主义”这个概念是在写了《丁庄梦》《风雅颂》之后出现的,但最清晰的出现是在《四书》中,是因为《四书》的那些情节和细节。但是,“神实主义”在这中间有了非常清晰的概念,有了对自己小说的更正,我也希望通过对它的表达给自己的写作推开一扇新窗。
别的作家都在讲荒诞的、魔幻的、现代的、后现代的、黑色幽默的(东西),但你会觉得这些都不准确。我经常说,今天的评论家是相当偷懒的,他们不太去思考用一种新的理论去表达新的小说,总是用旧理论去谈新事情。所以,在《四书》之后,我写了《发现小说》这样一本书来讨论现实主义、二十世纪文学,也提出了“神实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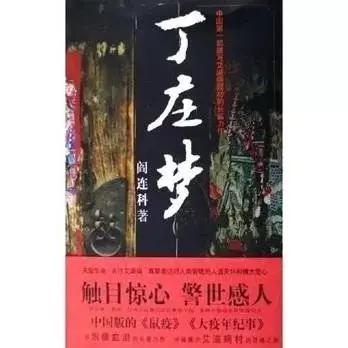
真善美是主旋律假恶丑同样是
腾讯文化:您怎么看待人性,特别是几千年传统的农耕社会生长出来的人性?
阎连科:第一,人性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是分不开的。比如,我的青少年时期在非常偏远的农村,那时会觉得人性充满温暖和美好,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经过的事情越来越多,你会发现人情越来越复杂,会看到更多黑暗面。我想这与我的经历和年龄有关,所以在写作中也会更清晰地表现人性的复杂性,解剖人性最阴暗的一面。我想这不是表达你对生活的美或不美,而是你认识到人和世界就是这样。
第二,我们不要简单地用真善美和假恶丑去理解小说,真善美是主旋律,假恶丑同样也是主旋律,因为我们把假恶丑呈现给读者,见证了人性最黑暗的部分,那也让人性变得更美好,让我们更警惕一些东西,它同样也是一个正能量的作品,我们要正确理解正能量的宽泛性,不能简单理解为某一点。
腾讯文化:比如《炸裂志》里这类群体,每当他们走向一个未知的新生活时,对过去基本没有任何眷恋,并且以前农耕社会留下来的传统也没有积淀。比如,您写到,突然有一天村长想到哭坟的习俗已经忘了很久了。您是怎么对他们这种表现做判断的?
阎连科:在我全部的写作中,《炸裂志》是一部最直接关注中国三十几年现实的作品。关于农耕文化、改革开放、城镇化,乃至于中国梦等很多问题在其中都有很大信息量。
今天的社会现实情况是:当我们迈开步子,把改革作为发展,所谓进一步城镇化和进入现代化时,许多东西都在被迅速地抛弃。比如哭坟的情节,小说最后他们才想起来重新去(哭坟)。
今天的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也在迅速抛弃过去。我们恨不得以一夜之间的速度奔向西方的文明,抛掉两三千年的文明。不管我们怎么强调国学和传统,但事实上文明正在被抛弃。
比如,我们到处看到立交桥,但是立交桥墩子下的古文明其实都被抛弃。《炸裂志》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
腾讯文化:您刚才说到的迅速抛弃,知识阶层身上也有,王蒙把它总结为弑父弑兄的行为,就是后人不断地否定前人。
阎连科:我想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共同的、有预谋的抛弃,从城市到乡村,从南方到北方,从知识分子到农民。除了建筑问题,还有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过度崇拜(问题)。我们今天所有的理论都来自于西方理论,而非中国原有的或古典的理论。西方从理论到实践正在取代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谁都无法阻挡它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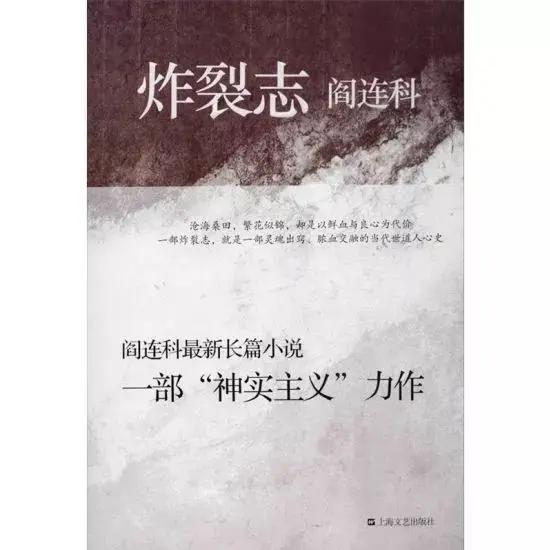
写《炸裂志》时没有想到潜规则问题
腾讯文化:小说里的主人公的姓氏安排有什么寓意?比如姓孔的(孔明亮)带着全村青壮年去当贼致富,姓朱的(朱颖)带着全村女人出去卖淫致富,姓程的又依赖于姓孔的。
阎连科:小说毕竟是小说,没有明确意义,并没有想得那么远。比如,我家在河南嵩县,家门口就是程颐、程颢,写《两程故里》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在两程故里读书。
小说是要讲究趣味性的,要给读者留下更多东西。我让他姓孔、姓朱,没什么明确目的,但是会给读者带来更深远、更复杂的思考。有时写作的人只要给读者一滴水,读者就能从这滴水上看出大海,这滴水必须交给读者。
就写作来说,我仅仅是希望交给读者一个望远镜,至于读者望到哪里是另一件事。写作者一定要留给读者诠释的空间,否则小说没有可读性。今天的读者是极其智慧、极其会读小说的,你要留下很多让他创造的可能性。
腾讯文化:您在小说里给孔明亮的升迁设计了一套官场逻辑,您怎么看待传统社会里权力运行的潜规则?
阎连科:其实我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潜规则的问题。我不可能像《国画》《羊的门》之类的小说写得那么细腻深刻,我的强项其实是放弃那种最真实的东西,而完全用想象抵达另外一种真实。
关于这套线索,我全部的努力就是要讲一个好看、丰富、有意义的故事。这个有意义是指读者在阅读中,甚至在读后回想时,会忽然发现故事含有多层意思。
在我的全部写作中,《炸裂志》是第一次听到有很多人说:阎老师,我是一口气把这个小说看完的。它在我整个写作中确实是最好看的一次,同时它的现实性和探索性也仍然存在。
在这个小说中,我的想象力有可能超过了《受活》《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在《受活》之后的写作都在原地踏步,但是写到《四书》《炸裂志》,我想或多或少是有进步的。最明显的就是小说中的想象更加狂野、飞扬,当然这种想象是非常接地气的想象。
腾讯文化:在您眼里什么是一部好小说,是卖得多,还是写得好?
阎连科:我想每一部伟大的小说都存在问题。如果一部长篇小说完美无缺,那么它不会有多大价值。一部小说存在问题根本不可怕,最重要的是有多大的不可替代的创造性。创造性同时也会伴随巨大的争论和缺陷。
对我来说,只要你的写作创造出了别的作者不具备的小说元素,那就是好小说。当然,一个作家每天都在创造,可能一生都没有创造出一部具有创造性的小说。
小说更多是停留在小说本身,是故事、人物、情节、细节,反映出作家的文学观和世界观,给人类带来思考。小说有没有价值在于你给这些读者和批评家留下了多少诠释空间。你留下的空间越大,作品的意义就越深远、越深刻、越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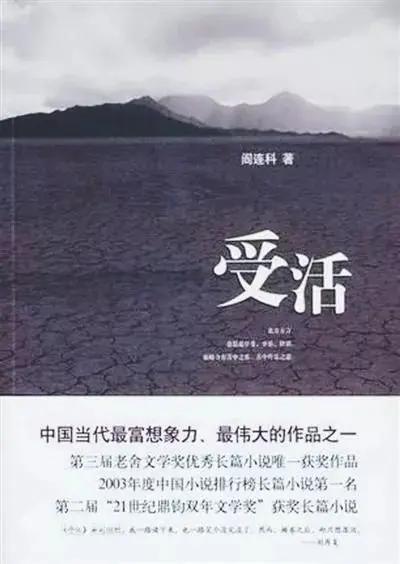
今天每个人内心都极其分裂
腾讯文化:很多西方汉学家都在说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叫做超稳定。对于您笔下农村文化的超稳定结构,您怎么认为?
阎连科:西方人在谈到超稳定的时候,可能指的是这样一个社会结构。比如,他们会认为你们有多少人下岗,或者有多高的房价,社会就会崩溃。但这些数字在中国都失去了效应,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个超稳定的社会。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西方所谓的超稳定是从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科学的数据来对应中国文化,认为是超稳定,其实并不是这样。
今天的社会最不稳定的是所有的人心,每个人的内心都极其分裂,人性的崩溃已经到了边缘。这可能是我们最敏感的神经,不被西方人把握,只有我们内心知道。
就像《炸裂志》写的人心的分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裂,各个阶层的分裂,城乡的分裂,贫富的分裂,这种分裂已经到了一种神经接近于崩溃的状态。
但是,中国是一个久远的、有传统的社会,有可能某一件事情就把我们统一起来。比如奥运会、钓鱼岛,就会把很多分裂的情况统一起来。所以一边是分裂,一边是有可能挽救缓慢分裂的各种办法。
我们中国人心最分裂,但也往往容易被某一个事件所吸引,从而进入某一个专注点,这一进入就是五年、十年。我想我们的超稳定可能在这。当有一天我们的人心没有被统一到一个事上时,那社会就真的崩溃了。
腾讯文化:就拿《炸裂志》里申请超级大都市的情节来说,他们虽然凝聚到了一块,但最后的结局是悲剧。您刚才也提到了奥运和钓鱼dao。奥运之后,北京的空气越来越差,70-80%的场馆今天都荒废了;钓鱼dao事件,全国上下同心凝力,但事实上很多城市是在打砸抢。把这些投射到书里,超稳定结束之后,是不是都得悲剧收场?
阎连科:文学和生活不能彻底对应。《炸裂志》充满想象,它的真实感是小说某种精神上的真实感。比如,这个城市最后成为超级大都市之后,一个有野心的人带着一个城市三千万的人们朝着西方去。
这是个极其荒诞的情节,但它恰恰表达了刚才我们谈到的某一事件和情节,能够把中国的人心带到某一个方向。这是不是悲剧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今天中国人的心被某一个来自于阴谋的事件所带领,对应的恰恰是今天中国人内心所有的焦虑和不安。
这部小说的奇妙之处就在于精神上的真实。虽然小说里的很多情节和细节在生活中无法发生,但是我们不会怀疑它不存在。
腾讯文化:您在写作时,对民族主义狂热或者是民粹主义有没有关注?
阎连科:我想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都来自于中国几十年习惯的革命和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一百年来都处于革命和运动中,即便是搞经济也是一场运动。这使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迅速地发动起来,被带到某个地方去,比如大跃进、反右、文ge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