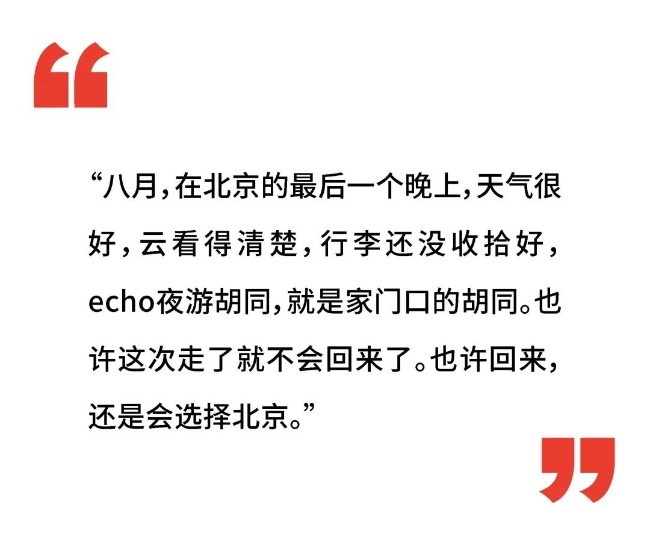
“你只能反复告诉ta,这不是你的问题。”在一期离开北京的播客里,竹子印象最深的是这句话,“这个感受非常普遍。刚离开时候,我会想个人原因和环境因素哪个更大。”今年8月,她离开了北京。
很少会这样,离开一座城市,人们要如此谨慎地反思、审视自己,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但北京是个特别的地方。
人教版教材里,每个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就该认识“北京”,它出现在课文《我多想去看看》里:“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我多想去看看!”
来到北京总是相似的野心或者激励。地图上,北京是雄鸡的心脏。去北京,有出息。
而北京又是个复杂的庞然大物。它创造了许多名词,北漂、朝阳群众、海淀妈妈,人们被北京定义。关于它的文章光怪陆离,《北京零点后》是密集,《北京折叠》则是吊诡。今年六月,北京成为中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实现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的目标。
于是,说起“离开北京”,像是逃兵,被竞争、房租和交通压垮,一种被淘汰的失败。
近三年来,“离开北京”这个话题越来越热门,而且人们的去向越来越多元,去深圳、去上海、去成都、回老家、去国外,已经有很多地方可以拿出来和是否留在北京相衡量了。这是怎样的一种趋势,同时也是一个个真实故事发生的情景呢?

20+,
离开北京的 gap year 探索
毫无疑问,竹子在北京已经足够努力,光看她的履历表就可以知道。
从2019年毕业前,到2022年,竹子在北京至少换过五份工作:广告公司、纪录片工作室、文化空间、剧场、媒体……
与此同时,她还在夜里兼职,有时是咖啡店的店员,有时则是酒吧bartender,最晚时清晨六点下班,早上继续上班,精力充沛得像个孩子。
北京满足了她探索的欲望。竹子在东北成长至22岁,学习的广电专业,在家乡一带往往只能找到事业单位的工作,她总是倒在笔试环节。
在北京,工作机会要庞杂得多。剧场那份工作,竹子起先只是想搜索现代舞课程,却找到了招聘启事,几个月后,她就与以色列、加拿大老师,一同出现在舞蹈周节中。另一家文化品牌,竹子则干脆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在空间里遇到了陈嘉映与刘瑜。
北京永远有最新的东西。竹子刚来北京时,短视频上了风口,无论她在的哪家公司,都愿意试试短视频;疫情之后,她的工作又转成了新晋宠儿——播客制作。
就连兼职的酒吧,在北京也有足够多的划分。一种是她热爱的酒吧,多在东城,譬如school,人群混杂着随意喝酒,聊天才是要紧事。
另一种泛称为三里屯酒吧,由知名调酒师、优秀供货渠道、稳定而资深的投资者组装而成,像一辆福特汽车。据说,部分酒吧有着严苛的规则,着正装进入,消费达标可以进入二层,再往上升,还得有点品味,一种隐喻。竹子的态度是:“我暂时是不太习惯三里屯酒吧。”
在京三年,竹子的工作就在“东城酒吧”类型和“三里屯酒吧”类型中切换,要么是更成熟和商业广告公司,要么是体量更小或更理想化的文化公司,总是不满意,两者难以平衡。商业化带来了无价值感,而缺乏商业的理想同样感到让人虚无,竹子说:“那种没有一个行业和岗位想做,就和咖啡师没有一个店想去的感觉是一样的。”
疫情是让竹子离开北京的直接原因之一:她所兼职的酒吧和咖啡店都不得不关闭。正职的文化空间也从实验性的,变成努力求生的小店。
竹子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至少她还挺喜欢bartender的工作。于是,她去了三亚,继续做bartender。

此前,她犹豫过,对于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能够成为白领的人来说,完全变成bartender是否是一种堕落?
但三亚好像没人在乎。这里曾经去过、住过北京的人不少,现在,他们都在这里,等到夜里来喝杯酒、聊会天。
竹子的生活变成了发呆、潜水、无所事事或是学习。她想:“离开北京对于我们这样机会很少的小孩来说,其实只是让自己有得选,哪怕只是看起来的、暂时的。我终于发现,当吧员不是一种跌落。而是回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再去看能做什么,代价是什么。”
可以把离开北京看作是竹子的gap。她在北京已经培养了足以养活自己的技能,只是,浩瀚的机会让人疲惫。她需要休息和考虑。
竹子打算继续学业。那之后,会不会再回到北京?也许吧,谁也无法预测几年后的事。

同样去往了旅游城市的还有日尧,她在大理和滇西之间往返,从事动物保护工作。
在离开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前,日尧决定:“我要到山里去,人越少越好。”而后得偿所愿。
滇西的村寨得开车抵达,距离县城一个小时的路程,拢共二十九户人家。每天早上八九点钟,长臂猿像公鸡打鸣那样把人叫醒。村民们把长臂猿叫做“甲米呜呼”,傈僳语,“呜呼”就是模拟它的叫声。
和族人建立联系,日尧也会和他们一起喂牛、打笋子,偶尔用汉语聊聊天。傈僳族人说汉语依然遵照自己的语法,先说主宾,再说谓语。
大理的办公室没那么山野气息。其实日尧过去并不喜欢大理:“总让人想起安妮宝贝,或者文艺青年。就是太文艺了的感觉。”但她觉得大理和想象中很不一样。
在大理,日尧租住在750元一个月的房子里,看得到苍山,走路几分钟便能到达古城。她参加过706空间的聚会,在那里,比她还要“离经叛道”的人更多,数字游民们分享着经验,大家把大理叫做“大理福尼亚”。
“离开北京以后,感觉到世界开阔了,原来还有那么多种生活。”这是日尧的感受。
在北京,日尧最自在的行为,是工作后去看live。非得在现场,才能冲刷格子间里螺丝钉的感觉。每周或每两周一次,从公司出发得一个小时,回家得两个小时,北京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超大城市里可供选择的娱乐地点种类不多。日尧的工作地点曾在798边上,有同事趁着午休一口气逛了三个展览。今年,庞宽进行了十四天直播,日尧很容易地认出那就是798里的星空间。
798园区里四处是涂鸦,时不时有人拍照,日尧觉得那很傻——她太频繁地来到798,对于涂鸦已经习以为常。她几乎不拍照,能找到的完整涂鸦照片只有一张,是一行字:“今天是好人,明天不一定!”
换了工作近一年,日尧还没有去过live,也没有再去找live house。好像不再需要了。日尧暂时没有计划再回北京:“现在,我还有好多地方想去。”
30+、40+
最后的离开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