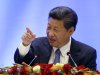文史大家宋云彬在日记《红尘冷眼》中,写下了建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他以亲历者的身份作了真切、生动、具体的记载。这记载,还原了历史真相,也还原了那荒唐岁月。这些“运动”无一不“扩大化”,给人们带来了无妄之灾,也有饱含辛酸的“笑谈”。宋云彬日记是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补充与旁证的。
一
1952年初,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2月23日,浙江省主政者告知时任浙江省政府委员的宋云彬,浙江大学有“‘大老虎’,苏步青、蔡邦华等交代问题,群众表示不满”,同日,从谷超豪处得知,在浙大,受到冲击的,还有“民盟同志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寿恒等”。3月23日,得知“苏(步青)交代问题不真实,五次均未得通过”。没有问题而要“交代”,这又何从“交代”起?无法交代而作的“交代”,则被认为“不真实”了。在宋云彬,他是了解情况的,可举一例。1952年3月10日,在文教、卫生、新闻、出版系统之打虎大会上,“有孙世立者,当场坦白贪污黄金四千五百两,其兄孙世轮已早受逮捕,贪污黄金五千两之多,其他银元谷米等尚不在内。医师王季平当场坦白,贪污黄金及其他物资,数量超过孙世立”。这交代的都是巨款,而这些单位一年的经费又有多少,遑论作为医师的,能经手多少钱?又何来这么多黄金?主政者以为“打虎运动”有了大收获,清醒者如宋云彬则在次日赴文管会“谈昨晚打虎情况,闻者大噱”。只是简约地如实写于日记中,但“闻者大噱”一语就很可以反映出这如同闹剧一样的逼供是如何在制造冤案,而在当时又是怎样被作为笑话来看待的。
这次三反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可以从宋云彬在1952年5月10日记载中看到:“下午(浙江省)沙文汉副主席邀浙大一部分教授茗谈,对‘三反’及即将进行之思想改造交换意见”,“物理系教授束星北首先发言,反映‘三反’运动中种种偏向,声泪俱下。”且言及对具体领导浙大“三反”的某人当面指斥:“我很鄙视你,你不配领导‘三反’,更不配领导思想改造!”作为享有盛誉、被称为“中国爱因斯坦”的一代物理学家束星北,以如此激烈的言辞一改以往温文尔雅的处世态度谈“三反”,也可见这次运动对他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伤害之深了。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程孝刚、苏步青、陈建功等多人,也都对三反运动中不讲政策、伤人之深的偏差作了尖锐的批评。
二
1958年刮起了“大跃进”的狂风。在宋云彬的日记中,可以见到已作为“右派”的他记下的种种荒唐事迹。1958年7月7日,浙江省政协组织人员去丽水参观,“晚,参加文教专业组,听取丽水县文教方面各负责人之报告。报告扫盲工作者谓经过八昼夜苦战,扫了五万文盲,每人认识了一千五百字”。对此,宋云彬的反映是,“骤聆之,殊难相信也”。凡有常识的人也是“殊难相信”的,但却是在“大跃进”中实实在在发生的怪现象。
在1960年,因“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已漫卷全国,5月10日,晚饭时与家人以及友人闲谈时,宋云彬感慨,“凡事必须实事求是”,他回忆在郑州参观所见,“参观展览会,讲解员指陈列的七个大鸡蛋,谓是一只鸡在一天内所下,并谓现已跃进到每天一只鸡下十四个蛋”。他还谈及1958年“有人赴天津参观农村,谓一亩试验田产粮达十万斤,皆与事实不符也”。鸡下蛋的“大跃进”,是可以编入新版《笑林广记》的。
1958年席卷全国的,还有大炼钢铁。大炼钢铁遍及各单位,连宋云彬所在的中华书局也领受了炼钢任务。原料从哪里来?要各人自行设法提供,1958年10月19日,宋云彬由他的女婿“买到废铁十一斤,值二元”。次日,“送废铁十一斤交中华书局炼钢部门”。10月23日,“下午将下班时,忽得通知,有紧急会议,必须参加。6时,会议开始,主席报告本单位自二十六日起,每天须出钢二吨。人民公社全部社员除年老病废者外,皆编入炼钢部队”(按,1958年10月18日,中华书局在“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全国皆办人民公社的形势下,已成立“十月人民公社”。我所就读的北京政法学院在8月即已改名为“钟声人民公社”,但仅是挂了一块牌子而已,当年所发的毕业证书,也并未用什么“钟声人民公社”的名字)。“会散后,匆匆回家吃饭。饭后即赴局参加劈木柴”。次日,忽得通知,令宋云彬所在的后勤第八组“全部组员参加劈柴”,下午,又“继续劈木柴”。以木柴引火炼钢,已是笑话,但从这“紧急”通知来看,也是颇当作一件事的。
三
1957年7月开始的反右运动,是众多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先是,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宋云彬读后“为之悚然”,感觉到鸣放“自此收矣”。但是,尽管有此认识,却在6月10日出席浙江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发言时表示“不甚赞同”这一社论,认为人民日报针对卢郁文接到之恐吓信发议论,殊不知写恐吓信者决非人民内部的人,不必予以重视,一重视适堕其术中也。知识分子的天真,表露无遗。而在浙江日报交宋云彬审阅这一发言记录,6月11日以头条新闻发表这一发言,加以小标题曰“宋云彬不同意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时,还没有清醒过来:“其意是宣扬邪,抑恶意挑拨邪,不得而知矣。”对反右的决策有非议,他被定为“右派”已是“理所当然”了。宋云彬的日记留下了一个“右派分子”个案的记录。查当时的材料,为“坐实”宋云彬的右派罪名,罗致的“罪行”有:一、他认为浙江省领导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偏差;二、他认为浙省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不够重视;三、他主张应有创作自由,反对行政过多干预;四、提倡“内行领导外行”,认为领导应该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这些言论,使他蒙难22年。
在宋云彬被定为“右派”后,还连累到了他人。1958年9月3日,他得知新华书店的王平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罪名之一,为“曾数次奉命送书”到宋云彬寓所,由此,“降为勤杂工,月薪二十元”,后,又“被开除出店”。
在精神极度痛苦的情况下,宋云彬“无夕不饮”。1958年3月1日,“偶成一绝”:“驱遣牢愁酒一杯,名山事业敢心灰。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与同为海宁籍的从延安走来的女作家陈学昭一样,以对省委领导不重视文学事业的批评而获罪,成为“右派”。虽经周恩来命周扬打电话给浙江主政者,说陈学昭的用意是好的,但也未能幸免。而已升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也被打入另册沦为贱民了。1958年4月8日,宋云彬得到通知,从九级干部降为十四级,工资为131元(原为232.55元),房租则从9.45元增为16.07元。1958年5月5日,又接机关事务管理局电话,令迁往涌金门外67号。至此,对他作为“右派”的处理才告结束,但所受的屈辱则还在延续。可举一例,1958年12月18日,在中华书局,“下午奉陪开会,讨论到所谓右派分子可否担任责任编辑问题,又受一次侮辱”。宋云彬没有写下讨论的结论,这是他刻意回避了,那时教师中的“右派分子”都已被赶下讲坛,又遑论在出版物中需署名为责任编辑的“右派”?
四
1959年3月中旬,“忽接全国政协秘书处电话,云邀请余当政协委员,通知寄杭州被退回,现已经派专差送去云云。未几果接到通知书,内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扩大)协商决定,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特此通知。”对这一记录,我有两点不明:一、政协秘书处何以尚未了解宋云彬已由浙江调至北京中华书局工作?二、浙江有关方面何以不把信转至中华书局交宋云彬而径直退回政协?浙江的有关方面当然是知道宋云彬调往何处的,是他们开的调动介绍信。对第一点,我的解释是,宋云彬虽为“右派”而作为历史上有贡献的知名人士,被列为政协委员仍为统战的需要,却因一段时间的中断联系,而不知已调动了工作;对第二点,只能猜测为浙江有关单位仍是心怀不满了:何以这“右派”仍能蒙受中央高层领导的青睐?
1959年4月25日,宋云彬见到了政协送来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计副主席十四名,常务委员一百四十二名”。作为有心人,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常务委员中的“右派分子章伯钧、龙云、黄琪翔”三人的名字,又写下了在小组讨论时组长沈体兰的“传达说明,谓全体委员一千零七十一人中有右派三十八人”。这是“传达”,可见是政协领导的“说明”。这传达,说明了“提名章伯钧等为常务委员之理由”,想必也有说明政协决定三十八名右派为政协委员的“理由”,但在“传达”时从简了。宋云彬的日记,保留了一份历史资料。
在宋云彬的日记中还写有一些“右派”的神态和活动。1959年4月23日,出席政协会议。“休息时遇章乃器,傲岸态度依然似昔也。”这也说明了,以章乃器来说,对“右派”并未认“罪”,或也无“罪”可认也。
宋云彬以个人身份加入民盟,罗隆基就是介绍人之一(另一人为中共秘密党员周新民),但来往并不密切。在作为“右派”时、或作为“摘帽右派”的年月中,却有了来往。于1960年2月政协组织的参观活动中,3日,在洛阳,宋云彬去了章伯钧夫妇的房中“闲谈”。“叶笃义、陈铭枢先后来”。在洛阳,因黄药眠、朱光潜有病,宋云彬也为他们的诊治提供了意见。1960年3月12日,在郑州参观,晚,又在“章伯钧房中闲谈”。1961年6月23日,宋云彬去政协“小吃”,“遇熟人甚多”,“坐了章乃器的车子回来”。1961年6月28日,“5时半,坐罗隆基的汽车去政协”。1961年6月30日,“晚7时,坐千家驹的汽车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建党四十周年的纪念会。1961年9月16日,“5时半,乘罗隆基车赴政协吃夜饭”。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中有专文写罗隆基,说章伯钧作为“右派”由行政三级降为七级,还有专车,“罗隆基是从四级降至九级。”“专车便没有了”。而从宋云彬的记述来看,罗隆基是仍有专车的。1961年12月17日,章伯钧至宋寓,“谈约1小时”。这些“右派”,也还有一些“政治活动”。1961年3月29日,在民盟总部,宋云彬参与听取了“章伯钧谈尼泊尔国情”,甚为“扼要”。
因了宋云彬的日记,为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在作为“右派”的一段时间里,留下了些许活动身影,但也仅是身影而已;这也弥足珍贵了,毕竟,对他们在这一阶段的情况,留下的记载不多。
五
1958年的“大跃进”带来了严重后果。1960年12月17日,宋云彬写有:“近来学校学生及各机关干部多患浮肿病”,“面目手足浮肿”,“甚至全身浮肿,有死亡者。”其中的一代学人卢芷芬,“即患此病死也”。卢芷芬生于1910年,于1960年去世,才50岁。他于1931年考入无锡国专学习,与周振甫同学。于1933年进入开明书店,与先一年进入“开明”的周振甫一起作为宋云彬的助手编辑《辞通》,为《辞通》编索引。建国后到北京,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又在宋云彬领导下工作。1957年,作为书生的卢芷芬未能免祸,1960年终因缺乏营养而去世。那时可购的食品已极稀少,有所谓“高价食品”的,也不易购得。1961年3月30日,宋云彬在中华书局“买到一只老鸭,重约3斤,每斤四元”。这12元是什么概念?当时一个二级工的工资是28元。大学毕业生刚工作时的工资是43元,一年后“转正”的工资为53.4元。
宋云彬的日记,可作为信史的补充,为一段时间里的“运动”留下了可供回味的一鳞一爪。
《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