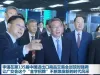中国农村一景。中国农业农村部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村级债务总额已达到9000亿元,村级组织平均负债达130万元。
最近这几年有关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就是"债务风险",近三年两度掀起讨论热浪,主角均是中国房地产超霸恒大公司,华尔街关注的重心就是恒大破产后的债务风险是否会外溢。今年从8月中旬恒大在美申请破产之后之后的热议持续了约20天,《华尔街日报》9月8日那篇《人人看空中国,但债券投资者除外》按了暂停键,该文称恒大债务风险不会外溢,因为许多中国公司发行的美元债券与美国国债之间的收益率差保持相对稳定,这表明投资者认为,虽然中国经济放缓,但不会严重到令这些公司无力偿还债务的地步。恰在此时,《中国新闻周刊》于9月6日刊发一篇《70万个村庄,欠了9000亿?》,海外一些自媒体以为这是重大新"新闻",立刻又延伸至"中共即将垮台"这个老话题。
村级债务是积年沉疴
其实,村级债务问题算是积年沉疴,多年来也不断有文章谈到。
按时间先后排序,以下几篇很有代表性:
贺雪峰:《解决村级债务刻不容缓》(2015年10月28日)
梁晓飞、刘良恒:《越是“明星村”,负债越严重?》(《半月谈》,2019年5月13日)
邵海鹏,《村级债务已达9000亿!“小村大债”怎么来的?如何拆弹?》(第一财经,2023年3月8日)。
梳理这几篇文章,村级债务的形成一目了然:
1、债务分新旧,成因不同。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18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截至2006年底,全国村级债务规模为4000亿元。
中国农业农村部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村级债务总额已达到9000亿元,村级组织平均负债达130万元。
根据上述文章采访三农专家们,村级债务分成两类,其中一类是1990年代至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间村集体形成的债务,被学界称为“传统村级债务”或“旧村级债务”,为4000亿。这部分税费改革前形成的旧村级债务,部分是因收缴税费导致的债务,部分是村集体为完成上级的经济考核任务而举债兴办集体企业形成的。除了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民间金融机构的借贷之外,还有向村干部与村民借贷的高息借款。另一类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形成的新村级债务。村庄建设导致的建设性债务是新村级债务的主要来源,项目制则是新村级债务产生的制度背景,笼统计算,2019年的9000亿减去2006年以前的4000亿,新村级债务约为5000亿。
2003-2023“建设新农村”花费巨大
说起来,中国农村在中国改革中的地位曲折多变,当年中国改革始自农村,带头吃螃蟹的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发起的包产到户。简言之,1989年以前的中国农村改革曾经中国社会带来了生机,但从1990年代中国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农村在一段时期是放任自流状态,迅速走向破败,不少地方乡村黑势力泛滥,出现了所谓“三农问题”,当时政策研究者与学界将乡村治理分解为农业(生产)、农民(人)、农村(社区),似乎认为可以分开治理取得成效。胡温时期,“三农”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因此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始乡村治理。从2023年开始,口号随着治理重心不断变化,胡温时期叫“千村示范、万村整治,造就万千美丽乡村”。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浙江的乡村治理口号是“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美”。如今早已弃用“三农问题”,称之为“乡村治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需要花大量银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公共财政资源是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向农村输送的。具体说,中央政府为了保障专项转移支付体现政策目标,往往要求地方提供30%~60%比例不等的配套资金,村庄在承接项目时也需要一定资金投入,其目的之一在于对基层政府或地方社会产生激励作用。但是,很多村子没有能力筹集相应的配套资金,只能采取借债、欠款等方式,因而形成村级债务。研究者总结说,如果说旧村级负债是一种资源挤压型负债,新村级负债则是一种资源输入型负债,形成于21世纪以来国家大规模自上而下向农村输入资源的过程中,是资源下乡的一种异化结果,这一总结堪称到位:“产生巨额新村级债务的原因当然不在于资源本身,而是在于资源落地的操作方式”——说白了,在中国腐败的吏治环境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项目资金成了村干部这个小的权力共同体的吸金管道。
在建设性债务之外,新村级债务中还有一种因集体经营项目产生的经营性债务。村级债务中经营性债务占比高的村子大多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浙江省丽水市的村庄就有这样的例子。《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提到,截至2022年6月底,丽水市有986个村子有村级债务,负债金额共计5.93亿元,其中集体经营性负债约为3.73亿元,占比接近63%。经营性债务的偿债能力,由举债村的经营能力决定。丽水市村级债务中,3.73亿元的集体经营性负债推动形成资产6.09亿元,年度收益4722.45万元,平均收益率达12.64%。当村庄自身条件一般或是村集体经营能力有限,经营性债务可能会成为难以填满的窟窿。广东省一些城市周边的村庄为了发展经济,向银行借贷在村里建了工业园,期望工业园建成后租给企业,形成稳定收益,但是一部分工业园的设计不科学、招商不顺利,项目经营失败,因此形成村级负债。经营性债务则主要是向当地农商行、信用社的贷款,还有一些是向“先富起来的村级精英”的借款,往往是有息债务。
据研究者调查后分析,经营性债务可能会比建设性债务更棘手。吕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建设性债务形成后其实就锁定了,不会增长,但经营性债务可能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地为了盘活经营性项目有可能持续投入,使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贺雪峰的文章认为,村级债务直接影响了乡村治理。村级债务总量并不庞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数量远大于此。村级债务数量并不大。甚至相当部分村庄,国家每年转移下来的财政资金,要远远大于村级债务。因此,村级债务问题本质上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对村级债务的认识问题,对村级债务负面后果的认识问题。国家每年向农村转移支付超过万亿的资金,目的是为了缓解三农问题,建设搞好乡村治理。但村级债务不解决,农村正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不确立,无论多么巨大的转移支付资金在落地时都会事倍功半,达不到应有效果。
村级债务的风险不会外溢
中国债务问题确实是个问题,恒大等房地产公司的涉外债务只是其中一部分。除了时不时热议的地方政府债务之外,本文述及的村级债务是另一积年沉疴,但它不算政府债务。这里我得特别说明一下,中国政府机构的末端是乡镇,村委会只算“村民自治组织”,村长村支书均不纳入国家干部等级序列。
基于以前我对中国地方债、中央政府债务、企业债的分析,我认为在中国各种类型的债务中,村级债务可能是风险最不会外溢的类别,影响的主要是欠债的乡村本身,不会在中国引起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更不会对中共政权形成冲击。这就是村级债务形成时间长达20年,年年都在累积,但并未听说引起金融爆雷事件,比当年P2P的影响小多了。美国几大金融评级公司分析中国债务,基本上未涉及这块的原因也在于此。
现在回答一个曾被问及的问题:如果中国实行政府或者准政府组织破产制度,学习现时的英国伯明翰(刚宣布破产)、昔日的美国底特律,中国农村是不是将遍布破产村镇?好象也不至于,因为毕竟平均每个村子只摊到130万元债务,至于村里的秩序如何维持,钱多钱少,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些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村级的项目资金,多是被相关利益集团层层瓜分,落实到村民头上的可能不到一半。如果村委会不能再继续举债运转所谓“项目”,最多就是让村干部这个权力共同体少了一个吸金管道。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